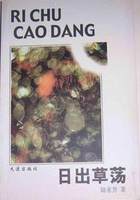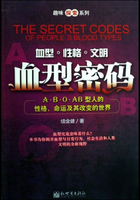1948年,波兰还没有提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为人们认为在人民民主国家,大力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时机还不成熟。这对贝塔来说十分有利,因为他的书与苏联作者采用的写作方法处于非常明显对立的地位。从莫斯科中央强加给作家的标准观点看,他的写作属于大逆不道,是犯罪。当然,他的作品选择的题材本身政治上无可非议:对希特勒主义兽行的描写,可算是非常符合中央愿望的,总的说来,波兰人对俄罗斯人的仇恨并不亚于对德国人的仇恨。描写德国人的暴虐行径,这样就把读者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德国人所犯的罪行上,从而达到使波兰民族作好“心理准备”即准备与苏联友好的情绪。的重要目的。因此,各种描写游击队战斗的书籍、描写盖世太保暴行和集中营大屠杀的书籍层出不穷,那时甚至容许出版正面反映波兰国家军在1939年与德军奋勇斗争的书籍。尽管波兰国家军保卫的是“贵族老爷”的波兰,而这个波兰一直是苏联的眼中钉肉中刺。但是政治上合乎规定的题材却并不能保护贝塔不受评论家们的攻击,假如评论家运用正统的标准评价贝塔作品的话:贝塔描写的集中营,是他本人看到的样子,而不是应该看到的样子。因此,他的一切过错也就出自这一点。在集中营应该看到什么?要列举出来并不难:1.囚犯们都应团结在一些秘密组织中;2.这些组织的领导者都应该是共产党员;3.书中涉及的所有俄罗斯囚犯,都必须是具有道德力量的代表,而且个个都应表现出英雄气概;4.要根据囚犯的政治观点对他们进行有所区别的描写。但贝塔的短篇小说却没有包含这些内容。显然,党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认为波兰作家还没有达到经受“转折”考验的程度。“转折”就意味着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此,许多党的批评家就给贝塔归纳出几条主要罪行:他们指责说,他的作品类似道德败坏的堕落文学即美国文学,因为其中表现了悲观主义;在他的作品中也没有任何“自觉斗争”的思想(以共产主义的名义进行斗争)。批评家提出的这些意见保持了劝说的腔调。贝塔那时还年轻,应该培养他具有成长为真正的共产党作家所需的素材。党认真地观察了他,发现在他身上蕴藏着非常有价值的罕见财宝:真实的仇恨。
贝塔是聪明的。当他熟悉了列宁-斯大林理论家的着作之后,他深信这就是他要寻找的东西。他心中的满腔仇恨就像奔腾的河水,在前进的道路上会冲毁一切。若让河水漫无目的地向前奔流则毫无用处,要怎样引导它流向正确的方向呢?办法很简单:就是在河上建一座水磨坊,让大河的水力来推动磨盘转。好一种解脱啊!有用的仇恨,就是要把仇恨用在为社会服务上。
贝塔仇恨的根源,与萨特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1905-1980),法国思想家、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大师。称之为“恶心”的东西是一样的,即对人的厌恶,人作为生理上的活物由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所决定,受到时间的毁灭性影响。人应跳出对自己的束缚,哪怕采取任何手段。假若贝塔是法国人,或许他会成为一个存在主义者。但也许这对他来说还不够。他带着轻蔑的微笑看待思想上的思辨,因为他在集中营里见过很多哲学家为争夺垃圾箱里的剩余食物彼此大打出手。人的思想没有任何意义,精明的花招和任何个体的自我欺骗都极易被揭穿,真正应该考虑的只是物质的运动。贝塔就像海绵吸水那样汲取辩证唯物主义。这个体系在物质方面满足了他描写残酷真相的需求,辩证方法使他在成为人上人的过程中有了一个飞跃,即把人类看作历史材料。
不久后,他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石头世界”可以说是作者情绪的象征——石头,意味着无情和赤裸裸。这本书由几篇非常短的短篇小说构成,它们几乎没有任何情节——只是叙述者所看到的东西的素描。贝塔善于运用对外部细节的描写来暗示整个人类的处境,他是个中高手。《石头世界》的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希特勒战败之后的中欧。因为,贝塔曾在德国的美国驻军基地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手中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书中出现了很多不同民族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其中有过去的希特勒分子和囚犯,有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德国资产阶级,有美国的士兵和军官。在有节制的文字下面,作者掩藏着对结出了希特勒主义果实的文明的极端厌恶。他画出了一个等号:基督教等于资本主义等于希特勒主义。可以说,他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在讲文明的终结。这本书的语调就是一种呐喊:“你们给我讲文化、宗教、道德——可是你们看看,这一切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对贝塔来说,就像对他的很多同行来说一样,希特勒统治时期就是欧洲实行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而与此同时,也是俄国革命在全世界获胜之时——人们当然仍需要进一步奋斗,但不管怎样,已经跨越了转折点。贝塔及他的所有同行,在战争结束初期发表的作品都包含着这类内容:人是无力与历史法则相抗衡的,甚至那些怀具最良好意愿的人,也会被**恐怖机器变成受到恐吓只关注保护自己生命的原始人。所以,阅读了这些书籍的读者都处于面临抉择的境地:要么选择自己已经亲身经历过的具有没落性质的旧文明,要么选择只有靠胜利的东方强权才能实现的新文明。这个强权获得了超乎人们想象力的成就: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一系列顺利情况的巧合,而是时代最高法则的反映(可是,俄罗斯及其制度在“二战”时曾差点遭到惨败)。
《石头世界》是贝塔的最后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他尝试运用一切在西方文学中认为是最有效的艺术手法:矜持、隐讽、冷嘲、戴上面具的愤怒等等。不久以后他就意识到,关心这些艺术手法完全是多余的。相反,他越是写得过火,越是受到赞扬。人们期待他的作品具有呐喊、狂热、明白易懂、有倾向性的特点。那些党员作家之间(贝塔那时已经入党了)展开了竞赛,看谁写的东西更能令人理解、更简单明了——这样一来,也就抹掉了文学和宣传之间的界限。贝塔在自己的小说中,直接加入了越来越多政论性的内容,他把自己的愤怒情绪都发泄在对资本主义道德堕落的攻击上。也就是攻击帝国范畴以外所发生的一切。例如,他曾引用报刊上的消息——马来西亚的斗争,或者印度的饥饿——在此基础上,他写作一种介于报道、新闻摄影和文章之间的东西。
1950年,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与他被盖世太保抓捕之前,在华沙从事活动的那个时期相比,他改变了许多。他身上已没有了从前的那种胆怯和虚假的谦卑。过去他走路时常常低垂着头,略显驼背,现在他是个身子挺得笔直的男子汉,脸上带着非常自信的表情:他变得干巴巴枯燥乏味,醉心于参加各项活动。以往腼腆的诗人,如今已经完全变成了政客。此时的他已是位显要的宣传家了,每星期他那辛辣的杂文都会出现在官方周刊上。他常常去东德,在那里搜集资料写报道。没有一个记者能像一位曾经有过无私的文学工作时期的作家那样杰出地为某种事业服务。贝塔在他自己那些恶毒攻击美国的文章中,就曾运用过去写作的全部经验和技巧。看着这位令人尊敬的虚无主义者的脸庞,我在想,任何形式的写作都有一个下坡路,作家通常得费多少力气,才能让自己不顺势往坡下滑去。促使他做出这一番努力的良心的要求就其实质来说是非理性的。不承认艺术是无私的的新信仰,摧毁了这种内心的指令。贝塔,尽管对人内心的一切绝对命令持怀疑态度,但在他那些反映集中营生活的短篇小说中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他既没有伪造任何东西,也没有刻意取悦任何人。后来,他在作品中播下了一颗政治种子,而这颗种子又像溶液一样结晶了。从此他所写的一切,都成了千篇一律和墨守成规的刻板式的东西。但是——我曾想——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很多杰出的作家也曾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政治激情,像斯威夫特、司汤达和托尔斯泰。甚至可以说,由于他们的政治激情,也就是说,由于作家希望告诉自己读者的某种重要寄语,他的作品获得了力量。那些批判自己所处时代之政治制度的伟大作家和贝塔这类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全然不因袭苟且,他们不顾自己所处的环境而进行活动,贝塔却是在将文字用笔写到纸上时,耳朵就已经伸出去想听到党内同志的掌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