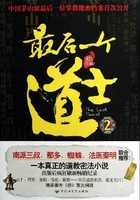袁度点头接过宝镜,细细端详,只见那镜直径一尺不到,镜面青莹耀日,背面盘着一条龙,鳞鬣爪角无一不全,栩栩如生,又刻有篆书铭文三十二字,团围成圈,辞曰:“盘龙盘龙,隐于镜中。分野有像,变化无穷。兴云吐雾,行雨生风。上清仙子,来献圣聪。”正中间有一方印,文字古怪不可识,大概就是邢幽清所说的天帝之印。又听得邢幽清继续道:“此镜的纯阳之气已被消耗,需要再吸纳数十年日光精华方能恢复。我在人间之事已毕,不敢再多滞留,这水心镜你代我送回峨嵋,交还于掌门罢。”又指着崔元之对袁度道:“我这个关门小弟子从小多难,父母早逝,我推算他一生坎坷,如今又将有场大变故。希望你能带他上峨嵋,也算是归了宗。”
崔元之忙道:“师父,我过几天就要去杭州读书了,才不去峨嵋呢。您说的大变故到底是什么啊?”
邢幽清点头叹道:“都是天意,你日后自会知晓。这把紫云剑我便正式传授于你,还有一件防身宝物,也一并给了你罢。你注定要归峨嵋,万不能违抗掌门的命令,我传你的养生之术切莫忘却,勤加修炼,当身安命延,最终亦能遨游上下,得成正果,也不枉我们师徒一场。”说完将紫云剑与一个红色的锦囊交给了崔元之,又对二人说道:“那分水墩下禁魔之所虽已破坏,但还需封印,以防侵蚀地气,切记切记!”话未说完,满室中忽然充满了异香,并隐隐有丝竹之声,邢幽清立刻现出法身,赤发蓝睛,身着鳞衣,五色光华四射,忽地转为如练白气,扶摇直上,渐渐转淡,再也看不见了。
崔元之见邢幽清飞升而去,想起这十多年来的情分,不觉有些伤感,含泪叩头相送。袁度轻轻将他扶起道:“前辈修成正果,崔兄弟应该高兴才是。”崔元之拭去眼角之泪,拱手道:“袁大哥,师父的事就多拜托了!”袁度忙回礼道:“不敢当,崔兄弟打算什么时候出发?”崔元之摇头道:“我家人尚在此处,况且我还有继续学业,怕不能同去峨嵋了。不过那分水墩我倒可以与你同去一探。”
袁度闻言微微颔首,暗道:“此子尚未觉悟,怕将来要大大地经历一番磨难了。”当下也不说破,只笑道:“那甚好,等我回去收拾收拾,那地穴阴气很盛,等正午再去较好。”
“也好,我偷偷溜出来一晚上,再不回去等爷爷起来就麻烦了。正中午我们便在分水墩上碰头吧。”说完,崔元之便一把推开殿门,日光正照射入内,映得满殿亮堂堂地。
袁度将玄天黄符、水心镜和谷璧等诸般宝物放入怀中,将张恩溥的桃木剑挂在腰上,又朝三尊石佛磕了个头,尽了礼数,这才出殿来,掩上殿门。忽听得山门口崔元之惊叫道:“袁大哥你看,天上这是什么?”袁度听言心头一动,抬头一张望,只见一个红球从西栅升起,直冲天空,忽地猛然下坠,轰的一声,腾起无数浓浓的黑烟,弥漫半空,隐隐有火光闪现。
“糟糕,西栅着火了!”崔元之焦急地叫道,那富源当铺就在西栅,此刻失火,怕殃及,心中十分担心,便急急跑了出去。
袁度也跟在他后面,两人先后穿过桑林,绕过转船湾,渡霅溪。一路上就听见水龙会“镗镗”的锣声报警,并四五台大水龙车,数十名青壮年抬了,急急往西栅老街而去。还未到西栅,便已觉得热气熏面,这火竟是极大。西栅入口处早已停当了四台水龙车,足足有腰粗的大木桶,里面连着两个唧筒,众人从旁边的霅溪中汲上水来,灌满了木桶,好几个壮汉不断地掀动杠杆,水就从唧筒中喷洒而出,如同一条条白龙一般,直朝着火苗喷去,顿时雾气弥漫,夹杂着浓烟,不可视物。又有数人,手执挠钩和斧头大锤等物,在一旁等候,只待火势蔓延过来,立刻拆房推墙,切断火源。
崔元之见火势猛烈,西栅深处的屋舍已尽数被焚毁,心中大是慌乱。“这里危险,两位快快离开!”几名龙兵(救火人)见到袁度他们,忙跑了过来,“镇上已经将植材学堂辟出来安置灾民,两位可以先去那边。”
袁度答应了,连拉带拽了拖着崔元之就往学堂那边而去。好在崔元之此刻也心神不定,仿佛无知无觉一般,只跟着袁度一路迤逦而来。到了学堂,只见到处都挤满了灾民,因那火来的突然,又十分猛烈,大概只有一半多一点的人逃了出来,都在议论这火来的奇怪。吃斋的老太太们指责年轻人们不信菩萨,结果惹菩萨怪罪了;媳妇们怪丈夫抽大烟,定是不小心火烛;男人们怪女人手脚笨,早上起来烧火做饭都会出事;年轻人们纷纷叫嚷着要找出火灾的源头,将那户人家打个半死。
崔元之四处寻找,希望能看到爷爷平安无事,可搜寻了半日,连一个仆人都未曾见到,心中更是一片冰冷。袁度见逃出来的那些人多半是住在西栅前端的镇民,更深处的怕是已经都是全家葬身在了火海之中,心中知道富源当铺定是不免。崔元之又找了片刻,颓然坐倒在地,眼中已是泪水汹涌,口中喃喃道:“爷爷,你不会有事的!一定不会有事的!”袁度见他伤心,也只好轻轻拍了拍崔元之,以示安慰。
又过了两个多时辰,龙兵来报,火已经灭了。灾民们急忙都回去检视情况。袁度与崔元之也跟着往西栅而来,眼前的景象令他们大吃一惊,整条西栅老街几乎被烧光,只余下片片焦土,段段残垣,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那些逃出来的和救火的镇民一个个灰头土脸,瘫坐于地,到处是叹气声。夹杂着小孩和妇女的哭声,呜咽声,乱成一团。
崔元之却不停步,一直就往西奔去。袁度怕他出事,忙跟了上去,沿着街跑了大约数十丈,看到崔元之跪倒在青石板上,那里原来是富源当铺,而如今也是墙倒梁塌,化成焦炭。袁度上前,见崔元之双眼发愣,呆呆地望着前面的废墟。袁度顺着他视线望去,那断壁之下有几块烧焦的残骸,看来崔老板已不幸遇难。
崔元之呆了一阵,站起身来,走过去,将身上的锦衣展开,铺在地上,然后一块一块将焦黑的骨殖捡起,包好,捧在怀中,其间未发一声,但也未掉一滴泪。袁度见他神情恍惚,知道是刺激太深的缘故,怕他郁积在胸,忙道:“崔兄弟切莫太过悲伤,令祖在天之灵恐怕也不愿见到你这样子啊。”崔元之闻言慢慢转过头来,望了袁度一眼,眼眶尽是赤红之色。
袁度怕他想不开,忙又道:“邢前辈飞升之前曾说过,将有场大变故,怕指的就是现在吧?既然是命中注定,你也别太难过了。”崔元之摇了摇头,低声道:“爷爷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如今他也离我而去。我……”
正说间,忽然袁度“咦”了一声,朝西面跑了过去,来到一所屋前,蹲了下来,似乎有所发现。崔元之也慢慢地跟了过去,只见那边围了不少龙兵,屋角蜷着一个人,被烧的焦黑,一手拿着一根长条形的黑炭棒,一手紧紧握着拳头。
袁度见那人手指上戴了一个扳指,被火熏得漆黑,弯下腰去擦了擦,露出了里面的蓝绿之色。
“这个掐丝珐琅扳指,镇上只有一个人有!”一个龙兵狠狠地盯着那人,口中狠狠地说道,“就是那个无恶不作的混混李二!居然丧尽天良,烧了一条街,害了这么多人,死有余辜!”
袁度却心中有疑,他将李二的尸骸翻转过来,面朝上,将嘴撬开,细细察视,见整个口腔内都是黑灰,乃是活活被烧死。他想了一会,说道:“纵火之人难道就没有想好躲避之策,会被烧死在这里?”
“一定是最近天气干燥,一点火星立刻就酿成大火,来不及逃跑,结果作法自毙!”龙兵们兀自恨恨不已。
袁度想了会,拉着崔元之走到角落无人处低声道:“李二没有那么大本事!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红球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而且此火必有古怪,火起之时已是天亮,居民肯定有足够时间逃出,岂会全都葬身火海,一个不剩?你看这封火墙也没有起作用。”
原来小镇的民居多为木结构,连成一片,一旦一家失火,极易蔓延,因此往往在每隔数家便砌一座高大的封火墙,用青石作基,砖泥夯实了,涂成白色,顶上再铺上黑瓦。若是邻家失火,只要火焰不超过封火墙,这边便无虞。而如今整条街都被烧遍了,封火墙别说是防火了,就连阻缓一下火焰的蔓延的作用都未曾见到。崔元之闻言,颤声道:“除非是各处同时起火,因此才会焚了整条街,怕这红球是有人用的邪术。若真是这样,我必将他揪出来碎尸万段!”
“这李二只是个替死鬼而已。究竟是何人要焚毁整条西栅?”袁度说道,“从西高桥起到植材学堂,一共是四百八十三户人家,这里都是寻常百姓,也不会得罪术派之人。若要真的报复,也只须焚一家一户,蔓延不多,如今却烧了一片,难道是为了掩盖什么?”
崔元之听得袁度如此说,咬牙道:“这也忒残忍了些。究竟是哪个邪魔妖人,竟害了这么多无辜之人!”袁度心中却道:“如今这镇上有术之人,除了我与崔兄弟以外,只有张氏兄弟了,难道是他们来此纵火不成?”又转念一想,“龙虎山应不会做如此伤天害理之事,纵火犯当另有其人。”
正想间,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西面传来:“阿弥陀佛!苍生有劫,善哉善哉!”袁度与崔元之循声望去,见一老僧身披袈裟,托钵站于西高桥上,口念佛号。龙兵中有认识的,忙叫道:“智南方丈,是福严寺的智南方丈!”纷纷上前拜见。智南缓缓走下桥来,他须眉皆白,身上的袈裟与缁衣上都缀满了补丁,脚上也是一双修修补补的芒鞋,虽然年纪很老,但看他走路的样子,步履轻盈,倒像是一个年轻人一般。
智南来到袁度面前,放下钵盂,合十行礼道:“原来杜施主也在此,贫僧失敬了。”袁度忙还礼道:“不敢欺瞒大师,晚辈实姓袁,单名一个‘度’字。去年冬天,要不是大师援手,晚辈早已经冻死在桑林中了。大师的恩德,晚辈没齿难忘。”
智南微微一笑,道:“袁施主不必谢老衲,佛门常开,普度众生,施主愿意来白莲寺,自然是与老衲有缘。见施主目露神光,不是寻常之人,敢问袁施主对此场火灾有何见解?”
“这场火的确有些蹊跷,个中缘由晚辈不甚清楚,更不敢臆测,不知大师有何高见呢?”袁度恭敬地说道。
智南望着地上李二的残骸,点头道:“寿夭因善恶,生死缘一念。这火虽不是他放的,却也是他放的。”龙兵们听如此说,都去回禀了龙头,按“李二纵火”为由上报县里。
崔元之却不明白为什么智南要如此说,刚想反驳,被袁度一把按住了,悄声在他耳边道:“妖人之事,切不可当众宣讲,以免民心动荡。”崔元之点了点头,便不再提了,想起爷爷之死,又是一阵伤心。
智南看了看崔元之,念了一声佛号,叹道:“崔施主也莫忧伤,令祖生前与我福严寺广结善缘,自会免堕苦海,往生极乐。我如今回白莲寺暂住,协助处理灾后事宜,两位施主若无事,今晚可以来找我,我有个故事想讲给两位听听。”
袁度行礼道:“那是一定,晚辈也有很多疑问要找大师,今晚自来拜访。”智南微微一笑,将钵盂拿起,对龙兵们说道:“我且去看看灾民们,有伤病者自好救治。”镇民都知道智南精通医理,时常云游四处,治病救人,当下欢拥而去。
崔元之从未听说过智南的名号,问袁度道:“这个智南大师是什么来历?”袁度道:“我来此十年,隐居桑林中,对大师的事迹也有所听闻,听闻他武功高强,能飞檐走壁,又有道法,能降妖捉鬼,又精通岐黄,能起死回生……”
“乖乖,都快是个神仙了。”崔元之惊道。袁度笑了笑道:“很多是民间的流传而已,未必是真的。不过大师慈悲心肠,每年冬天都会来白莲寺开设避寒所,活人无数,我也曾受过他的恩惠,至今感激不已。听大师说话,像是知道这场火的来由,待我晚上亲去问他。你无处去,可随我去桑林小屋一住。将你爷爷安葬了,也算是尽了孝道。那分水墩我们改日再去也不迟。”
崔元之见屋舍尽毁,也只得跟袁度回桑林小屋,想起前一日还是大商铺的少掌柜,如今却是孤苦伶仃,连这世上唯一的至亲之人都已离去,不由得更是伤心。袁度带着他在桑林中找了一个风水较好的位置,挖了一个坑,将崔老掌柜的遗骸安放好,崔元之一面哭着,一面用手将泥土推下掩埋。袁度又取了一大块桑木板,立在坟前,充作墓碑。崔元之咬破中指,用血在墓碑上书写了墓铭,下款写“孝孙崔元之泣立”,回到屋中又哭了一回,这才沉沉睡去。
袁度在一旁不住地叹息:这少年遭此大变,真是令人好生不忍,这一番磨难,怕是对修行有伤,唉,希望他能早日跳出来。当下也不离去,就在一旁陪着崔元之,只觉得倦意涌了上来,靠在稻草堆上便合眼而寐。
等到他醒来,已是哺时,金乌西坠,转头看见崔元之尚未醒来,想必是伤心过劳的缘故,也不忍叫他,见屋角的酒缸还在,里面的毒酒还剩下大半,如今已没有了宝蟾丸,这酒是再也喝不得了,只得忍痛重新封起,搬到屋后埋好。都忙活完毕,这才盘膝打坐炼气,将真元慢慢收拢于丹田,存想太极圆转如意之象,他在分水墩与石佛寺中两次损耗真元,功力已经大打折扣,正须慢慢调养一番。袁度调息了一个多时辰,方收了功,见一旁的崔元之已醒,正望着他。崔元之见袁度醒来,指着桌子道:“天色已晚,袁大哥先吃了饭吧。”袁度朝桌上望去,只见摆了一盘青菜,一盘南瓜与两碗白饭,不由叹道:“没想到你这个富贵人家的少爷也能下得了厨,烧得一手菜。”
崔元之低下头道:“爷爷说洗衣做饭,端茶送水,这些虽然是下人的粗活,但也是绝好的修行,富贵子弟更是要身体力行之,万不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成一废物。”想起爷爷昔日的教诲,心里又开始难过起来。袁度也怕他再乱想,忙道:“那我们快些用了饭,我也饿狠了。”
当下两人草草将饭吃完,收拾好了就往白莲寺而来。那白莲寺原为南北朝时名士沈约的祖产,捐出作为寺,名叫金莲塔院,后几经战乱被毁,于北宋崇宁年间方得重建。寺内又筑有一塔,名叫白莲塔,元末朱元璋与张士诚在此作战,白莲塔曾被毁坏,后世几经重建,直至咸丰庚申年间,太平军打破江南大营,李秀成克常州、苏州,逼近上海,此处正逢战场,白莲寺毁于战火,白莲塔也遭到极严重的损坏。到得同治七年,白莲塔终于轰然倒塌,成为一片废墟。如今的白莲寺是光绪年间重建的,其址在镇西西高桥之外,与西栅老街隔了一块浅浅的水塘,因而未曾被这次大火所蔓延到。
两人来到寺前,见山门紧闭,崔元之上前拍门,擂了半天,才有一老僧提着灯笼前来开门,袁度将来意说明,那老僧带着二人来到西厢的客房门前,说道:“智南大师还未回来,你们且在此等候吧。”说完自顾就去了。
崔元之自小调皮,镇上没有不曾去过的地方,对这白莲寺自然也十分熟悉。他指着北面道:“那里就是白莲塔的遗址了,也是师父布阵的一个星位,就在塔下的地宫里,如今都被盖住了,自然进不去,袁大哥可要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