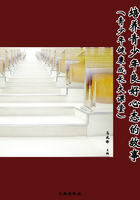我笑了,笑出了眼泪,涓涓如细流,“我会亲眼看着,一定会,看着你怎么死。”
我将赤裸的身子藏进温热的水里,只觉口中苦涩,笑声更大,痛苦绵长,“你死了,又能怎样?又能改变什么?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么不愿恨你,多么不愿你死?……可你为何要这样对我?你这样对我,你若不死,我该怎么活?”
我仰天凄厉大笑,“我该怎么活?你告诉我!”
“丫头……”谦益低唤我一句,再说不出话,只是静声看我,脸上是复杂变幻的表情。
须臾,他将我拉拽入怀,死紧的抱住,如同要将我揉进他的身体里,融为他的骨血,再也不能与他分开毫厘片刻。
“丫头,你我重新开始,好不好?我带你离开,你想要怎样我都答应,我们去过你想过的生活,逍遥自在。江山,权势,我……都可以……不要了。只要你……只要你肯回到我身边。”
我拼死挣开谦益的怀抱,嗤笑,“江山,权势,你会不要?别说笑话,一点儿也不好笑。”
“丫头。”谦益急切看我,“回到我身边,我们会幸福,相信我,我会让你成为世上最幸福的妻子……”
“是么?”我轻讽,“你几时也学会痴人说梦了?要我回到你身边,要我重做你妻子,除非我死!”
“丫头……”
“我说了,除非我死,否则我绝不会重回你身边!你给的所谓幸福,我根本不屑一顾。你明白吗?”
“丫头,别逼我!”谦益隐忍了怒火,一双眼眸亮出一道意味不明的光,言语冷寒,“倘若将我逼急了,后果不是你能承受!”
我倔强的抬头,毫不畏惧,“竹谦益,你怎不回头好好看看,从头到尾都是你在逼我!是你逼我接受你给的一切。在我已不是你的女人,已不爱你的时候,你还要一味的逼我回到你身边……”
“丫头。”谦益打断我,“你记住,你一日是我的女人,终生都将是我的女人,这是不会变的。你爱我一日,就必须爱我一生。除了重回我身边,你别无选择。”谦益用了最柔软温和的语调,可言语却狂肆至极,狷霸至极,简直不可理喻!
我冷笑连连,愤怒几让我的理智彻底崩溃,“我不妨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以前不爱,现在不爱,将来也不会爱!生生世世我都不爱你,也不会爱你。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即便我死也不会再回到你身边!”
不能怪我,是你伤我在先,是你伤我在先,“我一日也没爱过你!你根本不值得任何人爱。我的爱,施舍给猫狗,也不会给你。”
我激怒了谦益,他的脸一霎间像是乌云密布的昏暗天空。仿佛风扬黄沙,电闪雷鸣,黑云滚滚蔽日而来。他倏忽将我压至池壁,目透凶光。
良久,他轻颤着,又将几乎喷薄而出的怒火隐忍下去,放开我,轻声细语道:“丫头,别怪我!”
我如何能不怪你?我惨淡一笑,泪便止不住流淌。这一刻,你与我都像极了受伤的野兽,彼此的疼痛只能以挥舞尖锐的爪子相互伤害来发泄。我别过头,谦益,你我为何会走到这一步?后无退路,前是悬崖,再走一步就足以粉身碎骨。为何走到了绝境?
是你错,我错,还是我们都错了?
谦益冷笑,跃出了浴池,三两步走至门口,出门前又停住脚步,没有回头,只冷声道:“我会着人来伺候你。”
他开门离开,不带一个多余的动作。
门外,天仍未亮。阴雨暗霾,由这个凌晨延续到下一个凌晨。
一日复一日,朝暮相接,这场雨竟下了半月有余。恍似上天见怜,不忍以青天耀日为我心头的寥落伤痕雪上加霜。
半月以来,我日日在雨帘前弹奏,曲不成曲,调不成调。谦益日日在雨幕花树下长剑飞舞,招不成招,式不成式。我与他的心如两条平行的直线,不相交,日相望,空守着对方妥协。
夜幕降临,我与谦益,只剩下最原始的关系。他似乎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确定我还活着。我却在这种方式里,生不如死。他说,若恨,你就将我恨得刻骨铭心吧!天上地下,你也只能如此恨我一人。
这便是他说,我承受不了的后果么?他要我即使恨他也要恨得深刻,恨得唯一。
这就是他的霸道,他的无情。
我冷笑,“你其实是要折磨你自己,所以,你折磨我。”
他也笑,“这世上,除了你,已没什么能折磨我了。”
我沉下脸,依旧冷笑,道:“那好吧,我们便彼此折磨。看谁先妥协。只是——我伤自己便是伤你,你又如何能赢?”
我以为他无论如何赢不了,可接下来的日子,却一再证明,即便他赢不了,也绝不会输。
我在众多双眼睛的监视下行尸走肉般活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摔跤、磕碰几乎都成了奢望。只要我的身体稍稍轻晃,不是大批丫头奔涌而至,便是无数肉垫飞身而来。所有能伤害身体的东西都被人藏了起来。便连我随身携带的银针袋,也不翼而飞。
所有陪护我的人,每日都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的活着。
但凡我伤了自己,便会有人自我眼前消失,从此不再出现。我乏了,这样彼此折磨,原来我也赢不了。
我现今只想,解脱。
我开始日盼夜盼,盼潜光,盼哥,盼离耶,盼索里,甚至盼着想要我命的宜凌,盼着有人能将我从这生不如死的日子里解脱出去,就算死了,也好。我蓦然觉悟,原来,死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死不了的折磨。
又盼了半月,对于外界,我已全然无知。我慢慢改变,温热的心冷却下来,也如石头一般坚硬。我已变得不再是我了。对着铜镜,我时常看到一个双眼空洞而茫然的女人,披了身华贵光鲜的衣裳,有一张妆容精致的脸。
却偏偏像掉光了华丽羽毛的孔雀,说不出的恶心、丑陋,且失去了飞的能力,失去了她曾经拥有过的天空。她的灵魂,仿佛已一点一滴蒸发去了不知名的国度。
我知道,谦益看了我的模样心疼不已。我也知道他早做了某项决定,在他第一次强迫我之前就做了。只是他迟迟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他在等,等什么我不知道。他总问我,我是否恨死他了,就算死了,也不会忘了恨他?
我说我若死了,入了黄泉,只会记得我爱潜光,不会记得你。到那时,就算是恨,我也不会施舍给你。
他勉强一笑,不再说话。
终归,我还是怀孕了。
谦益知道消息的那夜,在凉亭里那般放肆的欢喜。
我异常平淡道:“你高兴太早了,他未必能出生。”
谦益登时敛笑,平缓跟我说道:“孩子若无事,磬儿便无事,孩子若出事,我会让她第一个填命。”
我茫然失神的望了谦益一眼,“女人生孩子的时候,如果难产,很难说她与孩子能不能活下来。有时候,大夫和稳婆决定不了,端看这女人是否愿意让自己与孩子活下来。”
谦益猛然一拳砸向石凳,石碎了一半,砸出了他一手血。他半跪着紧紧搂住我,“丫头,不要逼我。”
我僵直的坐着,单薄一笑,“如今你做的每件事,说的每句话,其实都是在逼我永永远远离开你。”
“丫头。”谦益将我搂得更紧,怕一松手,我就如梦幻泡影般消失不见。
“你爱我么?”我凄冷笑问,不知为何问了这个问题。
“爱……”
“你不爱我,你只爱你自己。”我冷清笑道:“你若爱我,何忍这般折磨我?我恨你,我好恨你。”
“恨吧,丫头。只要你能好过,你就拼命恨我吧。”他凄然而笑,“或许我本不该来淼水,不该来救你,更不该爱上你。”
许久之后,谦益苦笑接道:“丫头,我后悔了。后悔爱上你了。你害了我,害了我呀。我若仍只要那壮丽山河,只要那把紫玉九龙椅,该多好。为何我偏还要你的爱?对你,我若放得下便成佛,放不下就成魔,偏我又是天生魔障难除之人。”
我痴痴笑了,“因为你恨我,恨我不爱你了。你也恨潜光,恨他总与你争抢。你见不得我们好过,你见不得。”
“或许吧,谁又知道呢?我若知道,便也能解脱了。那该多好?”谦益放开我,站起身,负手亭前,月影杳然,我与他的人影却那般疏离。
“我想,你一定不知道。我第一次见你,便知你喜欢上我了。而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不知过了多久,谦益再度打破沉寂,幽然说道:“你慕容家,本不知天下三足,我占其一,受了墨阳王怂恿,当下急欲攀附太子。江东王府,实乃大洛富庶之地,算是财厚兵强。我虽未必希罕那份钱财兵力,但若能归我所用,绝不是坏事。然,如若不能归我所用,自是绝不能便宜了太子。”
我不说话,静静听谦益细述过往的事。
“那日,我力邀太子前去飘香酒楼观花魁比试,暗中又将消息透给了你的兄长。依慕容景夔的性子,他必会带你前往,意图博太子一个青眼。结果撞上了刺客行刺之事。当日那名杀手,并非‘空空公子’门人,实乃我所派遣。所去亦非行刺太子,只是助我演一出‘英雄救美’的好戏。果然,你第一眼便喜欢上我。”
“你不知道,其实每一个藩王府参选郡主的脾性喜好,我皆已一清二楚。你的喜好,我更反复琢磨了十余日。那日,我的装束,我衣衫上的纹饰,我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都经过了反复斟酌。丫头,你又怎逃得出我的手心?”
是啊,我当真没能逃出你的手心,一眼失心。怪只怪,你太可怕了,这事居然也能筹划到如斯境界?“只是即便那日我一眼爱上了你,也未必不会嫁给太子。”
“我自然有法子让你嫁不成太子。你若嫁了太子,依你的才情脾性与太子对你的喜爱,宜凌必是嫁不成了。她嫁不成,我的计划岂非泡汤?”
“所以我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你若真如传言中一般冰雪聪颖,我就捧你上天。若不是,我必踩你入地。而你无论是上天还是入地,都注定嫁不了太子了。父皇要的太子妃,既不能太聪颖,亦不能太庸碌。”
“那日,十一(青王)、十四(辰王)依我之计行事。你果是聪慧得紧,自视甚高如十一弟虽是气闷发窘,却也自认弗如。一切都在我的计划当中,宜凌亦如我所安排,表现中规中矩,不出彩亦不失色。唯一意外的是,你的一曲《百鸟朝凤》居然当真引出了百鸟朝拜的奇观异景……只此一曲,陡然便生出了许多变数。这才逼得我没办法,不得不兵行险招,乾坤殿前跪了一夜,求赐于你。”
原还有这些内情?难怪太子选妃才智比试之时,辰王与青王不仅对我“照顾有加”,还奇怪的都曾看向谦益。
“可是,既然你已早有了安排,又为何要使计令我爱上你?”你有计谋如此,就算我想嫁太子,也有心无力。
“两点原由。其一,这是最主要的原由。你见老七在先,与之相处数日却没爱上他。一百个女人中或许才出你这么一个,让我很是好奇。对你,我有强烈的征服欲望。其二,若用女人做棋子,让她爱上我,比我许诺任何有吸引力的条件都可靠。”
“可你后来并不相信我爱上了你。”
“是,很多时候,我连自己都不相信。”谦益毫不迟疑道。
一个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人,已不是可怜能够形容了,“问你个问题,你将宁毓儿当什么?”
“棋子。”
“但你为何没让她也爱上你?”
“因为我需要她爱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