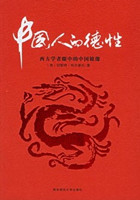康复中心的救护车好像早就埋伏在周围某个黑暗的角落里似的,很快就哇哇怪叫着开进了小区。
两名白大褂直接把温怡拉上了车。
10
这一次,温怡在康复中心一共待了十天。
在这十天里,她不但接受了以前那些针剂和药物治疗,还接受了电抽搐治疗。
程院长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像温怡这种兴奋躁动或情绪消极有自杀企图的病人极其有效。但这种治疗对病人的负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等到温怡被丈夫从康复中心接回去时,她的身体整整瘦了二十斤,一头美丽秀发也几乎掉光,其情形已经与她在疯人院里看到的那些真正的疯子毫无二致。
更糟糕的是,经过上次的跳楼闹剧,几乎所有认识或不认识她的人都知道她患了精神分裂症,都知道她进了精神病院。
无论她走到哪里,都会招来异样的目光。
丈夫沈天帆尽管在外人面前仍然一如既往地对她好,老婆前老婆后地叫得亲热,上楼下楼都牵着她扶着她,但在家里,当只有夫妻二人相对的时候,他脸上的厌恶与冷漠是遮掩不住的。
这也难怪,谁摊上一个疯子老婆,谁的心情都不会好到哪里去。
温怡在家休息了一个星期,才开始回学校上班。
三天之后,老校长在晚上的例行会议上委婉地宣布了学校解聘她的决定,理由是学生家长对学校聘请一个精神病人做老师意见很大。
开完“欢送会”,已经是晚上九点多,温怡走出校门的那一刹,止不住泪流满面。
忽然,她脸上显出一种少有的坚忍与狠毒,一边用力擦拭着眼睛里委屈的泪水,一边咬着牙说:“我不哭,是谁把我害成这样,我一定叫他加倍奉还。”
可是脸上的泪水却怎么也擦不干,她抬头一看,原来是下雨了,看来连老天爷都可怜她,在陪着她一起流泪呢。
雨是在不知不觉间下起来的,等温怡感觉到的时候,雨势已经很大了。
温怡没有骑摩托车,也没有带伞,她在雨中缓缓地挪动着脚步,浑身上下很快就被雨水淋透了。
秋风秋雨,冰凉彻骨,但她感觉到比自己淋了雨的身子更冷的,是她的心。
雨越下越大,路灯被细密的雨帘遮挡着包裹着,只能发出昏黄的淡淡的光芒。
大街上几乎见不到一个行人,一辆车。温怡孤零零一个人走在路上,路灯像一个可恶的魔术师,一会儿把她的影子拉长,一会儿把她的影子缩短。
当她走到学校围墙拐角处时,忽然听见身后有人踩踏着地上的积水,踢踢沓沓地走来。她回头看了一下,那是一个中等身材的路人,全身上下被一件黑色的雨衣包裹得严严实实,在她身后十几米远的地方不紧不慢地走着。
她看不清对方的脸,也分辨不出对方是男是女。
她唯一能清楚感受到的是对方的脚步声,那是一阵很奇怪的脚步声,听起来显得有些踉跄,杂乱无章,没有节奏,似乎与正常的行人走路的脚步有所不同。看来也是一个孤独的路人。
劲风夹着冷雨吹打过来,她浑身上下淋得像个落汤鸡,牙齿格格作响地打了个寒战,用手理一理被雨水粘在额头前的一缕头发,不同自主加快了脚步。
走过这条宽阔的大街,前面是一条窄小的巷子。说是巷子,其实并不准确。因为这里本来是一片有待开发的空地,不久前来了两个建筑队,将这里一分为二,在左右两边各搞了一个建筑工地,筑起了两道高高的围墙,围墙中间只留着一条宽不过两三米、长约四百余米的通道,看上去就像是一条深街小巷。
因为是临时建筑,所以路边并没安装路灯。在这风雨交加的夜晚,小巷显得比平时更加黑暗。
温怡走进小巷的时候,并没感觉到有什么异样。
当走到小巷深处时,忽然听到了一阵奇怪的脚步声,一阵凌乱的没有节奏的显得有点踉跄的脚步声。
她回头看了一下,小巷深深,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到。她柳眉微皱,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而身后的脚步也跟着加快了。
她这才意识到,原来那个雨衣人是在跟踪她。
她忽然想起上次也是在回家路上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在盯视她的情景,恐惧顿时像这无边的黑暗一样,将她紧紧的包裹住了。
抬头看一下,自己所处的位置是小巷正中间,距离前面隐约透出灯光的路口大约还有二百米远。
她咬咬牙,猛地加快脚步,往前跑去。
虽然小巷里漆黑一团,咫尺难辨,但她扶着围墙向前行,所以跑得很快。
身后的雨衣人听见她跑动的脚步声,意识到她已经觉察到了自己的企图,也马上加快脚步,急速向她追赶上来。
温怡越发证实了自己的想法,那家伙一定是冲着自己来的。甚至她大胆猜想,上次那个盯梢者说不定就是这个人。
她的身体本来尚未完全恢复,这一路奔跑,顿时气喘吁吁,心都快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了。但她不敢停步,她不知道那个人为什么要追踪她,但她知道对方绝没有好意。
一路狂奔,近了近了,出口就在前方几十米开外了,她手捂胸口,跑得更快。
黑暗中,她脚下忽然踢着一块砖头,向前一个趔趄,身子不由自主摔倒在地上。只不过几秒针时间,后面那人就已经大步追赶上来。
雨天路滑,温怡扑倒在地,向前滑出好远,来不及站起,就看见有一条黑影站在面前,挡住去路。
“你、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温怡浑身发抖,在泥地上向后爬行退却。
“我是谁?我是谁?”听声音,对方是个男人。
他喃喃地重复着温怡的问话,忽然嘿嘿傻笑起来,这笑声让温怡想起了疯人院的疯子,那些疯子的笑声不正是这个样子的吗?
“我是谁?嘿嘿,我是谁?你问我是谁,我问谁去?”雨衣人忽然说出这样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来。
“你、你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雨衣人仿佛自己不会讲话似的,总是重复着她的话,接着又是一阵嘿嘿傻笑,忽然又跺着脚号啕大哭起来。
风雨交加的夜晚,孤立无援的小巷,听着这傻子似的雨衣人狼嗥般的哭声,温怡心里既觉得恐怖,又觉得莫名其妙。
她战战兢兢以手撑地,刚要爬起身趁机夺路而逃,雨衣人的情绪忽然激动起来,狂呼道:“我要怎么样?你居然还问我要怎么样?你们抢走了我最心爱的女人,还把我害得这么惨,我要杀了你,我要把你们统统杀光,杀光……”
温怡在黑暗中看见他的手在裤腰带上摸了一下,手里便似乎多了一件什么东西,再一细辨,她不由得吓得魂飞魄散,他手里拿着的是一把匕首。
她意识到情况不妙,想强撑着爬起来逃走,但全身瘫软,双脚早已不听使唤,使不出半分力气。
“救命呀,救命呀——”
她绝望地大声呼救。但大雨就像一个巨大的消音器,声音刚从她嘴里吐出来,就被吸收得一干二净。
“我要把你们统统杀光,杀光……”
雨衣人像个丧失理智的杀人狂一样,挥舞着匕首,朝她身上狂刺过来。
温怡仿佛听到了尖利的凶器刺进自己身体的声音,一下,两下,三下……无数下……
她知道自己完了,以手撑地,拼尽全身之力朝那雨衣人撞去。
雨衣人被她的头撞在大腿上,一个踉跄,一屁股跌坐在泥地上,嘴里还在狂呼:“我要杀了你们这帮王八蛋,我要杀了你们这帮王八蛋……”翻身站起,一路狂奔而去。
温怡虚弱地倒在风雨中,倒在泥水里。
她感觉到自己身上被匕首刺中的地方发出钻心的疼痛,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裂开了一道道口子,血水汩汩流出,染红了她周围的路面。
她甚至还闻到了飘散在风雨中的那股浓浓的令人作呕的血腥味。
凶手凌乱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但死神的脚步却越逼越近。
她忍不住把头埋在泥水中,惊恐而绝望地哭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就在她感觉到自己身上的鲜血似乎快要流干的时候,她的手忽然碰到了自己掉在泥水中的小坤包。
包里有她的手机。
她心里一动,忙挣扎着掏出手机,拿小坤包挡住劈头盖脸砸来的雨水,用手机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
数分钟之后,沈天帆和温晴一路飞奔,来到小巷里,而在小巷的另一头,接到沈天帆的报警电话之后,一辆警车也闪着红灯急急地开了进来。
手电强光和警车的灯光,把黑暗的小巷照耀得异常明亮。
风雨渐小,温怡俯卧在水泥路面上,面容污秽,双目紧闭,已经昏迷过去。
但她身上的衣衫整整齐齐,全身上下并无一处伤痕一点血迹,一点也不像她刚才在电话中说的有人要杀她,她身中数刀,就快不行了。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倒更像是她在下班回家途中摔了一跤。
沈天帆似乎明白了什么,摇醒妻子之后,几乎就要忍不住一个耳光打过去,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温晴急忙扶起姐姐,用衣袖擦着她脸上的泥水。
“对不起,我妻子精神有问题,刚刚她可能出现了幻觉,幻想有人追杀她。对不起,害得你们白跑了一趟。”
沈天帆尴尬地向深夜里冒着风雨驱车赶来的警察赔着不是。
对方领头的正是上回那个拿电池喇叭喊话的眼镜警察,他用手电筒上下照了照温怡,见她浑身上下并无异常,确认是报假案之后,脸一下子就沉了下去。
他把沈天帆拉到一边说:“沈先生,不是我说你,上次跳楼的事就闹得够大的了,你还不看紧你太太。你看这大风大雨的,她一个电话就让我们兄弟几个白跑一趟……你太太精神有问题,你就赶紧找专家给鉴定一下,把她弄进精神病院去关起来,你也省事我们也省事,是不是?”
“是是,您说得对,回头我就给她作个鉴定。麻烦你们劳师动众白跑一趟,真是不好意思,这点小意思请兄弟们喝个茶。”
沈天帆心中有愧,掏出两张百元大钞,悄悄塞到眼镜警察手里。
11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温怡被第三次送进疯人院,她还是没搞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自己明明已经死了,为什么却还好好地活着?那个雨衣人明明用匕首刺中了她的身体,为什么她身上全无半点伤痕和血迹?
也许唯一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昨天晚上在那条黑暗的小巷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她的幻觉,也许她的精神真的出现了问题。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次她只在疯人院里待了一天,就被丈夫接了出来。
沈天帆把她接回家里,给她洗了澡换了衣服,然后亲自下厨,为她做了一桌可口的饭菜。
在饭桌上,沈天帆告诉她,程院长说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危险,建议他们请省精神病院的专家来看一下。
沈天帆接受了程院长的建议,昨天亲自开车去了一趟省城,花大价钱请了省城的数位专家。他们将于今天下午来青阳,会诊地点仍设在康复中心。
沈天帆一边给妻子碗里夹她喜欢吃的红烧鱼,一边观察她的反应。
温怡神情淡然,说:“省城专家的出场费不低吧?谢谢你了,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也许疯人院已成为温怡一生中最恐怖的记忆,本来从上午到吃过午饭,她的情绪一直都很稳定,人虽然显得有点木讷,但也没什么异常,但当下午沈天帆用小车将她载到康复中心,她一看到康复中心那鬼气阴森的大铁门时,整个人就变了,变得狂躁不安,变得歇斯底里,像一个山村泼妇似的躺在地上发疯耍泼,死活不肯进门。
康复中心的病人都趴在大铁门上,一边睁大眼睛看着一边指着她大叫疯子疯子。
好不容易请门口两个保安把她架进院子,按坐在从省城来的专家面前,会诊还没开始,她忽然双目大放异彩,从椅子上跳起来,自腰间掏出一把不知是什么时候藏在身上的菜刀,直往专家身上砍去。
几名从省城来的年过半百的老专家还没见过这样的阵式,吓得面无人色,连滚带爬,落荒而逃。
省城专家的会诊就这样不了了之,草草收场。
最后还是两名高个子保安员奋不顾身,冲上来夺下温怡手中的菜刀,制服了她这个“武疯子”。
沈天帆跟程院长商量一下,一个人开车走了,而温怡却被视为极度危险的“疯子杀手”,再一次留在了疯人院。
……
半个月后的一天傍晚,沈天帆准时开着那辆别克轿车下班回家,走到电梯门口,碰见了逛街回来正在那里等候他下班的温晴,两人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
电梯门开后,两人双双走入。
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沈天帆抚摸着温晴略微翘起的肚子,一脸怜爱地说:“你已是有身孕的人了,别整天到处乱跑。”
“家里太憋闷了,人家只是出来散散心嘛。”
温晴忽然抱住他,在他轮廓分明的脸上亲了一口。
沈天帆忙推开她说:“这是在电梯里,别乱来。”
“又没别人,怕什么嘛。”温晴调皮地朝他伸伸舌头,看见了他手里提着的东西,不由问,“你手里提的什么好东西?”
沈天帆心情舒畅地朝她笑笑说:“是一瓶红酒。”
温晴心有灵犀,脸上忽然现出兴奋的神色:“干吗买红酒回来,难道她的……”
沈天帆点点头说:“是的,她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书》已经下来了。”
“真的?结果怎么样?”温晴急忙问。
沈天帆伸手刮刮她的脸说:“这一下如你所愿了。所以我才买了红酒回来庆祝。”
“真的?那太好了……”温晴再一次抱住他,两片诱人的红唇直向他嘴巴上亲去。
沈天帆嗅着她身上那股迷人的气息,一时心旌摇荡,难以自持,两人紧紧相拥,便在这窄窄的电梯里热吻起来。
当电梯上升到五楼时,忽然叮的一声,停了下来。
两人面色酡红,匆忙分开。
进来的是一个佝偻着腰的驼背老头,大晴天的,却穿着一件黑雨衣,雨帽的帽檐遮去了大半边脸,也不见他按电梯的楼层键,进来便往电梯角落里钻。温晴没看清他的脸,只是厌恶地往外面挪了挪。
很快七楼就到了,沈天帆和温晴两人手牵着手,赶紧走了出来。
电梯里只剩下那个驼背老头,电梯停顿一下,又关上了门。
沈天帆也没多加留意,两人开门进屋,还没来得及锁上防盗门,温晴就忽然推了沈天帆一把。
沈天帆一个踉跄,靠在身后的墙壁上。温晴像一只饥饿的小老虎,樱桃小嘴一张,冲上去一把就吸吮住了他的舌头。
沈天帆的呼吸一下变得粗重起来,两人宛如久旱逢甘雨,等不及上床,就倒在柔软的地毯上,扯掉了对方身上的衣服……
“激战”结束时,两人不知怎么已经躺在了客厅里的沙发上。
温存良久,两个都觉得有些肚饿,沈天帆起身说:“咱们去做饭吧。”
温晴一边往自己优美白晳的胴体上罩着衣衫一边撒娇地说:“不嘛,你去做,我来给你打下手。”
沈天帆狡黠一笑说:“想要我给你做饭,那也不难,你得叫我一声好听的。”
温晴叫道:“姐夫。”
沈天帆不高兴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叫这两个字。”
温晴急忙改口说:“那我叫你天帆好了。”
沈天帆摇摇脑袋说:“还是不够动听。”
温晴明白他的心思,红着脸甜腻腻地叫了一声:“老公。”
沈天帆“哎”了一声,屁颠屁颠地跑进了厨房。
不一会,厨房里便响起一阵叮叮当当淘米做菜的声音。
温晴俨然是这间房子的女主人,冲了个凉,然后光着身子蹬上二楼,在卧室的衣柜里拿出一件质地柔软的睡衣披在身上,跑进厨房抽抽鼻子问:“老公,饭菜做好没有,我都快饿死了。”
沈天帆忙碌地说:“还有一个排骨汤没做好,你先把这几个菜端出去,准备开饭吧。”
温晴走到饭厅里,收拾餐桌,端上饭菜,摆上碗筷,把两把椅子摆放在餐桌的同一边,挨得近近的。
“对了,他最近坐骨神经痛。”她体贴的自语了一句,回头拿过一个沙发垫子,放在左边那张椅子上。然后又从消毒柜里拿出两只高脚玻璃杯,起开沈天帆晚上带回来的那瓶红酒,倒上两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