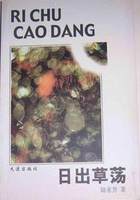风把他的头发吹起来。
黑子听到了一种声音,那声音像一股清澈的水流注入了他的心里。朱碧涛在芳草萋萋的河滩上吹响了萨克斯风,朱碧涛吹的是一曲《东方红》。
黑子异常激动,原来那怪模怪样的东西可以吹出这么动听的声音。黑子痴迷陶醉了。
他的心被乐曲声带向了远方。
他相信有一个地方会使他的心明亮起来,会使他远离苦难的曲柳村,远离忧伤的泡沫。
他痴痴地看着野河滩上吹曲的人。
他痴痴地听着那悠扬嘹亮的乐曲声。
曲柳村的寡妇丘玲娣的目光瞄准了飘逸洒脱的知识分子朱碧涛,朱碧涛每次游斗完,回到小泥屋,都会对着镜子梳头发。朱碧涛每天收工回来,也会对着镜子梳头发。他的头发永远梳理得有理有条。他的身上有种特殊的味道。丘玲娣见到朱碧涛,她的心就会莫名其妙地颤抖,朱碧涛身上的那种高贵的气质让她着迷。
深夜里,她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她想着朱碧涛的头发,想着那双睿智的眼睛,想着他的白脸,想着他长长的手和长长的腿,想着他身上散发出的饼干的香味。她的心荡漾着无边无际的春水。
朱碧涛是神是鬼?
她弄不清楚,她只想得到朱碧涛。
她想,只要和朱碧涛睡上一觉,哪怕给他五斗米她也愿意。五斗米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生命的不断延续,意味着不能用金钱来估价的珍宝。
徐娘半老的寡妇丘玲娣正对着中年下放右派朱碧涛想入非非的时候,她听到了有人摸进她房间的声响。她一激灵从床上坐起来,低声问道:“谁?”
“是我,玲娣。”那人涎皮赖脸地扑到了床上,来不及脱衣服就把她压在了身下。那是丘玲娣的老情人老猎头。
老猎头很粗鲁,迫不及待地剥光了丘玲娣的衣服。丘玲娣说:“老狗,你弄痛我了,你他妈的就不能轻点!”
老猎头气喘吁吁地说:“臭婆娘,你装什么蒜,你还不是喜欢我重一点,越粗越好嘛!等我没用了,你要我才怪呢!你是一只骚母狗,就要重重地弄你,你才舒服!”
丘玲娣气坏了,她想推开老猎头,但这壮年汉子的劲太大,压得紧,她根本无法推动他,只好躺在那里,由他去了。
丘玲娣在黑暗中被老猎头冲撞得晕晕乎乎的,不一会儿,她就发出了呻吟。
她用双手紧紧地箍住了老猎头的脖子,在他的耳边一遍一遍地舔着。
她心里突然有一个想法——自己身上的男人就是朱碧涛。
她在心里一遍遍地喊着朱碧涛的名字。
老猎头终于瘫软下去,丘玲娣这才从幻觉中清醒过来,有些无奈又有些愁绪。老猎头毕竟不是朱碧涛,他是一只老狗,臭烘烘的老狗。
丘玲娣恶狠狠地骂道:“老猎头,你是一只死狗!”
老猎头在黑暗中嘿嘿地笑了。
一天傍晚,社员们收工了。
朱碧涛扛着锄头走在最后面。丘玲娣也放慢了脚步。
朱碧涛躲着她,这些日子,朱碧涛发现丘玲娣老是用火辣辣的目光挑逗他。朱碧涛看丘玲娣放慢了脚步,自己也放慢了脚步。丘玲娣见他慢下来,走得就更慢了。
社员们都走远了,他们还在后面期期艾艾地走着。
不一会儿,丘玲娣见没人了,干脆就站在那里等朱碧涛。朱碧涛也停住了脚步。丘玲娣转过身,对右派说:“右派,你怎么不走了,怕我吃了你?”
朱碧涛笑了,笑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
丘玲娣怦然心动。
她的声音柔和起来,“右派,过来吧,咱们一起走,我不嫌弃你,我不怕,让他们把我也划成右派好了,我和你一起挨斗也无所谓。”
丘玲娣火辣辣大胆的话让朱碧涛有些感动。在曲柳村,朱碧涛坚信,没有一个女人敢这样和他说话。
他走了过去。
他们一前一后相隔不到两步地走着,要不是田埂窄,丘玲娣肯定会和他一起肩并肩走着。可就是这样,丘玲娣的心里也已经很满足了。她心里一阵狂喜,自己的愿望好像就要实现了。
“右派,你在城里有老婆吗?”丘玲娣赤裸裸地问。
朱碧涛说:“有,孩子都十岁了。”
丘玲娣又问:“你想她吗?”
朱碧涛说:“想,怎么会不想,人心都是肉长的。”
丘玲娣突然小声说:“你想做那种事吗?”
朱碧涛没有回答他。
他的脸红了。
丘寡妇说:“如果你想,晚上就到我家来,我等着你。”
说完,丘玲娣一阵碎步先走了。
因为马上就要到村口了,丘玲娣并不想让人看到她和一个大右派走在一起。
朱碧涛看着她的背影,怔在那里,若有所思。
夜深了,丘玲娣竖起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突然,传来一阵响动,她赶紧走出房门来到了院子中央,没有人。不一会儿,她听到屋顶传来几声猫叫。她骂了声:“该死的猫!”
她回到了屋里。
她左思右想,走进厨房,从一个陶盆里摸出两个鸡蛋,放进锅里,生火煮了起来。
鸡蛋煮熟了,朱碧涛还没有来。
鸡蛋都放凉了,朱碧涛还是没有来。
她心神不宁。
她把两个鸡蛋用一条小手帕包好,吹熄灯后溜出了门。
迷蒙月光下的乡村一片苍茫,夜色中浮动着一股暗香,那是桂花的香味,中秋又快临近了。
她摸到了朱碧涛的小泥屋的门前。
里面还亮着油灯,静悄悄的。透过门缝,丘玲娣看见朱碧涛穿着背心在看着一本砖头一样厚的书。
她想,他肯定害怕上她家,他也许是在小泥屋里等她来。她推了一下门,门紧插着。她推门时弄出了声响,朱碧涛问道:“门外是谁?”
丘玲娣小声说:“右派,是我!”
“你是谁?”朱碧涛沉着而冷静。
死鬼!丘玲娣在心里嗔骂了一声,她说:“右派,我是丘玲娣,快开门。”
朱碧涛还是沉着而冷静,“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你回去吧。”
假正经!丘玲娣心里又骂了一声,她又说:“右派,快开门,我真的有急事要找你,求求你了,右派,快开门吧!”
她心急如焚。
朱碧涛站起了身,走到门边,把门打开。
她一进门就把门关上,来不及插上门闩就扑进了右派朱碧涛的怀里,在他身上乱摸,呼吸着他身上散发出的饼干的气味。
“你……你干什么?”朱碧涛推开了疯狂的丘玲娣,她手中拿着的两个鸡蛋啪地掉在地上。
丘玲娣欲火中烧,满脸通红,胸脯起伏。
她又扑了过去,紧紧地抱住朱碧涛,嘴巴里吐出一串含糊不清又表达十分强烈的语言:“右派,我……我的心肝,我……我……要……要……和……和你睡……睡……”
朱碧涛一阵恶心。
他使劲推开了丘玲娣,怒吼了一声:“你给我滚出去!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不要你这廉价的同情和施舍!”
丘玲娣清醒过来!
她破口大骂:“你这不识好歹的东西。老娘送上门来,你也不要,你真是个死右派!”
朱碧涛气得发抖。
丘玲娣又换了一副脸孔,“死右派,我告诉你,你今晚要是和我睡,那就罢了。你要是不和我睡,我就和你没完。”
朱碧涛冷冷地说:“你想怎么样?”
丘玲娣冷笑了一声:“我就大声地喊,说你骗我到你屋里想强奸我!你看着办吧,就这两条路。”
朱碧涛说:“滚!你给我滚出去!”
丘玲娣真的叫了起来:“右派耍流氓强奸人啦——”
她还没喊完,一个人从门外撞了进来,他扑上去捂住了她的臭嘴,那人说:“丘玲娣,别人怕你耍泼,我可不怕你,你这个破鞋,无法无天,敢勾引右派,明天叫民兵营长把你绑了吊在树上饿你三天三夜,你他妈的就什么也喊不出来了!”
那人就是大队文书王松国。
丘玲娣一看不对劲,赶紧溜了。
“松国,多亏你给我解了围。”
“朱老师,委屈你了。”
“没什么,我什么风浪都经历过,还在乎什么?我不是说过,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嘛。来,学习吧,别耽误时间了。”
“唉!”
王松国从地上捡起了那手帕包着的两个鸡蛋,他打开来,递给朱碧涛:“朱老师,吃吧,不吃白不吃,送上门来的。”
朱碧涛笑了,“对,不吃白不吃。”
朱碧涛吹奏的萨克斯风让黑子着迷,他还把王春洪、李远新叫到了河堤上,在晨风中听那涤荡灵魂的声音。
三个少年坐在河堤上,看着朱碧涛入神地吹奏,他们的眼中闪烁着许多向往和陶醉。
黑子在那亮晶晶的乐曲中幻想自己长出了翅膀,飞向了远方。在音乐的指引下,黑子的灵魂在寻找可以栖息的地方。
中秋节那天,乡村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那天,人们没有看到朱碧涛瘦长的身影在乡间悠闲而落寞地晃动,乡村里的人听到了音乐声,那不是《东方红》,也不是《北京的金山上》,更不是《解放区的天》,而是他们从没有听过的一支乐曲。
美妙动人的乐曲吸引了黑子他们。
他们坐在小泥屋的门口听着那支朱碧涛不厌其烦地反复吹奏的曲子。
很久以后黑子才知道那是《欢乐颂》。
在曲柳村的苦难生活中,用萨克斯风吹奏出的《欢乐颂》别有一番风味。
就那样,朱碧涛在小屋里吹了一天一夜的萨克斯风。
夜深了。
文书王松国提了一壶酒,端了一盆红烧肉走进了朱碧涛的小泥屋。
他看到朱碧涛面前的小桌上放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有朱碧涛和一个漂亮的穿着列宁装的女人,还有一个长得十分灵秀的孩子。
朱碧涛没有理会王松国。
在这月光如银的夜里,朱碧涛的眼中闪烁着泪光,他一遍一遍地吹着《欢乐颂》。文书王松国静静地坐在他旁边,听他吹奏。
一直到天明。
那壶酒和那盘红烧肉动也没动。
中秋之后,下起了连绵不断的秋雨。
黑子每次路过朱碧涛的小泥屋,都担心泥屋会倒掉,但他无能为力。他想做些什么,又做不到,他的力量实在微弱。他发现泥墙的裂缝一天比一天大。有几次他鼓足了勇气走到朱碧涛的门前,想进去告诉他,但最终还是没能走进去。
夜里,雨下得很大。
黑子在哗哗的雨声中沉睡。
黑子听到了萨克斯风吹奏出的《欢乐颂》,他又长出了翅膀,在《欢乐颂》的指引下,飞向了一片阳光之地。在一个高高的山冈上,朱碧涛向他招着手,他朝朱碧涛飞了过去。朱碧涛穿着一身白色的中山服,镜片擦得雪亮,可以看到他晶莹的眼珠,朱碧涛的头上有一个黄色的光环。黑子向朱碧涛伸出手,突然,朱碧涛消失了。
黑子一个人在高高的山冈上,拼命地喊着朱碧涛的名字。
阳光消失了,黑暗无边无际地漫了上来,吞噬着黑子,一声轰的巨响。黑子从梦中惊醒过来。
是的,朱碧涛的小屋倒塌了,他被埋在下面,再也没有爬起来。
天一亮,许多人来到了那堆废墟上,他们七手八脚地扒开了泥土和房梁,从里面翻出了朱碧涛的尸体。很奇怪的是,黑子没看见那支萨克斯风。
后来,黑子和王春洪以及李远新在那废墟上翻了很多遍,也没有翻出那支萨克斯风。
王松国把朱碧涛埋葬了。
他把从废墟中翻出的书都抱回家去,一页一页地烤干,重新装订起来。后来,他和黑子一起考上了大学。他告诉黑子一个秘密,朱碧涛在春天的梅雨季节来到曲柳村又在秋天的雨季死去,这段时间里,朱碧涛教给了他许多知识,其中有俄语。这个生不逢时的初中生终于在右派朱碧涛的指引下,走向了上大学之路。不论他未来的命运如何,王松国至少成了一个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