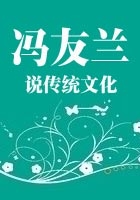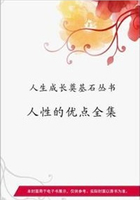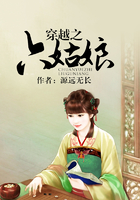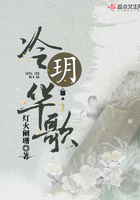自唐代以后《孝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长期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封建纲常起了很大作用。
一、《孝经》的章节结构
《孝经》主要有今文《孝经》和古文《孝经》两种版本。古文《孝经》在秦始皇焚书时,与其他儒典同遭厄运。今文《孝经》据传出自汉初,为河间人颜芝原所藏,因为是用通行的隶书字体书写,所以称为今文《孝经》。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孝经》一篇,十八章”,郑玄为之作注。全书以孔子与曾子之间的问答方式阐发孝治思想。第一章为开宗明义章,是全文的主旨。“夫孝,德之本也,孝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为天子章、诸侯章、卿大夫章、士章和庶人章,从社会人群的角度,分别规定了不同等级身份的人应该遵守的孝道标准。第七章为三才章,从天理、人性和社会的角度论述了孝的地位和作用,“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利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第八章为孝治章,以君王为陈述对象来讲如何以孝治天下。第九章为圣治章,讲圣人应该如何用孝道教化百姓。第十章为纪孝行章,讲孝子应如何孝敬父母。第十一章为五刑章,阐述了不孝为诸罪之首的观点。第十二章为广要道章,讲·“孝”为什么重要的道理。第十三章为广至德章,讲孝为什么是最高的德行。第十四章为广扬名章,讲孝道与扬名后世的关系。第十五章为谏诤章,讲父母有了过错的时候,孝子应该怎么办的问题。第十六章为感应章,讲孝道与神明的关系,孝道达到极点就可以感应神明。第十七章为事君章,讲孝子与事君的关系,孝子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第十八章为丧亲章,讲父母去世的时候孝子应该怎么办。
(郑玄(127年一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人。东汉儒家学者,中国著名经学家之一。郑玄先学今文经学,后习古文经学,网罗众家,通融为一,成7汉代最大的“通儒”,是两汉经学之集大成者。其经学成就及由其学术而形成的学派,后世称之为“郑学”、“通学”或“综合学派”。)
二、《孝经》的书题主旨
近代曾有人为《孝经》编制了一个“系统图”,比较简明地反映了《孝经》中的思想结构。比如,在《开宗明义章第一》中指出《孝经》的教育思想依据:“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将“孝”作为对人的道德教化的根据。《孝经》指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所谓“本”,即是指的“德行之本”,也就是指出“孝”为人之天性,为人性之本,行乎于内,父子之道也,行乎于外,君臣之义也。这种由“小我”之家向“大我”之国的“孝”道转换具有非常重要的行为典范作用,“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孝之于母,爱也;孝之于父,敬也。敬也是明君垂治天下的一贯要道:“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则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倡导孝道,使其周流天下,自然能“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石台孝经》碑刻于唐天宝四年(745年),题额由当时的太子李亨用篆书写成“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注孝经台”,碑石所刻内容即是“孝经”。碑文由唐玄宗李隆基为孝经作序和注释。因为整块碑石立于三层石台之上,所以取名《石台孝经》,也称“孝经台”。)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统治者的利用,《孝经》中许多具有进步意义和价值的内涵都被冲淡、曲解或被掩盖,因此有必要对其加以重新认识。孝是自然规律的体现,是人类行为的准则,是国家政治的根本。这是《孝经》的基本观点,也是全篇的基石。对于生活在家庭中的人来说,孝主要体现在事亲上,即对父母的奉养。那么怎样奉养才算孝呢?“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其亲。”(《纪孝行章》)“生事爱敬,死事哀戚。”(《丧亲章》)也就是要以爱敬之心奉养健在的父母,要以哀戚诚敬之心祭奉亡故的父母。子有爱敬之心,则父母乐;子有哀戚诚敬之心,则在天之灵安,这就是孝。
除了直接奉养父母以表爱敬之心外,作为个人,事亲者应具有怎样的修养和品行呢?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这是父母所给,不能损伤,即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开宗明义章》)其次,要立身行道,树立自己的德行,以求扬名天下后世、光耀父母来体现孝的深旨,是“孝之终也”。再次,对待外人,也要尊重,不能得罪。即“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天子章》)最后,要做到“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纪孝行章》)唯有这样才可以明哲保身,避免祸患。《孝经》告诫人们要珍惜生命,协调好自身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这也是对当时社会动荡、战乱频繁现实的一种含蓄反映。
有孝就有不孝。《孝经》倡导孝在一定意义上是针对不孝而言的。《孝经》所说的不孝主要包括:子对父只重视物质供养,而不重视亲情上的安慰,臣对君犯上作乱,骄横妄为,最终自身罹祸,即“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纪孝行章》)
《孝经》用辩证的观点,对孝的内涵做了更全面的阐发,使人对孝的理解更加深刻。人不仅是家庭之中的一部分,而且也是社会中的个体,社会中的孝如何体现呢?《孝经》针对不同地位、身份的人分别进行了论述。
(一)天子之孝
要对自己的亲人恪尽孝道,还要推而广之,以此教育人民,规范天下。正如《天子章》所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二)诸侯之孝
《孝经》说:“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诸侯章》)辅佐君王,保住社稷和人民才是诸侯之孝。
(三)卿大夫之孝
作为辅佐国君的卿大夫,孝的真谛完全体现在言和行上,言行俱遵行正道,“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这样才可以保住宗庙。(《卿大夫章》)
(四)士之孝
《士章》里说“忠顺不失,以事其上”要忠诚依顺,一心效主。《孝经》说:“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
(五)庶人之孝
要做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庶人章》)也就是说,按照春生冬藏的规律进行劳作,是庶人之孝。
这里,对“孝”的含义和内容的表达已经扩大到社会生活中,而非狭义的仅限于对父母之孝。这种以“孝”对社会生活的规范,用孝来解释和衡量的一切行为是一种服务于封建统治的政治手段。用孝来规范社会、规范政治生活、协调上下关系,以孝治国,是《孝经》所极力倡导的。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仁政”思想的变通。
通观《孝经》,谈治国之处甚多。尤其突出天子要以孝治国的观点,除《天子章》外,篇中多举先王、明王、圣人之例来加以佐证。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开宗明义章》)所谓“至德要道”就是孝。“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孝治章》)以孝治国的作用之大,于此可见一斑。“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圣治章》)这里的“本”,也仍然指孝。孝既然对治国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天子自当推而广之,“以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以身作则,遵行孝道,这是天经地义的,也因此可以“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感应章》)强调天子以孝治国,是对“教之所由生也”这一观点的具体阐述。后世对《孝经》中以孝治国和天子要遵行孝道的观点往往不予重视和突出强调,实际上是忽略了《孝经》的精髓和价值。
尊老爱幼、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良传统,“百善孝为先”,“人之行莫大于孝”这几句谚语就说明了华夏儿女对孝道的重视。《孝经》中说道:“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说明了每个人首先爱的是自己的父母——孝,然后爱自己的兄长——悌,推而广之即为“泛爱众,而亲仁”。由家庭伦理扩大到社会伦理,由道德范畴扩大到政治范畴,所以孝能治国,移孝以作忠,进而为民族尽大孝,因此也便有了“求忠臣于孝门”。
为了进一步论证孝道之神圣性、合理性和至高无上性‘,《孝经》又从天人关系上寻找理论根据,“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庙致敬,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这样,孝道就不仅有了人道的现实合理性,而且有了天道的神圣性和合理性。
三、对古代教育的影响
(一)《孝经》在汉代的突出地位
汉代推崇“以孝治天下”的治政思想,因此,《孝经》的价值在汉代被炒作得很火。汉朝历代皇帝均重视社会对《孝经》的习诵,甚至有几个皇帝亲自授过《孝经》。自惠帝后,汉代所有皇帝的谥号前都加一个“孝”字,以此来突出《孝经》在社会和国君治政过程中的地位。在教育领域里,文帝时始设《孝经》博士。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诏以《孝经》等未明,令举贤良文学高第。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郡县置学校,乡聚设庠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平帝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
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东汉光武年间(25年一57年),诏令虎贲士皆习《孝经》。明帝永平年间(58年一75年),诏令期门、羽林之士悉通《孝经》。《白虎通义》将它与《春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郑玄则把《孝经》作为“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认为《孝经》起到总汇六经的作用。从教育制度上来看,“汉制以《孝经》试士”,“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从教育实际上看,《孝经》成为初等教育的重要内容,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
(汉惠帝刘盈(前211年一前188年),西汉第二位皇帝(在位时间前195年一前188年)。他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次子,母亲吕雉,在位七年,死时年仅二十三岁,谥号“孝惠”,葬于安陵。)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孝经》
魏晋之时,三足鼎立,烽烟四起,战事频繁,但《孝经》里的思想依然为统治者所倡导。晋武帝泰始七年、惠帝元康元年,均由皇太子亲讲《孝经》两次。东晋元帝尤其重视《孝经》,曾作《孝经传》以教化世人。穆帝曾三次亲讲《孝经》,行释奠礼,并集群臣研究《孝经》的经义。南齐武帝永明元年(483年),诏令于国学之中置郑玄注《孝经》。梁武帝亲撰《孝经义疏》,并让昭明太子从小学习《孝经》。北朝诸代也特别重视《孝经》,并将《孝经》立于学官。
(三)隋唐君谕传《孝经》
隋唐时期,《孝经》也颁行天下。唐太宗认为,“行此(《孝经》)足以事父兄,为臣子。”唐玄宗曾两次亲自注批《孝经》,并于天宝三年“诏天下家藏《孝经》,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申劝课焉。”据《新唐书·百官志三》载,国子学设“五经博士各二人,正五品上。论语、孝经、尔雅,不立学官,附中经而已。”《孝经》《论语》和《老子》一并被列为旁经,这说明《孝经》和《老子》《论语》一样被视作国子监的必修课程和公共课程。而在科举考试中,《孝经》和《论语》也并列作为必试的科目。高宗仪凤三年甚至规定,《道德经》《孝经》并为上经,贡举都必须兼通。在后世;《道德经》曾屡停屡废,而《孝经》一直都是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
(唐玄宗李隆基(712年一756年),唐代的中兴君主,睿宗的第三子。因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亦称为明皇。英武有才略,开元时期文治武功鼎盛,世称为“开元之治”。后宠爱杨玉环,封其为贵妃。玄宗喜爱歌舞音乐,曾于梨园教歌舞,所以后世尊其为伶人之祖师爷,死后庙号玄宗。)
(四)宋代《孝经》归入“十三经”
在宋代,《孝经》受到统治者重视的程度也丝毫不比以往逊色。虽然在当时疑经之风盛行,许多学者也开始对《孝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产生了疑问。但宋太宗曾以御书《孝经》赐李至,认为“千文无足取,若有资于教化者,莫《孝经》若也。”宋真宗曾诏令邢爵撰《孝经义疏》,还亲撰《孝经》诗三章,命群臣赋和,并将《孝经》作为十三经之一,颁布发行,立为官定教材。宋代一朝宰相司马光也极推崇《孝经》,称“其文虽不多,而立身治国之道,尽在其中”。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也曾颁御书《孝经》于天下州学。
(五)金元借鉴《孝经》,用以治政
金元两代统治中原后,移风易俗,实行汉化,推行各种有益于统治的汉族制度,因此也对《孝经》颇为推崇,借以治政。金海陵王天德三年,以唐玄宗御注《孝经》授于学校。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以女真文《孝经》分赐护卫亲军。金章宗明吕元年,下诏以《孝经》作为科举考试内容。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诏令国子学以《孝经》为基础教育内容。元武宗时,以《孝经》译成蒙古文,诏令“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以其孝亲思想教化民众,维护统治。
(海陵王,名完颜亮(1122年一1161年),字元功。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孙,熙宗的表弟,他杀死熙宗后自立为帝。在位十三年,后被部将完颜元宜杀死。终年四十岁,葬于燕京郊外。)
(六)明清《孝经》纳入蒙学教材
《孝经》一直就是明清两代社学和蒙学的基本教材,明太祖极推崇《孝经》,清顺治帝又御注过《孝经》,康熙年间刊刻了“满汉合壁”《孝经》,雍正年间又刊行了《钦定翻译孝经》,并有御编《孝经集注》。但是,明清两代的官学和科举考试主要是以《四书》《五经》为内容,清代汉学考据学者如姚际恒等人经过详细考证,否定了《孝经》为孔子或孔子弟子所作,毫不客气地将《孝经》归入伪书之列。清代咸丰时曾诏令各省学政,科举考试都要加试《孝经》,但那已是昙花一现了。《孝经》渐渐淡出了官定教材之列,逐渐为统治者和当代的学者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