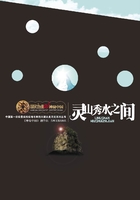文晓敏咿咿呀呀的冲到榻边,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狠狠的用胳膊肘撞了我一下。
我一个踉跄,向旁侧迈出了一步,才将将稳住了身形。
文夫人睁开眼睛,看了看眼前的情形,挣扎着要坐起身,说道:“你们别乱猜疑了,我相信不是桐雨。”
宁玉一向是文夫人的贴身丫鬟,自然忠心护主些,她瞟了我一眼,又看向文夫人,说:“可是夫人,这是有人要害你腹中的少爷,我们不得不防啊!”
文晓敏坐在文夫人的榻边,听了这话,也信服的点了点头。
文夫人皱了皱眉,呵斥道:“够了!在这上海滩,打我叶锦霞这个肚子主意的人绝对不少。可是,文家是什么地方,也不会随随便便让人算计了去。桐雨是我的儿媳妇,我绝对相信她,你们,还有什么异议?”
她的话在文家向来是最有分量的,她既然这么说,也没有人再敢说什么。
我望着文夫人端庄的侧脸,不禁暗暗的感激她这份坚定的信任。
文夫人摆了摆手,示意我们都下去,她要休息了。
我抿了抿嘴唇,打算回去理清楚繁杂的思绪,便转身回房了。
通过这一次的祸端,我也意识到了,我在文家时日尚短,空有个大少奶奶的头衔,既没有立威服众,也没有被文家人所真正接受。若是以后不想任人宰割,除了依附文夫人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办法。
不过,到底是谁要下毒害文夫人肚中的孩子呢?
为什么,还要嫁祸给我呢?
这次的风波还未平息,第二天下午,我收到了莱茵修女的捎来的急信。
阿九被车撞伤了。
我与阿九是从小在修道院一起长大的,情分比亲姐妹还要亲,听到她出了事,我自然十分焦急。
我一出文家大门,便叫了辆黄包车,急急向阿九所在的仁心医院赶去。
谁知道冤家路窄,撞伤了阿九的竟然是文浩源的车。
文浩源看见我,嘴角向上扬了扬,语气一如既往的轻佻:“大嫂,我们还真是有缘。”
我看着他这个样子,无端的想起他那天信誓旦旦说过的话,“我文浩源想要的东西,还没有什么是得不到的。”
该不会,阿九这次受伤,根本就不是意外吧?
我心下一惊,瞪着文浩源质问道:“你的车怎么会撞到阿九?难道说,你是故意的?”
文浩源挑了挑眉,吩咐自己的司机先去付急救费,继而才不紧不慢的回答我的疑问:“你想知道,就陪我喝杯咖啡吧。”
我皱了皱眉头。
上次在霍家老爷的寿宴上他那么一闹,本就有不少风言风语,此刻如果再不避嫌,只怕后患无穷。
文浩源见我犹疑,便无谓的耸了耸肩,问道:“还是说,阿九姑娘剩下的医药费,大嫂准备自己交上?”
威胁,明晃晃的威胁。
修道院那么穷,自然是无力支付。而我虽然是名义上的文家大少奶奶,但我手中的钱,不过是每月的正常开销,文夫人眼下又出了事,我怎么开口要一大笔医疗费呢?
我隔着玻璃看了看昏迷不醒的阿九,妥协了。
反正咖啡馆是公共场所,我们只要保持距离,想必也没什么要紧。
出入咖啡馆的女客,多半是洋人,要不就是身穿洋装的小姐贵妇,像我这样穿着旗袍进去的,倒真是很惹眼。
侍应生帮我拉开了座椅,我有些拘谨的坐了下来。
这时候的咖啡馆属于高档消费,我虽然在学堂里常听别人说起,却也没有机会来过。
文浩源见我笨手笨脚的样子,就帮我加了糖和奶,稍稍搅拌了一下。
我接过杯子,也没有心情品这西洋的饮料,直奔主题道:“我现在陪你来了,你可以告诉我,阿九为什么会受伤吗?”
文浩源从西装的口袋里掏出了一条丝帕,递到了我的面前。
我伸手接过,展开一看,不由的愣在了那里。
这不是,我离开修道院时,阿九想要给我的那块丝帕吗?
这上面的梧桐叶,我还清清楚楚的记得。帕子的一角,还沾了一丝新鲜的血迹,像是阿九受伤时溅上去的。
咖啡馆的角落里,一双眼睛恰好看到了我接过丝帕的这一幕。
我那时若是懂得保护自己,也不会有后来的遍体鳞伤。
我将那块丝帕攥在手心里,继续追问道:“这是阿九的贴身之物,怎么会在你手里?”
文浩源浅啜了一口杯中的咖啡,慢悠悠的答道:“我不知道,我的车正开在路上,她突然从路边冲出来,想要拦我的车,结果就被撞伤了。她迷迷糊糊的时候,手里还紧紧的抓着这手帕,叫着要拿给你。”
我微微一怔。
难道说,阿九是因为坚持想把我当时不肯要的手帕拿给我,又不知道文家的地址在哪里,只是见过我坐的文家轿车,这才在街上胡乱的拦轿车来找我?
那不是,害阿九受伤的罪魁祸首就是我吗?
我有些心疼的看了看手中的丝帕,不自觉的有些出神。
文浩源饶有兴味的观察着我的表情,似笑非笑的问我:“怎么?这个对你很重要?”
我回过神来,敛去了多余的表情,淡淡的笑笑,摇了摇头,答道:“也没什么要紧的。”我怕自己和文浩源单独相处的情景被有心人看见,所以准备离开,“好了,阿九就麻烦你治好她,我先走了。”
“等一下,”文浩源从风衣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盒,“我还有话要说。”他打开那精致的绒面小盒子,露出了里面一模一样的两对珍珠耳环。
我认得那耳环,是当时在霍家惹得霍小姐不高兴的那两对,没想到,文浩源还留在手里。
“你没把它们交给霍大小姐?”我记得自己是当中叮嘱过的。
文浩源淡淡的一笑,挑眉答道:“我了解伊方,她说不要的东西,是决不会再看一眼的。不过这不是重点,我想告诉你的是,这耳环是我在法国买办那里订制的,款式本应是独一无二的,我很奇怪你为什么会有一样的。我后来去问那个买办,才知道有人在我之后,用同样的图纸又去定制了一对。而那个订制的人,就是我的大伯母,你的婆婆。”
我瞳孔一缩,虽知道他是意有所指,却还是明知故问:“你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