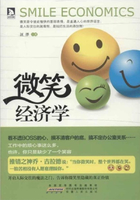1909年,中国自主修建的首条铁路沟通了北京与张家口;拔贡考试成为最后的晚餐;美国宣布退还庚子赔款浮溢部分的本利,用于中国教育。而对应在信阳,就是学生将离任知州张书绅团团包围。并非舍不得朝廷命官,而是舍不得他囊中的赃款。
张书绅离任之前,衙门里便已四处放风,重点官绅还收到过知州的名帖与便笺。名为辞行,实为索款。这种暗示只能奏效:各级地方官均不能擅离汛地,此乃祖宗成法。须等后任接印视事,你才能走人。故而欢送前任,同时也就是欢迎新任。这面子你还真不能伤。否则新官会有丰富联想。
知州的便笺该如何回复,李玉亭迟迟拿不定主意。土地纠纷的处理,完成于张书绅任上,李家为此花了不少银子。这几任知州,最让李家肉痛的,就是这张某人。也不是他贪腐得出奇,败坏得离谱,主要是把柄落在人家手里,你得躺在人家的砧板上数日子。而且他现在开炉房化铸银两,又须仰仗州衙。
在此之前,田赋一直是州府的主要收入,统称钱粮,也叫丁粮。按照本意应当缴纳皇粮,但早已折算为银钱。不过呈交的虽是银子,却依然口口相传,称为“封粮”。可以想见,上缴的只能是散碎银子,而且成色混杂,无法直接递解到省城藩库,必须就近凿验,再铸成银锭或者银锞,小元宝都未必合用。这工作最直接的联系是库大使,但真正主事的还是知州本人。主要领导一抓人事二抓财务,古今同理。
李玉亭最喜欢化铸小元宝。其紧要处在于火候适可而止,过犹不及。银液倒入模子,左右两摆,印成双翘,再一转,将中心转出螺纹,所谓翘边细纹。纹银一词,便由此而来。这个火候不强不弱,动作不大不小,否则便会影响元宝的成色与外观。
炉房里的空气肯定不会清爽,但李玉亭还是愿意驻足其间。每当有事需要决断,更是如此。事情越大他待的时间越长。炉房的一切管事说了算,俗称钱鬼子。和盛炉房的管事,是前户房书办项克敏。作为牌桌上的对手兼好友,他深受东家李玉亭信任,但夏先生对他却有所保留。决定之前,李玉亭曾经跟夏先生商量过,当时夏先生眉头一皱:“他是个美人肩,只怕不能担事。而且看他为人,貌似豪爽,实则机心,还是慎重些好。”
李玉亭到底还是没听夏先生的。项克敏毕竟出自州衙,人脉熟络。按照规矩,李玉亭虽是东家,但进了炉房也是只能看不许问。稍微多说两句,管事的便会摘下围腰顺手一扔,告辞走人。这是托人不疑疑人不托的讲究。李玉亭到炉房,总是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看学徒在赵明远的指点下化铸银两。若得空闲也开口说话,不过只问操作技术,不问往来账目。那天他在炉房内站立片刻,便有了准主意。回去之后让夏先生写封拜帖,同时赠送程仪两个大元宝。大元宝是书面用语,炉房称为“整宝”,标准重量是五十三两六钱。
夏先生刚刚出门,李立生突然派人前来,邀请李玉亭到教堂喝咖啡。那时李立生早已将大本营搬到城墙跟前,就在小南门附近。从李家到教堂,坐轿顶多十分钟。他知道李立生有话要说,喝咖啡只是托辞,去后一问,果然有事。李立生要到李家寨给新教徒施洗,他们都是李家的佃户,王本固一家,邓建勋一家,张瀹泉一家,共有十几户。这是个大场面,论理他们该来州城的教堂,但路途遥远,更兼拖家带口,委实不便。李立生善解人意,决定上门服务,想让李玉亭出席仪式。表面说是作为见证,其实还是想让他耳濡目染。
天晴得颇为亮堂。墙边的西式壁炉也同时酝酿着温暖,乳白的杯子将咖啡衬托得无比细腻。李玉亭用小匙子轻轻搅动咖啡,一阵浓香扑鼻,他的心情也因此而越发顺畅,便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闲聊一阵,李立生突然问道:“知州张书绅即将离任,据说他贪污有三四万两赃款,半数打着你们和盛炉房的戳记。这消息确切吗?”
李玉亭微微一愣:“你们不是不过问地方事务吗?”
“学生们说的。我只是询问,不是过问。”信阳的第一所小学和中学,都是李立生或曰教会创办的信义学校,时间是1901年,地点在南关的教堂旁边。那所中学还是女校。因教会最反对的都与女性有关:溺死女婴与缠足。信义学校的学生未必受洗入教,但要定期参加礼拜,接受宗教教育。彼时教士在多数国人心目中还近乎青面獠牙,而信义女校的要求尤其严格:绝对不能缠足;学校有权否决父母包办的婚姻。故而只有走投无路的穷人,才会为免费教育而冒险。如此一来,学生数量不可能多,李立生熟悉其中的每一个。
“为官一任,岂肯空手而归?钱肯定不少,至于具体数目,有多少是我们和盛炉房加工的,那还得问你。”
“什么意思?”
“只有上帝知道。”
二人哈哈一笑,随即散去。几天之后是黄道吉日,利于远行,张书绅要启程。不仅日期,连时辰都是查过定好的。夏先生早已吩咐备好车马,但李玉亭却迟迟没有动身。提醒两次,也未见动静。最后等李玉亭坐车抵达内城,却见城门已被人潮包围。各个学堂的学生不时呼喊口号,言之凿凿,要求张书绅清退赃款,干净离任。内城门口是第一道包围圈,州衙门前还有一道。各个学堂的学生都有。
官办的小学那时已有两所,一所是过去的申阳书院,位于城外西北的子贡祠。这是高等小学堂,相当于初中;另外一所在信阳州贡院,就是秀才和童生三年一次应试的考场,为两等小学堂,高初合办。豫南道创办的道立师范学堂,已经改成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其中的学生类似过去州学县学里的廪膳生员,因为有待遇:月供膳食银三两。权利与义务对等,他们毕业前五年须到各级学堂任教。当然并非义务劳动,报酬颇为可观:到优级师范和高等学堂任教,每月五十两;为中学和高等小学服务,也有三十两之多。
师范学堂的学生年龄大知识丰富,他们围堵知州不难理解,无法想象的是两所小学堂和信义中学的少数学生,竟也参与其中。人潮涌动群声喧哗,送行只能免掉。李玉亭转头驱车回家。夏先生得知情况,颇为惊讶:知州离任,不可能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丝云彩。那时的官服宽袍广袖涵养深厚,的确是大度能容。有无不是悬念,悬念只在于多少。如此准确的数目,谁能掌握?
最想知道答案的,既非局外人李玉亭,亦非当事人张书绅,而是新任知州祝鸿元。
学生包围州官,与造反何异?有清一代,对思想钳制尤深。生员秀才偶遇不平到文庙的孔子像跟前哭诉,所谓哭庙,本为常事,但虚弱的清廷都怕得要死,否则金圣叹也不会被江苏巡抚朱国治杀头。然而这一次,官府竟然毫无反应。确切地说,是无力反应。兵倒是不少,地方武装有巡检司,还有三班衙役;国家力量则有湖北新军第八镇的四十二标二营,他们驻防信阳,保护铁路。李立生对他们印象颇佳。他曾多次对李玉亭表达观感,声称中国军队正在开辟新纪元。
新任知州祝鸿元和道台大人,不是没有试图调兵,但新军拒不奉命。那两个可怜的父母官大概还不知道,新军就是革命力量的渊薮。因为其中有许多过去的生员秀才,文化程度高,容易接受革命思想。科举停办后,只有陆军小学还提供免费教育,并且另发补贴;而要进陆军小学,首先得有军籍,于是不少读书人顺水推舟,投笔从戎。革命党似乎并不避讳自己的革命思想,李玉亭曾经在某个酒馆与之巧遇,他们猜拳行令都是这个:“要革命啊,全福寿啊;要排满啊,三星照啊……”
学生围堵张书绅的首日下午,便有新军代表前来联络,自称名叫刘化欧,询问学生此举的用意。情由已明,他们非但不肯干涉,反倒暗中支持。后来才知道,刘化欧就是信阳新军中的文学社代表,革命党的核心分子。
兵丁非唯不来弹压,甚至连虚张声势都不肯。祝鸿元不敢激起民变,转而派出衙役,调查学生背景,寻找核心分子以及幕后推手。可查来查去,只能查出几个学生代表的名字,至于幕后主使,谁泄露出去的赃款数目,一时未能查得。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参与此事的不仅仅是学生。因为学生围城十多天,一直有饭铺供饭。八名马快是州府爪牙中的精锐,薪俸比普通皂隶高两倍,班头叫丁家骥。他们全部出动,可打听来打听去,也只查到送钱到饭铺订饭的是个乞丐,放下钱说明要求便转身离去,再无下文。
李玉亭的侄子,大李家的李世登,正就读于师范学堂,也是此事的组织者。当然,不是他策划的。他年龄较大,而且家资丰厚,为人又大方,难免财散人聚。运动一起,大家自觉不自觉地凡事都要问问他,他逐渐就成了组织者,所谓时势造英雄。李绪源闻听很是吃惊,多次敦促孙子迷途知返,但李世登始终无动于衷。某日李玉亭打从门前经过,正好碰见贤侄。虽然大伯李绪源竭力反对,估计父亲李绪宾也不会赞同,但李玉亭却暗怀同情。若非如此,怎对得起李立生口中的伟大变化?他冲侄子笑笑,看看周围没有官府的人,便飞快地掏出一把碎银子塞进世登手中:“好小子,买点油馍吃。记住啊,别说出去!”
李世登身披大褂,但还能看见操衣的领子。那虽是体育课的服装,但毕竟是师范学堂的专用装备,故而操衣加大褂成为他们的标准打扮,类似过去的秀才。看清来人,李世登赶紧按照见尊长的礼节,摘下眼镜答话。
这个态度让李玉亭很满意。他恨不得再掏出点钱,可惜囊中已无。财主出门,本不必带钱。李世登有点羞涩地冲叔叔笑笑,点点头把钱揣下,又下意识地提了提脚。他穿的是双新缎鞋,似乎不大合脚。没办法,这帮青皮后生都喜欢穿窄小一点的鞋子,既帅气又显得是仆人买的。一句话,既要革命,也要扮酷。
李玉亭盯着侄子,却依稀看见了自己的往昔。不同的是,他常常被人视为异端,而侄子没有。他笑着拍拍世登的肩膀:“傻小子,干吗非得穿恁小的鞋?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嘛。自己当心啊。”说完不等回话,便匆匆离去。
学生激情四溢,兵丁无动于衷,官员心急如焚。张书绅担心赃款有失,祝鸿元唯恐事态扩大。道台自然也不希望垮台。按照清律,处置不当激起民变,是要杀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