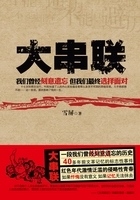1921年,退伍下士希特勒高喊革命,最终凭借出色的演说才能而攫取德国工人党的领导权。如果他没有失意退伍,而被提拔为军官;如果洪秀全科场得意,不知道历史会如何改写。还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参加共产党一大;军人蒋介石向钱鬼子靠拢,在上海开五家交易所炒股票;而真正的钱鬼子李玉亭,正试图从政:省议会换届选举,信阳要选出省议员,李玉亭有意小试牛刀。
当时的议会选举并非直选,类似如今的西方社会,也是代议制:先选出选举人,然后由选举人从候选人名单中选出议员。三十岁以上的成年男子,在选区住满一年,符合三项条件之一的,有选举权:任高等官吏;具有中学或者相当学历;有五千元以上不动产,或者商、工、实业资本。
被选举人的年龄要求三十五岁以上,其余资格也都更加严格:任高级官吏一年以上;具有高等专科以上或者相当学历;资产万元以上。
当时信阳最有影响的家族,出在张敬尧曾经驻扎过的五里店,姓陈,光绪皇帝曾经赐“祖孙翰林”匾一块。如今陈家有两个要害人物:弟弟陈善榘,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安福国会的众议院议员。当年徐树铮以“买鱼”为隐语,操纵总统选举,想来他也曾得实惠。不过直皖战争后国会解散,当时他已处于悬空状态;哥哥陈善同,光绪二十九年进士,现任河南省河防局长。一门两巨头,实力可见一斑。
这次信阳的选举,竞争主要在二陈之间展开。当然不是陈善榘与陈善同,而是陈善榘与陈其训。后者也有功名在身,是前清举人。李玉亭本来不想参与,但靳二哥鼓动他试试。反正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资格他都具备。
李玉亭在刘景向的辅佐下刚刚拉开架势参与竞选,立即如同噩梦初醒:忽一日清晨,和盛钱店大门上出现一张揭帖,声讨钱鬼子李玉亭。罪状有三:不修私德,青年纳妾;泄露机密,祸害主顾;交通军阀,糜烂地方。
纳妾虽然属实,但语气不免夸张;张书绅和心禅的确都有和盛炉房化铸的整宝,但并非炉房的过错。而且张书绅名下的还是赃款。交通军阀虽是全然诬陷,但内中却言之凿凿,声称民国九年的兵变,是受他的鼓动挑唆。他们预先知道内情,故而损失很小。
揭帖可不止这一张。整个信阳城内,不知凡几。李玉亭闻听,顿时眼绿。他真想号叫两声,可哪里能行。他这么一个要面子的人,如今被人一巴掌抽在脸上,却连还击的余地都没有,这比杀他都要难过。
当时刘景向刚刚发起成立信阳女子师范学校,以汝阳道内二十七县的屠宰捐为办学经费,他兼任校长。正常经费有着落,但还有前期投入,这其中有李玉亭的功劳,刘景向比谁都清楚。可你能怎么办?总不能随便拦住路人,就对人家声辩吧。他摇头苦笑道:“这张揭帖估计姓陈,但字号不定。玉亭兄,看来咱们不该掺和此事。”李玉亭的咬肌顿时团结起来:“那怎么能行?我要是没参加倒也罢了。就此退出,不等于应承了吗?”刘景向道:“狗咬你一口,你还能反咬回来?如今恶狗狂吠不止,除了后退不理,恐无良策。”
李玉亭坚决不肯答应。他是场面人,最要面子。如果谁想当这个议员,当面请他退出,那他完全可以愉快玉成。这样打黑枪,他宁死不从。回到家里,他立即找来邓东藩,让他调查此事。按照道理,警察对此最拿手,但邓东藩人虽然在巡缉营,过去的很多眼线还在。她老婆也有曾经的职业优势。李玉亭让夏先生先给邓东藩五十块钱:“这是弟兄们的跑腿费。等查出主使,另外看赏。”
因为这桩窝心事,李玉亭险些错过吴佩孚的精彩通电。上回是背面敷粉,明骂徐树铮暗指段祺瑞;这次则是隔山打牛,明嘲梁士诒,暗讽张作霖。
梁士诒曾经高中经济特科进士,而且还是一等一名,所谓状元。然而很不幸,这名字慈禧觉得碍眼,指斥为“梁头康尾”梁启超之梁,康有为之诒,因康有为也叫康祖诒。结果该科进士悉数罢去。民元以后,以铁路收益为基础组建交通银行,梁士诒曾为总经理,号称梁财神,是旧交通系的首脑。直皖战后,他经张作霖推荐而总理内阁。好端端的,吴玉帅因何要骂他?起因在于李玉亭特别关注的一个词语:铁路。
那一年列强召开华盛顿和会,鲁案被列入议题。鲁案的核心也是路案,胶济铁路的归属。梁士诒答应举借日款赎回路权,以国库券交付,用铁路抵押,十五年付清。不仅如此,还要让日本人做车务总管。此等条件,爱国将军岂能同意。他接二连三地发布通电,怒骂梁“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并仿《驱鳄鱼文》轰其下台:“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去位,吾国不乏爱国健儿,窃恐赵家楼之恶刑,复演于今日。公将有折足灭顶之凶矣,其勿悔也。”
一石激起千层浪,直系的督军纷纷跟进声援。张作霖虽然代为反驳,但心里有鬼,中气不足。大总统徐世昌接到通电,照例只可存档,却随手批示“交院”,转交梁士诒处理,等于直接表示不支持。无可奈何花落去,梁士诒黯然去职。
那时张作霖已与孙中山段祺瑞结成三角同盟,约期北伐,夹攻直系。然而此举非但无损于吴佩孚,反倒增添了他爱国将军的光辉。至少豫南四子观点如此:反皖是反日,反奉还是反日。直皖战后,吴佩孚给予战地农民每亩三元的补偿,此举,即便武王伐纣牧野之战时都未曾听说过。不仅如此,得胜之后理当分赃,曹锟本想要吴佩孚驻扎小站,就是当年袁世凯练兵的所在,以便控制京畿,但吴佩孚不肯。他对报界发表谈话,称京津为是非之地,决意到洛阳“专心练兵”,以师长身份“纠察天下”,“施德于民”。之所以属意洛阳,有两个原因:武王伐纣前曾在洛阳阅兵;洛阳的营房是袁世凯作为后方基地而修建的,设施很好,基本可以拎包入住。
这样的将军,谁能不支持?
蓬莱秀才骂得精彩,豫南四子看得痛快。痛快淋漓的李玉亭,并未意识到战争的风险在即。那天他突然收到靳云鹗的电报,要求借款五万使用一月,因该旅仍有一团驻在信阳。李玉亭还没来得及回电,彭团长便手持旅长电报前来叩门。他们过去便相熟,又有二哥开口,那还有啥好说的,立即办理。但这笔款项刚刚交付,次日上午饭沼便成为不速之客。
李家与饭沼素无往来。李家不做异地贸易,不须仰仗他的通关执照。上回在光山巧遇,算是他请饭沼吃了顿饭,回到信阳后,饭沼要回请,但李玉亭托故未去。饭沼宅院内有个高高的旗杆。那一天,旗杆上悬出一块布制的大鲤鱼,鱼身上满是黑丝纹。李玉亭一见,不觉心生酸楚。这家伙竟然又生了一个男孩儿。可是自己呢,多年过去依旧未能添丁。东洋鬼子哪儿来的如此运气?
那次收到请帖,李玉亭让夏先生送去红包,但并未赴宴。眼下这家伙不请自到,李玉亭未免心生嘀咕。从民国八年,也就是1919年的风潮之后,全国各地抵制日货已成潮流。既无私交又无生意往来,此刻突然出现,是不是夜猫子进宅?
还好,饭沼似乎无甚恶意,只送来一份《东北国民报》:“李先生,听说你喜欢读报,柜上订有不少报纸。但我可以肯定,这份报纸你没有读过。你看看吧。”
东北的报纸,李玉亭何从得见?接过来一瞧,是六天前出版的。六天时间从东北到信阳,可谓神速。饭沼好赖是个客人,李玉亭不好意思撇下人家兀自读报,只得与之虚与委蛇。而两人一开口,自然要谈政治。
“玉亭先生,我就是不明白,明明是贵国的内争,干吗总要扯上别的国家?”
“谁让他们总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贪心不足蛇吞象的。”
“咱们都是平民,也是朋友,不妨说得坦率些。我不明白贵国百姓为何总是看不起我们日本。国家不论大小,只论强弱;恰如黄金不论多少,只论成色。”
“个人论尊卑,更论贤与不肖;国家论强弱,更论有道无道。”
“我正想说这个问题。很多日本儒者都非常崇敬贵国的圣人之道。但他们认为,圣人之道已从贵国转移到日本。你们连续被异族统治,已经谈不上圣人之道。明清两朝都不配用大字,只有日本可用。这个大不指地域面积,而是有道。圣人之道在日本,故能称大日本。”
“可笑!贵国这种心态,无非像战国时期的列强看待东周,强仆凌弱主。”
“这话荒谬至极。明治以前,我国与贵国只有经济文化交流,从未建立正式的国与国关系。我国从未进入贵国的朝贡系统,何来主仆之说?《隋书》上记载有公元607年推古天皇致隋炀帝的国书,开头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次年隋朝遣使陪伴日本使者回国,我国史书记载有推古天皇答隋炀帝的国书,首句是: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日本虽小,对贵国一直持分庭抗礼的态度。唐朝曾派高仁表到我国答遣唐使之礼,太宗试图让我国进入朝贡系统,亦被舒明天皇拒绝。此事《新唐书》上有记载,说是争礼不平,空手而归。你们自己的史书,难道也未曾读过?”
“虽则如此,明朝的争贡之役,又作何解释?”
“当时我国处于战国时代,那是各个藩主的个人行为。就像现在贵国各地的军阀。”
“比如段合肥与张雨亭?”
“哈哈,这我可不知道。”
“无论如何,你们的文化总是来源于我国,相煎何急?”
“这我们从不否认。所以我们一贯认为,中日只是兄弟之争,是牙齿咬了舌头。英美俄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别老跟李立生打得火热。别忘了洪秀全闹长毛打的是什么旗号。”
“你这牙齿咬舌头,咬得可真是不小。台湾澎湖青岛旅大都咬去了。”
“多少都是兄弟之争。我们可以慢慢商量。你仔细读读这份报纸吧。对你有好处。”
饭沼走后,李玉亭仔细报纸,发现上面刊有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的声明,是对各地商号的警告:切勿站错队,为吴佩孚的军队提供贷款以及其他支持。李玉亭立即回过神来。当天傍晚,他订阅的《晨报》送到,上面也有张作霖的谈话,内容口气完全相同,都是恐吓。
李玉亭立即意识到战事迫在眉睫。他本能地感觉到了风险。并非为那五万块的贷款;出于对玉帅的坚决信任,他认为这是笔良好的风险投资。一旦玉帅平定天下,其政治价值远非经济价值可比。万一玉帅失利,也有二哥兜底。再说一万,即便亏掉,比比阵亡的官兵,还算是赚。都是反日爱国,他亏的不过是钱,人家亏的却是命。
风险与钱无关,主要是人身安全。上回烧香引出鬼来,一顿烟花导致他被劫持,不可不戒。县城挨着铁路,极易传染。奉系看似远在关外,谁知道信阳有无帮凶呢。饭沼就是隐喻。想到这里,他立即收拾好行李,准备回李家寨。
路过车站时,李玉亭随口问了问分红之事,胡传道闻听却只有皱眉:“恐怕有麻烦呢。据说交通部要重新审核资格。即便审核通过,今年也肯定不会分红。所有的收入,都由巡阅使署征用。”李玉亭大惑不解:“怎么还要重新审核资格?”胡传道说:“部里的台账丢失,找不到存根,担心有人冒领。”
后来才知道,东三省地域广阔,物产丰饶;内有理财能手王永江主持,外有日本倾力援助,1921年便已经实现财政盈余。张作霖财大气粗,备足三千万战费。直系无此条件,只能临阵磨枪:直隶实行亩捐,鄂省增加货税,同时截留京汉陇海两路收入,权充战费。具体情形,李玉亭当时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得匆匆上车回家。
李玉亭回家,也算是公私两便。这些年来,他一直没再生儿子,着急得要命。李立生带来的西医,号称照顾母婴最为专业,但这事儿李玉亭在他跟前自觉无法开口。那时他才意识到,白大褂不像白餐巾,的的确确是个厚重的隔膜。这些曲折,他只能就近求助于密友。胡泰运问了李玉亭夫妻的生辰八字,再分别把脉开好方剂,甚至还确定了同房的时间段。不在夜晚,而在午间。说是李玉亭长期抽烟打牌熬夜,阳气已然不足,而夜晚正是人们阳气最弱之时,不利于孕育。虽然听起来像是龚先生的腔调,但想想饭沼院中飘扬的黑色大鲤鱼,也只能宁信其有。
那时报上的电报战开始溅出火花。这边高声质问:“白山黑水之马贼,得以纵横一世,驰骋中原。国家之体面何在,国民之人格何存?”那边信誓旦旦,要“投鞭断长江之流,走马观洛阳之花”。随即北京榆关一带枪声四起炮声隆隆。还好,信阳尚可置身事外。
那天中午,李玉亭要跟柳媚行周公之礼。石膏大王的方剂中,大概有壮阳成分,比如淫羊藿之类,因而李玉亭颇得意趣。这些年来,柳媚开始薄施粉黛,形象丝毫未被时光的脚步践踏,长长的睫毛依旧如同蝴蝶翅膀微微扇动,令人心旌摇荡。此刻他刚刚进入状态,忽听寨外人声喧嚣,枪声四起。突然遭此惊吓,这可怜的钱鬼子就像倒霉的宋高宗,旋即泄精。那一刻,他满脑子都是上回带着阜阳口音的麻脸,以及他自来得手枪的冰凉枪口。
按照道理,寨子很大,根本不必如此惊慌。然而这回不比往常,枪声更加急迫,后来才知道是机关枪。而且不在大门方向,而在背后。那里有条小道通到山外。若非情况紧急,没有要害熟人,不会从那边过来。
后来才明白,祸事由于邓东藩的招引。从书写历史的角度出发,这也是直奉一战的分剧场。其根由则在于河南督军赵倜,莫名其妙地就成了奉系。曹锟是直鲁豫巡阅使,河南向由直系控制,可偏偏赵倜收了同出毅军的张作霖的三十万。起初慑于吴佩孚的威严,赵倜未敢轻动,后来获得不实战报,相信吴已战死,随即鼓足勇气,在开封宣布“武装中立”,以便挤上末班车的最后一个座位。
郑县率先打响。靳云鹗遭遇赵倜围攻,幸有冯玉祥东出潼关紧急援助。郑县要打,信阳自然也不能闲着。邓东藩所在的巡缉营奉命进攻武胜关,阻断直军后援。因主力悉数北上,此地驻军薄弱,仅有靳云鹗麾下的两个连,巡缉营因而占据上风。关键时刻,鄂军北上增援,两下夹击,巡缉营很快溃散。
战败后的巡缉营转头逃跑,直军则紧追不舍。大家都很在意枪杆子。朝哪里逃呢?县城肯定不能去。熟悉路径的邓东藩,带着营官阎曰仁直奔李家寨而来,希望暂时托庇于此。他们想跑,直军不干。若不尽快拿下,这些枪械败兵恐怕就要落入鄂军之手,这怎么能行。于是李家寨外顿成战场。
李玉亭顾不得培育后人,匆匆起身察看情况。得知内情,他哭笑不得,训斥邓东藩道:“你好糊涂!要枪你就给人家,何苦攥着不放?”邓东藩道:“营官说统领待他不错,不肯缴械。我当然要听营官的。”李玉亭道:“统领好营官好,能好得过孚威上将军吗?你们这些当兵的,就是报纸读得少,见识不够。任谁本事再大,能空手拉动火车,也打不过吴子玉呀。全国上下,哪里的舆论不支持他?”邓东藩满脸战败的晦气,嘟囔道:“我哪儿知道到底是谁跟着他呀。”
直军越来越近。李玉亭派人喊话,问清对面来人的确奉着吴佩孚的将令,是靳云鹗的部队,便由他接洽,巡缉营接受改编,归入中央陆军第十四师。因为靳云鹗已经晋升十四师中将师长。
从那以后,李玉亭再也未能威武挺拔,也再无脸面欣赏柳媚风姿绰约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