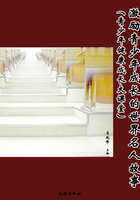结识将军,李玉亭当然情愿。军营设在车站东厢的空地上,以帐篷为主。进得营门双方见面,靳云鹗向冯玉祥介绍了李玉亭的情况,夸他够朋友讲义气,足以倚重。冯玉祥闻听连连点头:“这位李先生我认识。我刚到信阳时,劳动他们迎接,结果没接上,是吧?哈哈。既然荐青如此看重,那理当成为我们十六混成旅的朋友。来来来,请上座!”李玉亭谢座道:“冯将军神出鬼没,令人过目难忘。今后有事尽管吩咐,立德一定竭力效命。”冯玉祥对他们摆手笑道:“自打建军,大家一直说我们十六混成旅是花子军。你们今天来,真是有口福。要不我还真不知道如何招待你们。”靳云鹗道:“口福?焕章有何山珍海味?”冯玉祥哈哈笑道:“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吧,咱们上练兵场。”
那时雄壮之声已经隐约而来,撩拨起李玉亭的好奇。出去一看,冬天的大操场上早已热气腾腾。练瞄准的,习劈刺的,士兵们要么舞枪弄棒,要么徒手翻飞于单杠双杠之上,气息生动,直扑人面。沙场秋点兵的气氛,想来不过如此吧。李玉亭暗自感叹。走着走着,他发现刺杀的靶子都画着日军的图样,对冯因而更添好感。
大家一路走一路评论。靳云鹗频频点头。最外边是靶场,两支部队都在练习瞄准。冯玉祥随即吩咐他们比武:两支部队一人一枪,总环数最高者优胜。
两名军官早已跑来敬礼候命。其中一个面庞清瘦,眉毛在后半部直折下去,形成尖锐的角度,仿佛在告诉别人,他和他的部队都不是好欺负的;另外一个眼睛很大,右脸颊下有根长长的黑毛,嘴唇紧紧地抿成直线,刺刀一般。二人个子都不矮,敬礼之后便立正站好,纹丝不动。冯玉祥向大家介绍,前者是二营营长佟麟阁,字捷三,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因该营的三连连长告假,由连副带队训练,佟麟阁不放心,特来监督。后者则是学兵队第二连的连长张自忠,字荩忱,法政学堂出身,刚到军中不久。
冯玉祥点到谁的名字,谁便立正敬礼。需要比赛的,就是二营三连与学兵二连,或曰佟麟阁与张自忠。随着噼里啪啦的枪响,二人虽然竭力保持镇静,频频提醒士兵不要慌,注意平常训练的动作要领,可自己的眉眼之间,还是有一丝紧张,或曰一分期待。看来竞赛的结果他们都很看重。
最终近乎平局:学兵二连总环数优胜,可佟麟阁麾下有三人打了十环,二连的学兵只有一个十环。三连打出七个九环,但学兵二连足足有二十六个。
冯玉祥问问三连那三个射击冠军的情况,当即决定将两个年轻的补入学兵队,由队长冯治安分配。学兵队就是随营军校,里面的士兵都是军官苗子。冯玉祥点评一番,现场看赏。学兵二连每人一个肉包子,优胜的士兵也是如此。本来要奖励前五名,这样只能奖励三十七个。大家喊声“谢旅长赏”,抓起来便啃。冯玉祥道:“不要谢我,要谢就谢老沈!今天是他请客!”送来包子的那个老伙夫,闻听抓起围裙不断擦手,一边擦一边鞠躬,仿佛那上面沾有无数细菌,对他形成严重的困扰,以至于满面愧色。
看操完毕,回营吃饭。这等训练水准,让靳云鹗赞叹不已。冯玉祥笑道:“训练得再好,战斗力再强,上峰只是不爱啊。老是欠饷,我快成花子头了。”靳云鹗皱眉道:“我还不是一样欠饷,常年的寅吃卯粮。”冯玉祥道:“你终究有个好兄长。他多少能关照一些。我可不行,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反正是朝中无人。方便的时候,你也替我说说话嘛。”靳云鹗哼了一声:“别跟我提他!我素来瞧不上家兄的做派。臭官仔而已。”
回到司令部,七八个人围成一桌。冯玉祥道:“以往我跟警卫连一同吃饭。今天来了嘉宾,只得陪客。”随即招呼上饭。菜是一大盆,白菜炖豆腐;饭是二十个肉包子,热气腾腾,另外还有棒子面粥。冯玉祥递给靳云鹗一个大包子:“都不要客气,趁热吃吧。包子就这二十个,要是不够,就只能吃窝窝头了,那个管饱。吃吧,吃吧!”说着话自己抓一个就啃。
靳云鹗跟李玉亭对视一眼,都感觉诧异。这就是将军的饮食?不过邓建勋家的水平嘛。靳云鹗道:“焕章,你搞的什么鬼,这就是我们的口福?”冯玉祥一边嚼一边点头:“是啊。要不我们只能吃窝窝头。不信你到隔壁看看。”
旁边就是警卫连。靳云鹗放下包子过去一瞧,果然只有棒子面粥窝窝头,外加盐水煮黄豆。摆在最里边的有块窝窝头上印着红色的“勿忘国耻”字样,冯玉祥将之抄起,信手一掰,将“国耻”扔进嘴里嚼嚼,然后又夹了一粒黄豆:“不错,窝窝头没有沙子,黄豆的咸淡也合适。”靳云鹗道:“白菜炖豆腐加肉包子,你就这样待客?”冯玉祥道:“白菜炖豆腐是待客的菜,肉包子还不是。那真是你们的口福。”
原来头天夜里,冯玉祥带领警卫排长赵登禹查岗。路过伙房时,正好听见熬粥的伙夫老沈跟人发牢骚:“冯旅长真是贱骨头!人家旅长都吃肉包子,他偏偏要吃棒子面窝窝头。这样的旅长,有个啥当头?”冯玉祥略一停顿,接腔道:“我骨头贱当旅长,你骨头不贱,不还是个伙夫头?”老沈一听,扑腾一声跪下,挪出门外到冯玉祥跟前请罪。冯玉祥道:“老沈,你也是保定府的乡亲,跟随我多年。但是军有军规,你辱骂上官,我不能不罚。你说吧,认打还是认罚?”老沈连连磕头:“打怎么说,罚又怎么说?”冯玉祥道:“打是四十军棍,罚是两百个肉包子,要大个的。”老沈道:“我认罚,我认罚!”
靳云鹗闻听大笑摇头。冯玉祥道:“谁不知道肉包子好吃?可部队连续欠饷,大家连窝窝头都吃不饱,我能吃得下独食?”靳云鹗咬一口包子又喝口粥:“味道倒是不错。焕章,给我两根大葱一碟豆腐乳,这总可以吧?”冯玉祥道:“大烟我招待不起,大葱豆腐乳还可以。那我们就跟着远道而来的靳将军享点福吧。上!”
李玉亭陪靳云鹗上山督察工程。一路上,冯玉祥都是话题。靳云鹗也是穷苦出身,从小便替四姨放牛打杂度日,经常遭受表兄欺负。十六岁那年,他怒发冲冠,胖揍表兄一顿,带着母亲给的两吊钱和一身新衣服,赶到小站投军。别说单夹皮棉,一件换洗衣服随身行李都没有。入伍之初只能当副兵,没有枪,平常拿棍子训练,转移时棍子就是扁担。故而有个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只一条棍,我也没有枪。好在他力气大肯吃苦,很快转正并当了棚长(班长),直到如今。除了染有嗜好,他这个少将旅长的生活也算不得奢侈。他还是喜欢棒子面粥,大葱蘸酱就馒头。单饼卷鸡蛋就是美味。可尽管这样,尽管他对冯玉祥练兵那一套很是服气,但完全与士卒同吃同住,他也只能既感佩莫名,又敬谢不敏。窝窝头就盐水煮黄豆,他可是吃不下。
靳云鹗道:“焕章办事似嫌乖张,但为人带兵都不错。我把你介绍给他,本来是想让你们做做生意,现在看来不大现实。他的生意,你只怕做不成。”李玉亭摇摇头:“在商言商,做生意自然要图利,可看那样子,他的钱不是我能赚的。不过没有关系,多一个朋友,总是好的。他倒有点古之名将的风范。”
这么多兵来到信阳,各路商家可谓既喜且忧:忧虑他们侵扰地方,期待他们带来生意。那时各个部队都像宋朝的职业军人,家眷随营行动。十六混成旅的家眷不少,理当蕴含商机。瑞生福绸缎和老凤祥银楼,早早便预备好了货物。然而最终大家的忧虑全然消解,期待也全部落空。冯玉祥下令,即便正课时间以外,军官也不许穿皮裘皮鞋、绫罗绸缎。他自己带头着士兵服装,绑腿都不省略。虽然管不到家眷,无法直接命令她们,但他这么一引导,风气完全改变。
此举固然会影响李玉亭的布店,但瑞生福绸缎和老凤祥银楼受到的已非影响,而是冲击。怎么办呢?他们请求李玉亭出面。一来李玉亭是参议会副议长商会副会长,职责所在;二来呢,他不是好面子,也有面子嘛。靳旅长都称他八哥,冯旅长岂能不给点面子?
李玉亭表面淡然,但内心早已跃跃欲试:“按照规矩,本来也该回请他吃顿饭。饭桌上再说吧。成与不成,我不打包票。”
冯玉祥没有推辞,爽快地接了请帖。那时请客,得事先拟好菜单,送给主宾定夺,看看合不合口味心意。然而冯玉祥看都没看,便递还给夏先生:“请回去告诉李先生,不必如此。我的习惯,向来是一切从简,千万不要破费。”
这话让李玉亭很是为难。按照他的本意,摆顿西餐最风光,最有面子。胸前披着洁白的餐巾,碗碟反射着刀叉的光芒,保准是整个信阳城内的独一份儿。就像当年陪同段祺瑞。但是很明显,这不对冯玉祥的路子。尽管他是基督徒。还是鸡鸭鱼肉葱姜蒜、萝卜白菜松花蛋更好。而信阳招待贵客,无非是三八席面:八凉八热八大碗。大碗里有汤,但并非清汤寡水,内容其实颇为丰厚,不过下面煨着火钵,故而含水率略高。已入冬令,火钵不可或缺。
主宾重要,陪客的分量也要对等。道尹、县知事、李立生、刘景向,都是一时之选。至于李立生,他与冯玉祥是教友,所谓主内弟兄。可谁也想不到,菜肴如此丰盛,冯玉祥却视而不见,只吃他跟前的那两盘。大家不解其故,他解释道:“我老冯历来如此。按照道理,承蒙李先生盛情,我顺带吃点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军中粮饷两缺,士兵们每日不过以盐水煮黄豆充饥,我身为旅长,哪能吃得下如此佳肴?但是不来又有违盛情。我们驻军当地,少不得要烦劳各位,双方多加走动,是为增进军民感情。我是我的习惯,咱们互不干扰吧。”
尽管已有上次的经历铺垫,李玉亭依旧感觉突然。对付给面子讲面子的官长,他有经验;自己不讲面子也不给别人面子的官长,那可真是不好办。他赶紧端起酒杯接过话头,以便像清扫垃圾那样尽快地清扫尽沉默的尴尬:“冯将军安定常德,劳苦功高,举国皆知。大军莅申,秋毫无犯,百姓称颂。今日光临寒舍,李某蓬荜生辉。这不过是我们待客之常道,并没有特别为将军备办。尚望将军接受芹意。”
冯玉祥哈哈一笑:“李先生,老冯就念过一年三个月的私塾,你跟我说大白话就行。我自从掌兵,一直与士兵同吃同住。不信你问问他们俩。”
冯玉祥带着两个护兵。个子稍高的随即跨前一步:“冯旅长的确是这样,跟我们吃一样的伙食。”说完再退回原地。那时军队全都一天两餐。上午九点,下午四点。按照道理,这两个护兵应当早已饥肠辘辘,更兼火钵木炭通红菜碗香气四溢,必定更能勾动馋虫,可他们俩愣是目不斜视,挺身如松。
道尹不觉由衷赞叹:“冯将军果真驭兵有方。你看这两个护兵,那份精神,那份刚毅!”
冯玉祥微微一笑:“这个叫池峰城,这个叫吴化文,都是基督徒,也都是堪造之才。”
李立生接腔道:“既然如此,主内都是弟兄,无分彼此,不论高下。请他们也入席吧。”李玉亭和刘景向赶忙帮腔。道尹与县知事虽不情愿,但也无法开口。
池峰城和吴化文依旧像雕像一般站着。冯玉祥笑道:“主人诚意赐饭,你们还不赶紧谢过,坐下领赐?”
二人敬礼致谢,然后敬陪末座。李玉亭看看桌面,脑子一转,便有了主意:“冯将军,您在军中,每顿饭不过两个菜,如今我们十个人,平均每人也不过两盘菜。多余的几盘,就算招待贵客。你们为国作战,枪林弹雨,这点饭菜,并不过分呀。”
冯玉祥又是哈哈一笑:“这样也好!池峰城、吴化文,我可没本事给你们备办这么好的伙食,机不可失,你们赶紧敞开肚皮吃吧。”
二人的吃相孔武有力,恰似鸿门宴上的樊哙。大家相视而笑,气氛瞬间激活,李玉亭随即放下心来。原来这老冯并非不讲面子。即便当面不给面子,其实还是讲究面子,只不过讲究的面子更大更多。既然如此,那就好办。
关于军官的着装问题,冯玉祥没有松口:“军官必须艰苦朴素,方能真正奋勇为国。否则个个贪图享受,锦衣玉食,如何舍生忘死?而且我们已经欠饷十月,平常也只能开两成薪饷,实在没钱享受。至于家眷,我从未限制。她们并非军人,不必遵行军令。”
无论如何,气氛不错。尽管冯玉祥没有当面应允,但是不久之后,瑞生福绸缎店的老板在牌桌上告诉李玉亭,十六混成旅的副官过去买了块料子,说是团长鹿钟麟的母亲来队,冯旅长要赠送老人家礼物。从那以后,前来购物的家眷便逐渐增多。
眼看1920年即将过去,年关也紧随其后,正是算账的当口,李玉亭心里一直记挂着股权分红。正想着呢,忽一日凌晨,大地剧烈震动,将他从梦中惊醒。
受靳二哥的影响,李玉亭晨起的时间越来越晚。那日尚未天亮,他睡得正沉,忽觉头晕目眩,醒来时床铺依旧摇摆不停。有过上次的教训,他立刻意识到是地震,信手披上衣服光脚套进鞋子便朝外跑。早已入冬,鞋窝生冷如铁。好在跑到门口,地已恢复平静。稀疏的灯火相继点亮,人喧狗叫鸡鸣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拌和,像梦境一般真切。定了一定,李玉亭着人出去查看详情。天明之后消息传来,李家的房屋店铺均无大碍,但城墙的裂缝加大,已有局部倾塌之势。
几天之后,报纸发布消息,东西南北均有震感。北京“电灯摇动,令人头晕目眩”,上海“时钟停摆,悬灯摇晃”,广州“泥片掉落,客轮摇动”,不知源头何在。推测应该在陕甘一带,因为越往西破坏越剧烈:太原“房屋倒塌数间,人民微伤”,西安“门窗暴响,房摇墙塌,被毁房屋约有百户”,而古城兰州城内则一片惨象,三成房屋倒塌。
当时信阳已经很冷,甘肃的温度可想而知。灾民遭此横祸,无衣被遮身,无房屋蔽体,无饮食活命,而地方贫穷中央不稳,更兼连年征战,如何赈济?甘肃旅京人士在报上愤而抨击:“甘肃为国家征出租税之地方,甘肃人民即为国家负担之分子。今遭此亘古以来未有之浩劫,竟不能兼顾之余惠,既拂舆情,亦非人道。”
远在信阳的李玉亭,只有侥幸而已。侥幸灾祸地点不是信阳,或者说,信阳上回的地震烈度低。半月之后,眼看阳历年已过,已经步入民国十年的门槛,铁路方面依旧沉默不语,他便再度上门探问。胡传道领他找到站长,站长朝上面挂个电话,声称甘肃海原爆发强震,估计死亡人数超过二十万。根据交通部安排,京汉铁路决定今年不分红利,全部用于赈灾。
结果令人失望,但李玉亭没好意思失望。不但不能失望,回头还找来刘景向李立生等人商量,决定组织捐款,聊尽绵薄。动议发出后有人响应,但不够热烈,最终筹得一千余元,交与慈善会汇转出去。
这点钱不算多,李玉亭份额最大,五百。他有点不满意,但刘景向摇摇头道:“不必苛责。《中国民报》刊发《震灾救济委员会哀告书》,吴子玉、张雨亭、阎百川等军界人士纷纷签名,文化界的胡适之、蒋孟邻也积极参与。前大总统黎黄陂捐款一千,你猜猜冯焕章捐了多少?二十!信阳有此数目,已很难得,权且尽个心吧。左右都是杯水车薪。”
不能怪冯玉祥小气。
信阳城墙年久失修,又接连被上苍剧烈摇动两次,墙体开裂随处可见,有些地方已能爬出野狗。城厢的路况更是普遍欠佳,两边没有行道树。冯玉祥提出,部队出工地方出钱,由十六混成旅负责修墙铺路栽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