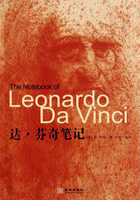除去这番搏斗的残迹,佛堂里似乎并无异样。我仔细检视每一处角落,遽见那幅壁悬《栖霞无尽图》已坠落在地。这是董北苑的名作。我平日很少进过这佛堂,这里惟有这画轴是我最为熟悉的物件,父亲曾说要将其挂到我的书房里。这画轴或许是在厮杀时被砍落,那挂绦已被砍断。我忽然看出这画轴有异样,这立轴的天杆上分明有三处剑痕!
这三处剑痕等距分布,像是刻意而作的记号。
这是父亲的剑痕么?这是父亲有意为之么?髹漆的斑竹轴杆,新砍出的剑痕。
我沿着剑痕掰动这轴杆。轴杆未及全断,竹管中便微露出一卷粗绢。
这轴杆的竹节已被打通,竹管里隐藏着一卷绢画。这是一卷高约尺许的画卷。画卷粗可盈握,似是一幅长卷。
这长卷并无轴头和扎带,火漆封印处却有父亲的手书:吾儿于大难之日启。
大难之日我开启了父亲留下的这手卷。这粗绢长卷色泽鲜焕,物景优雅,但却并无题署和钤印。自右向左看去,这长长的画心由屏风和床榻分隔成五段,而这画面正中是一个高挑的烛台,那烛火照亮画中的夜景。
这是一卷夜宴图。从卷首至卷尾,五段场景次第展开,五段画面中尽是歌舞欢饮的人物。我能辨认出其中的某些人,因我也曾在那欢宴的现场,我曾手执烛剪为那烛台剔火,那烛剪足有三尺长。我却不在这画上。这是韩熙载生前的最后一场夜宴。韩中书已于三年前辞世,而今理应尊称他为韩宰相了,国主早已追赠其为“平章事”。
韩熙载的形象出现在每一段画面中,他在这画卷中屡次更衣,而其最显著标志便是那美髯和高帽。即便在那脱衣露体的画面中,他也头戴这顶古怪的桶状垂缨帽。这是他自创的一种轻纱高顶帽,这款名为“韩君轻格”的纱帽一度成为朝臣和文士们的雅尚。韩熙载以俊迈之气,负不羁之才,既为文高学深的真名士,就自有一种孤标傲世的风度,而那些追步者总是难掩俗态,他们充其量不过是附庸风雅。画师逼真写实,以形传神,我却从中读出了另一种意蕴。这画卷散发着一种淡淡的哀愁。画中的韩熙载神色清寂,目光迟滞,似有难与人言的忧思,眉宇间也似有某种愤懑。他时而袒胸露腹,时而肃然凝立,时而心不在焉,时而却又有固执的注视。这是与欢宴场景极不谐和的神情。这夜宴的主人审音能舞,本是谈辩风生的一流人物,而在这画中却是如此的沉郁落寞。
那场夜宴的氛围确是既热闹又冷清,既缠绵又郁悒。这郁悒中似有某种苦闷和茫然。那位现场偷窥的画师,他在落笔作画时该是有着怎样的隐衷?这些画中人物除了父亲和韩大人,我最为熟悉的便是德明和尚了。画中的德明和尚身着僧袍,低首而立,他神色尴尬,双手似在鼓掌,但更像是在合掌,众人观舞,他却不看舞女。这显然不是出家人该光顾的场合。德明和尚曾为国主讲《楞严经》,他也是韩熙载的沙门好友。只因他曾在这妙因寺挂单,我一路骑马来到这里。我期盼德明和尚能予我以开解,或许他能告知我,父亲为何给我留下这画卷,这画卷又何以能保我家人免于大难。(编者注:妙因寺即今栖霞寺。)
万没想到,母亲大人对这画卷竟也一无所知!如此看来,父亲也对母亲保守了这秘密。我忽然对父亲生出几分陌生感。凛然可畏的父亲,沉默寡言的父亲,这沉默中究竟有着怎样的隐秘?父亲也会对国主隐藏自己的心事吗?
树树秋声,山山寒色。钟鼓低沉,黄叶翻旋。国主的銮舆正在下山,这是每年中秋例行的进香。国主造寺度僧无数,今年这个中秋他来的是这妙因寺。这妙因寺有父亲重建的舍利塔。国主下山之后即会回宫,他将在那深宫御花园与小周后赏月。而在皇宫近处的刑部大狱里,父亲正在等待国主定谳。
我在松篁苍苔间望着那辇道。那辇道上结驷连骑,烟尘漫卷。金瓜银钺护驾,龙凤旌旗飞扬。国主的辇驾正迤逦远去。我沿着栈道向下奔突数步,又爬上一棵老樟树。假若我有父亲那样的箭术,我会追上去射杀那个昏君么?我自忖并无这胆气,也无父亲那般力气。我骑马上山,这匹马也只是充作脚力而已。我恨自己手中没有猎弩。(编者注:弩亦弓属,其发矢用机括而不仗人力,瞄准、射远且力强。)父亲以一介武夫起家,虽有赫赫威名,他却不愿我走他的老路。在我出生时,他们也曾举办过桑弧蓬矢的射礼,他们也曾冀望我志在四方,可自从我初学骑马跌落马背,父亲就严禁我踏入那马球场。我记得那是我十二岁那年的秋天。金陵帝都豪门林立,林府独以球场闻名。那球场却是我不能涉足的禁地。父亲为我指定的去处是书房。我谨遵父命打消那些驰马逐猎的念想。父亲要我学做致君泽民的文臣,或是做一个食禄保生的循吏。我在太学里饱读那些修齐治平的古书,却至今仍是一个未经秋场的书生。我总难应付那些诗云子曰的考题,也惧怕那榜上无名的下场。不善骑射,不谙世事,不图上进,一个废物也似的文弱书生,而父亲却留我一卷大难时开启的图画。
藉此一卷图画救父亲脱难,我一时难以想出有何神机妙策。父亲是要我找人劫狱么?这画中惟一的武人即是父亲本人。父亲本可杀死那些禁兵逃走,既然他不曾反抗以致束手被擒,也就勿需等待别人劫狱。父亲是要我将这画卷献给国主么?我却知道国主早已见过这画卷。当年国主派顾闳中周文矩二位翰林待诏潜入韩府,他们窃窥默记那夜宴所见,而待他们将绘画进呈御览时,国主却只是付诸一笑,也并未将其作为珍品收藏。这手卷如何又成了父亲的藏品?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我俯瞰山下那滚滚东去的江水,又想到那些千百年间沉没其中的船舰和铁索。我遥望远方那座醉生梦死的都城,那城池之下又有多少湮灭已久的楼台和传说。我望着古诗人笔下这片迷蒙的烟雨,恍若看到那些古刹中有着无以计数的秘藏。父亲将画卷秘藏于这栖霞无尽的图轴里,而那位高僧就在这画卷中。
德明和尚淹通经藏,亦是有名的画僧。当年他初举进士,却因直言被黜,于是志绝仕进,一心学为浮屠。而今他却已不在这妙因寺,老住持说他回了青原山。我站在德明和尚曾经寄宿的僧寮前,又走到那井台前汲水。我畅饮半瓢清冽甘甜的井水,又在井底看见自己的身影。传说当年侯景败逃来到栖霞山,曾将劫得的天子御玺扔进了这井里,后来寺僧打捞出那宝玺,又将其献与陈武帝。这古寺有着太多的传说,这些传说与我无关。我只想尽早找到能予我以救助的人。德明和尚不在这寺里,我茫然地望着方丈门额的字匾,那是一块黑底白字的“虚白匾”度一切苦厄。
这额题是吏部尚书徐铉的书迹。古朴端厚,沉稳典雅,藏机变于谐和,有体方笔圆之妙。这寺院山门的额题亦是徐铉所书。徐铉的别业就在这栖霞山,就在这古木蓊郁的寺院西边,那是国主特赐的庄田。
徐尚书性情简淡,他是与韩熙载齐名的硕德鸿儒。江左文坛素有“韩徐”之并誉,即是指韩徐二人以文章书法名重于世。徐铉素与韩熙载交契深厚,他本人出仕较韩熙载略晚些,早年曾蒙韩熙载提携和赏识,而其女婿吴淑文章出众,亦深得韩熙载器重。韩熙载辞世后,这“韩徐”只剩一个徐铉,四方士人更视其为文坛泰斗。徐尚书也曾是韩府夜宴的常客,而他本人却不在这画卷中。那一夜我确也未曾看见他。此刻既已逃奔到这山上,我便决意要拜访他。徐尚书贵为翰林学士,也是国主的近侍,他或许能予我以支助。博学广识的徐尚书,他是本朝官员中少有的智者。当年他任御史大夫时,皇家北苑有大象暴毙,厨人寻胆不获,国主使问徐铉,徐铉说象胆当在前左足。厨人剖象前左足,果然就见胆在。徐铉说象胆随四时在足,今其毙在春季,故知在前左足。
太平有象。象为太平之象。人君南面而坐,以左为东,而东方为四时之春季。以徐铉之博识智慧,这画卷的隐秘弹指间当可破解。
徐尚书的别业宏丽而轩敞。我在那飞檐挑角的轿厅投上名帖,那门人却是面有难色,他说徐尚书不见生客。我掏出两块碎银,在那名帖上放一块,门人便说既然我是林公子,想必就不是生客,可他又说徐尚书偶感伤风,恐是难以见客。见他盯着我手中另一块碎银,我便说徐尚书若能接见,我身上还有更多。我将手中那块碎银也放在名帖上,门人便夸我“识事体”。
门人快步进去禀报,我在轿厅静待传唤。说来我确也不是生客。我与徐尚书有过一面之缘,那匆匆一面却给我以难忘的印象。何为儒雅,何为君子,徐尚书的仪态堪为天下第一楷模,但凡见过他的人都会与我有同感。
我正在回想着那次见面,就见门人哭丧着脸跑出来,他的胸前是湿漉漉的一片。徐尚书将茶汤泼在了他身上。
同为当世宿儒,韩熙载更为旷达,徐尚书却更为沉稳。彬彬儒雅的徐尚书怎会有如此粗鲁之举?门人说,是因他扰了徐尚书的棋局。
徐尚书是独步棋坛的国手,昔年某日他与国主对弈,宫人忽报大理寺卿萧俨求见。萧俨不耐久侯,便直闯宫掖,而见国主正沉迷棋局,他便挥手将那棋案掀翻在地。国主问他是想学魏征直谏么?萧俨说臣不及魏征,陛下亦非唐太宗!萧俨发怒是恐国主因弈棋而荒政,国主默然罢弈,不因萧俨犯颜而降罪,国主也因此而得美名。国主临御之初,也还有这从谏如流的说道。而今国将不国,国主便可随意将忠臣良将打入死狱。
那门人微笑着向我伸出一只手。
我又掏出一块碎银放在那手上。
朱栏回转,曲径通幽。徐尚书正独坐在山亭中,那山亭周围巧石玲珑,花木交映。徐尚书默坐不动,望去也似一块奇石。
我向徐尚书拜了四拜。即便是在太学拜孔,我也从未有过如此的虔敬。我对他以“大宗伯”相称。“大宗伯”本是对礼部尚书的敬称,徐铉昔日曾任礼部侍郎,此刻我以“大宗伯”相称,愈显出我对他的尊崇。我为扰了他的棋局而致歉。
徐尚书指间正拈着一枚黑子,他只是敷衍地回了半礼,却并不抬眼正视我,他只是盯着那棋枰发呆。亭中的石台即是棋枰,那些黑白棋子正摆布出一个残局。我并不为他的怠慢而介意,毕竟是我扰了他,而他正在为那残局入神。
我望着亭山上的题诗,那显然是徐尚书的篆书自题:崎石仍临水,披襟复挂冠。机心忘未得,棋局与鱼竿。
徐尚书以篆隶而闻名,尤好秦相李斯的小篆。这诗句的书法便是李斯体小篆。
“打劫!”徐尚书忽向棋枰落下黑子,就欢快地拍了几下手。我几乎就是棋盲,因此就不敢看那棋局,生怕他与我谈论。
“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惟消一局棋。棋有不走之走,不下之下。林公子也看出有何异样么?”
“学生无知,却不知这些文字有何奥妙……”
我望着棋枰上的那些文字,那纵横十九道线路各标有一字,我确是从未见过这样的棋盘。
“从来十九路,迷悟几多人。古谱失传,弈棋者每每不得要领。今有徐氏记谱,道术兼备,易识易记。顾我万年之后,或可以此而不朽。你瞧这棋谱,十九路各用一字标记,一天、二地、三才、四时、五行、六宫、七斗、八方、九州、十日……”
我已记不起自己是如何摆脱这话题,那或是因徐尚书觉察到我的心不在焉。徐尚书带我走过一片药圃,又穿过一道石拱门,又走过一条紫藤长廊。长廊的尽头是书斋。
这书斋明窗净几,古意盎然。间壁的博古架上玉轴牙签,典册琳琅,徐尚书奉诏编拓的四卷《升元法帖》就摆置在那明显处。徐尚书是驰名天下的书家。他的秦篆玉筋圆劲,气质高古,人说自大唐李阳冰之后篆法中绝,而今惟有徐铉能存其法,虽骨力稍欠,然已精熟奇绝。我囊中的“唐国通宝”上即有他的秦篆币文,而这书斋里也壁悬一轴仿李斯小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徐铉的小篆确是上乘妙品,其最妙绝之处在于,笔画中心总有一缕浓墨,至曲折处亦正当其中,无有偏侧。我无心观赏这些书画、钟鼎和碑帖,我只想说出父亲的不测祸事。
徐尚书不动声色地听我说完,我满心期待他予我以指点,而他却是缄口不语。我说他尝与韩熙载过从,不料他却对我说,那几年他已不再是韩府夜宴的常客。
韩熙载晚年为国主所猜忌,徐尚书与他疏远是为避嫌自保么?徐尚书把玩着手中的诗筒,他说自己与韩熙载并无宿嫌和私隙,然君子绝交不出恶言,他明里私下都不曾说过韩公的坏话。我不知他为何要对我这样说。
我拿出父亲留给我的《夜宴图》,徐尚书忽然眼睛一亮。我将画卷展现在这阔大的书案上。徐尚书俯身察看。当我说起父亲为我留画的情状时,他的眼中又闪过一丝亮光,但却紧接着就皱起眉头,他说自己也是爱莫能助。他说国事日非,残局已现。他说我毕竟青春年少,理应放眼长远。一番叹息之后,他又转回到那正在撰写的棋书上。那书案上亦有几册古人的棋书,一册是《围棋铭》,一册是《博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