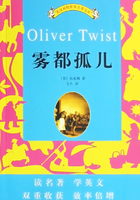禁兵们阵脚骤乱,有的立时倒地,有的掉头鼠窜。那高处的树冠中又有更密集的飞蝗石射出,那些逃窜者纷纷倒地。
隔着这样的距离,我听不见他们的喊叫声。小船漂在湖面上,申屠令坚并不急于近前。
我看见又一片飞石射向那所剩无几的逃窜者,又见那高处的树冠在风中起伏波荡,仿佛有人在波浪上舞蹈。
“耿大侠好个手段!”申屠令坚击掌称快。
那艘泊在码头的战船正欲逃离,就见一个黑球悠悠飞去。黑球自那树冠上飞出,像是一个拳头大的石块。那黑块飞向战船的桅巅,又坠落到甲板上。就听轰然一声巨响,战船登时炸腾起一团火焰。火焰立时吞没了桅帆,战船也变成了火船。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火器。我也从未听人谈说过。世间竟也有如此神奇的兵器!鸭梨大的那样一个黑团飞出,霹雳般一声巨响,霎时便将那帆船炸成了火船!
“好宝贝!”申屠令坚也是直呆呆望着那火船,一时难以回过神来。
虽是久经沙场的猛将,他却也不曾见过这般神器。沙场血战拼的是剑戟刀戈,凭的是勇猛和力气,那是硬碰硬的冷兵器。人头落地,如斩瓜切菜。寒光凛冽,虽也能砍击出火花,但却不会有这种轰然炸腾的火团。(编者注:史载宋灭南唐时即已使用火枪和火箭,而在更早时的唐哀宗天祐初年,即有“发机飞火”用于战事。原著者未经沙场,故其想象中似只有冷兵器的交战。)
那些禁兵尽皆毙命,岛上似已重归平静。申屠令坚猛劈一下手,艄公便奋力划桨。小船直奔那小岛。
战船烧得正旺,小船从旁穿过,我嗅到一股呛人的气味。这是硫磺和芒硝的气味。
晓风残月,岸柳烟波,眼前的湖岛已是静寂无声。透过那片风中摇荡的树丛,我望见耿先生那孤单的身影,此刻她正独坐在那岩石上饮茶。申屠令坚带我穿过禁军的尸体走近她。
耿先生起身怔怔地望着我,那眼神中有我从未见过的哀痛。她急急地向我奔来,又紧紧地抱住我。我在她的怀抱中失声恸哭。
当她看到这传国玉玺时,她的神情因震惊而有些木然。玺纽交五螭。底刻鸟虫篆。我望着她眼角的泪痕,望着她额头的汗珠,而她只是轻轻摩挲着宝玺上的火痕,一时间只是在喃喃低语:“史虚白,果真是史虚白……这就该是他的大事了。我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无怪乎李煜小儿要得到它,无怪乎林大人要舍命以保……”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始皇帝一统天下制传国玺,此乃万玺之王,镇国神器。为了夺取它,他们不惜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那火器好力道!就这么轰隆一声,兵船就炸了!”申屠令坚仰慕地望着耿先生。
“不过是炼丹,何期炼出这么个怪物。”耿先生的语气却是很淡然。
“好稀奇!那……那火器可有啥名目?”
“还能有啥名目?你也不妨是唤它作‘手雷’。”
耿先生默默斟茶,她双手端起瓷盏递给我,我看见她的手在微颤。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适才我已祭过林大人。”
我望着她前边草叶上的水珠,就默默地接过这青白色的茶盏,我将茶水缓缓洒在草地上,申屠令坚也洒下他手中那盏茶。
耿先生又为我们斟茶。申屠令坚忍不住又要落泪,便生气地说这茶盏太细作,就起身去往一旁的山泉边。
这山茶温润且有清香。耿先生只是默默地望着远处,眼神中依然有深沉的哀伤,神态也有几分疲惫。
“跟我说你是在哪儿找到的。”
“你果真是不知那藏处?”
我默默地掏出这诗签,这是我在栖霞山上抽到的诗签。她接过诗签疑惑地望着我。我指着签诗中的“梅”字,指着“梅”字的那个墨点。
“那山上有一棵梅树,就在那里你给了我这诗签。”
“荒诞……这却真是有些荒诞了……”
我从未见过她有如此疑惑的神情,她疑惑而探究地望着我。
“可你的诗签都是一样的诗句……”
“原本是有好些个签筒,出门时我只是随手取了这个,若是取了另一种,也就不是这意思了……”
我不由地望着她的手,望着她这修长的手指,就是这只手随意取了这一个签筒,这诗筒里有这首《寻春》诗,而于我而言,另一种诗签便预示着另一种遭际。
“这是你的命。”
我从未来过这湖中的荒岛,我没想到此处也有山岩和泉水。山泉自岩石上流下,那岩洞隐藏在一片茂密的草丛中。我惊异地望着那幽深的秘道。那是一个女阴状的洞口。(我在回忆中看见那个少年因窘迫而脸红,纵然是在那样一个悲伤欲绝的时刻,纵使我的心已然变得麻木而不觉。而今我将这般奇景形诸笔墨,绝非是要有意唐突后世读者的眼目,我只是想写出这自然天成的景致,只是想写出与耿先生最后相处的这场景。她说出门时随手取了这签筒,我却不知她的住处在哪里。我是冀望她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安身之所,虽然我至今也难以断定,那蓬莱仙岛上的秘洞会否就是她的栖身处。我记下她身后这个女阴洞,也要记下她眼前这个炼丹炉。)
这青铜丹炉实是一座三足圆鼎。鼎炉形体巨大,口沿处錾刻的兽纹粗犷狞厉,腹部的波纹却是流畅飘逸。底下的炭火烧得正旺,鼎盖处已是热气腾腾。一阵凉风吹过,我嗅到一缕肉香。
“我原以为你不会再害羞的……你须记着她。”
我愈加羞赧地低了头,幸好耿先生也只是点到为止。她轻轻摩挲玉玺的字迹,又将印身的烧痕示给我看。
“李从珂携宝自焚……这你可知是在哪?”
“洛阳。史虚白韩熙载彼时也在。”
她先是惊讶地看我一眼,又默默地再为我斟茶。这素雅的茶盏泛动着天青釉色,细嫩的芽尖在水中舒展漂沉。她拿过身边一个竹筒,这是一个新竹做成的竹笥,一端是原有的竹节,另一端是扣合的竹帽。这竹筒的表面依然是翠绿的原色,我能闻到这新竹的清香。
我在父亲的佛堂里找到了那画卷,那画卷隐藏在一节竹轴里。我不愿看到眼前这竹笥里藏有另一个画卷,我惟恐再见那“大难之日”的字样。
她默默地拔开竹笥的圆帽,这竹笥里确是有我不想见到的东西。
这是我献与国主的秘谶图。
我默默地展开这画卷。
我在史虚白墓中找到了前两幅,耿先生从宫中无尽藏院取出了第三幅。她已将这三幅图画裱合成一体,这是一轴完整的三联画:太平盛世;群小当政;天下大乱。
这“天下大乱”的一角已被内侍监烧毁。
“这数百号人就是为此而死么?”其实我是想让她对我说说这画卷的来历。
“天可怜见!他们只想毁掉它,不让天下人见识。但若天下人不解这道理,便会有更多人枉死。”耿先生卷起这秘图,将这图卷装回竹笥,又将竹笥递给我。“是以你应善自护持,择机将其流布四方,示与一切众生。林大人令你找到它,想必也是这番用意。”
“耿先生道力高深,做来自然是轻而易举……”
“你当老姑会长生不老么?就使再多活十年,不过三千六百天。只因你年少有根器,且经了这番磨砺,也就有了这指望。”
耿先生期待地望着我。她的目光从未有过如此的热切。
“好香!要我吃一顿才好!”申屠令坚闷声闷气地吼着离开那幽泉,此时他已饱饮了那泉水。
“我还想要你知晓,史虚白当年给周文矩看过这画卷,周文矩判定为顾恺之原迹。你别忘了,顾恺之也是这金陵人。”
“顾恺之是东晋时人,这就是有五百年的古画了……”
“陈后主也曾见过这秘画,给他看画的是江总。看罢他就跳进了胭脂井。”耿先生眯眼望向远处,那胭脂井其实就在不远处。
“周文矩画楼里有幅垂钓图,那鱼篓里也是有一卷图轴……如此说来,周文矩也该是知情者……”
“周文矩至死缄默,其实也算是盟友了。这谶图已成绝学,但也流传有序,周文矩也还考证出,顾恺之这画竟是前汉时的摹品。”
“韩公曾对我言及前汉张子房,那时我却不解其意。若说是摹品……”
“那祖本实是更远了,你再回推八百年……”
“回推八百年是……是周朝。姜子牙?”
“周文王梦得姜子牙,遂有八百年基业。姜子牙却又梦见了后来事。”
时光在疾速倒流,就在我的眼前,一如这奔流的云水,一如这倒卷的画轴,这画轴中有庙堂有山林,有朝臣有隐士,有一场又一场的杀身之祸,也有一个又一个的朝代兴亡。茫茫往代,渺渺来世。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道回旋,万古如斯。古老的秘密。先师们的绝学。他们所要传递的无非是这样一个自然的道理,一个被蒙蔽的道理。如此简朴,而又何其深切!
“那么,史虚白、韩熙载,还有我父亲,他们何以不将其公示于天下?这秘藏……”
“你说林将军拜的是哪尊佛?”
“弥勒佛。”
“这就是了。弥勒佛出世是为解救愚迷众生,可谁知还要等多久!”
“韩熙载也信弥勒佛,史虚白却是你们道家中人。”
“究竟根本,释道本也是一家。明道本为救世,叵耐人心沉沦,草民自贱,委实已是无药可救了。既是听天由命,也就不配见识这道理了。”
我望着那些禁兵的尸体,它们横七竖八蔓出我的视野。我想象着视野之外更多的尸体,一望无际的尸体,哀鸿遍野,饿殍满地。或死于劳役,或死于税赋,或死于苛政,或死于征伐。他们听天由命,而天命出自公门,出自廊庙。那是文臣们代拟的圣旨。翻云覆雨的圣旨。
世衰道丧,史虚白遁隐不仕,韩熙载意兴阑珊,士大夫苟且自谋。修齐治平,那内圣外王之道不过是为官家保天命,令草民顺天命。
这宝玺便是帝王们的天命,而这谶图势必危及这天命。而于享国者而言,这秘谶无异于洪水猛兽。他们必欲厉行禁绝,严防其流传。
这秘图就在我手上,就在这清新的竹笥里。
“不有人祸,必有天刑。地狱不空,真理不绝。那就拜托贤侄了,那将是你的成就。”耿先生淡眉轻舒,粲然一笑,“但愿你能待到那时日。”
我会待到那时日么?我望着她那深不可测的眼神,又望着手上的竹笥,内心隐隐感到一种迷惘和绝望。普天之下,众生芸芸,谁能读解这秘谶?
那时我只能想到申屠令坚这等人物。曾经的草莽豪杰,那时他却身为官家的使君。或许有朝一日他也能做皇帝,那时的他还能读懂这谶图么?
鼎炉高过头顶,申屠令坚只是闷闷地围着炉火转悠。肉香扑鼻,他却无法近前。他呆呆地舔着嘴唇,眼巴巴地望着这蒸腾的热气。
“刺史大人还是这般贪吃么?时光有限,就不会说些正事么?”
“这倒也有!”申屠令坚闷闷地挠挠头,“亏着有你这神通,这一船禁军全灭了,就不知带兵的是谁人!”
“紫微郎朱铣。”
耿先生淡然一笑,神情立时有些黯然,这黯然中有一丝感伤。
“那他人在哪里?”
耿先生缓缓抬起一只手,手指指向前方的鼎炉。
申屠令坚瞠目结舌。我也只是木然呆坐。耿先生的感伤转瞬即逝,她又旋即恢复了素常的淡漠。热气缭绕之中,这圆鼎的四方隐现出我熟知的神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玄武在北。城北的死者是朱铣。
我无力还原此前发生的那一幕。我也未能亲见那一幕。申屠令坚带我上岛,而当我见到耿先生时,所有的一切都已归于平静。那时耿先生正独自坐在树下饮茶。
那死者是她曾经的爱人。我不忍向耿先生发问。纵是如此,我仍能推断出朱紫薇上岛是为了那秘图。耿先生从内侍监手上夺走了那秘图,朱紫薇便带兵追到。他至死都以为国主欲得之物就是那秘图。
对于君主而言,朱紫薇实为不世出的忠臣。他必欲毁掉这秘图,以免其成为妖贼反乱的借口。而为尽忠职守,他不惜向自己的旧好下手。(那日护送我离去时,申屠令坚回望湖洲显得很悲悒。那时申屠令坚对我说,朱铣与耿先生绝交是因耿先生与妖贼有牵连。所谓妖贼,实为民间一些个劫富济贫的义士。他们依草附水,夜聚晓散,他们也曾在这蓬莱洲密谋起事。只因有朱铣的密报,那些团伙迅即被剿灭,而朱铣也以此晋升为紫微郎。)
有虔秉钺,如火烈烈。那纯阴之火已将朱紫薇化为乌有。那传说中的秘情也将化作永远的秘密。那仿佛是属于一个更古远年代的秘情,那情景一如这青铜古鼎上的兽纹,何其狞厉,而又何其神秘。
我无端地想象着他们最后的对决。当耿先生从那桃木剑中抽出三尺青锋时,在那生命最后的片刻,紫微郎朱铣该会留下怎样的遗言?
“为人臣者,身非我有,死君之难而已。”
我想象这是他最后的一句话。这是他生前最为人所称道的名言,我在太学读书的年月里就已熟知他这名言。文士为官,总要以巧言妙语邀宠扬名,他们生前以此赢官声,死后以此得不朽。
雨后空山,有孤云出岫,有松涛隐隐,天水间一派苍凉。钟声悠悠传来,这是玄武门报时的钟声。这该是朝官们点卯的时辰了,而我将从此与仕途绝缘。他们显亲扬名,他们封妻荫子,而我已无家可归。不再有父母。不再有家国。我的去路是逃亡。
此地不可久留。耿先生已为我备船,申屠令坚将送我一程。江湖路远,关山幽隔,此一别或将是永诀。我不愿就此匆匆作别,耿先生神色也有些怆然。我惆怅无语,便默默地望着那把剑。我只是望着那桃木的外鞘,我看不见那木鞘之内的青锋。
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是菩萨应起常住慈悲心,方便救护一切众生。若离杀生,即得成就十离恼法,命终生天,得随心自在寿命。
佛法戒杀,耿先生虽为江湖道人,却也分明是在修菩萨行。我望着她手中的这把剑,这青锋利剑自可劈开一切爱锁情枷。我又想到那右手持剑的文殊菩萨,那宝剑是明惑之剑,是智慧之剑,文殊菩萨用那宝剑断灭愚痴和覆障。
我的内心涌起一种沉重难言的眷恋。我一向讷于言辞,在这离别之际,纵有千言万语,此时竟至于无语。我心绪如麻,神志一片昏沉。这昏沉中亦有一种空虚。这宝剑也还将是她的随身之物,我便随口问起这剑名,其实只为掩饰这无语的空虚。其实我想问的是,这把剑还会用来杀生么?
耿先生凝视我一眼,就立时看透了我的心思,也看出了我的疑惑。她便说这剑名为“玄女剑”。她说她有三把剑,一断贪嗔,二断情缘,三断苦恼。她说早年她即用过那第一把剑,适才又用过了这第二把剑。我正感困惑不解,就见她剑指那丹炉。我问第三把剑在哪里?她说第三把剑是无形之剑。
她将那传国玉玺装进我的背囊。
她说她刚用过的即是这第三把剑。
无形之剑。她用无形之剑斩断了苦恼。这苦恼却成了我的背负。
“缘起缘灭,倒也不着迹象。”
“斩断苦恼可得成仙么?”
“成不了天仙就成地仙罢,反正也没多少元酒喝了,本来也还想多活几春……”
我凛然一震,看她的样貌似是并无一丝老态,依然是冰颜雪肤,依然是神清目朗,但这飘萧的长发分明是透着岁月的风霜。我望着她发际的一滴露珠,那露珠在微风中颤动。
“也还有些时日……”她似是以这话宽慰我。我说不出那些感激图报于异日的套话,我甚至难以向她以礼叩别。此时此刻,她那深潭般的碧眼漾着一种温情,那温情中亦有一种哀矜。她缓缓伸出双臂,默默地拥抱我。
申屠令坚在催我上船。耿先生浅浅一笑,又轻吻一下我额头。
“万里云天,皆非心外。你这就去罢。”
我强忍泪水望向远处,望着那片苍茫迷蒙的烟水,那一叶扁舟将会把我带往未知的远方。山水迢遥,何处将是我的落脚之地?我望着那烟水之上的沉重的阴云,我在那天水之间看见一个漂泊者的身影。如此寂寥。如此沉重。申屠令坚只是送我一程,而耿先生或将永不再与我相见。
我再次向她转身,而她已悄然离去。风起雾涌,林木萧萧。在那松风深处,她的身影消失在一片轻雾中。我听见雾中传来一声幽叹——
“清静!今儿个也是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