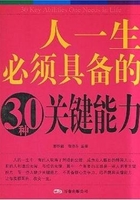在徐铉奉太宗皇帝敕编撰的十二卷本《江南录》中,耿先生事迹被写入“方术传”。徐铉在《耿炼师》一节中有如此这般的描述:“耿先生鹤发鸟爪,姿首妖冶,尝着碧霞帔,飘然若世外人,世人莫测其由来。然晦迹混俗,素以道术修炼为事,且能拘制鬼魅,其术不常发扬于外,遇事则应,黯然而彰。尝雪夜拥炉,索金盆贮雪,又令人握雪成锭,投诸火中,片刻徐举出之,皆成白金,而指痕犹在……”
徐铉笔下的耿先生俨然方外异人,而令人费解之处在于,徐铉对其世间真人的一面竟不着一字。南唐寖灭,徐铉以降臣之身追录前尘旧事,虽忘远取近,亦未免过于疏略。不干时忌,不涉隐曲,那部《江南录》不过是他的一番呓语。明哲世故如徐铉,其实是有意为之。今朝的史官遵奉的自是今朝的官家,身为降臣而为旧朝修史,他们聊可追记的亦只是风花雪月的余韵,他们惟恐因触忌而得罪。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徐铉写耿先生尽隐其侠风,写朱紫薇则惟彰其官德。朱紫薇虽为书法大家,但却并非博识高才之辈,与韩徐等饱学鸿儒相比,他的诗文实也无足称道,徐铉乃备述侈饰其尽忠职守事。朱紫薇清慎明著,克尽厥职,徐铉将其列入“循吏传”。如此作史方能投新主所好,惟因历朝君王无不倚重这等辅臣和循吏。所谓正心诚意,所谓修身齐家,终来不过维系在一个官运上。朱铣三世寒微,端赖合族人积垫,方有一朝登入龙门,而家族之荣枯亦维系于他一人。孤身在外为官,祖地却有合族百口人靠他照拂,朱铣断不敢少容松懈,亦不敢有半点闪失。名为济世拯民,实是为食禄养家。盖因动辄得罪,百慎一疏,即或有诛夷九族之祸。如此便有徐铉所言:“博练政体,兢兢自保。才优匡国,忠至灭身。”徐铉笔下的朱紫薇足可为天下榜样,然对于朱紫薇“忠至灭身”的真实情由,徐铉却语焉不详,仅以寥寥数语带过:“铣率兵剿贼于玄武,不幸为贼所虏,或传贼以化药解尸,身首遂失其下落。”
我却知晓朱紫薇身首之下落。他的尸身并未被化解。尸解即可成仙,朱紫薇实无这福分。我也知晓朱紫薇以身殉职的实情。徐铉的《江南录》为新朝君主所嘉纳,太宗皇帝亦将其视作南唐一朝的官修正史。我却深知这位史官所隐蔽的真相。《江南录》付梓时他尚在人世,我也与他略有过往,但我强使自己钳口不言。我甚至强使自己放弃质疑他的冲动:开宝六年那个中秋,是谁向朱紫薇密告了我的行迹?
那天清晨父亲被拘之后,我最先求助的就是这位德高望重的徐尚书。而在此之后,便有两位画师在我抵达之前遇害。我在舍利塔前偶遇耿先生,她以那样一种闪烁之辞告诫我勿求他人,那时她已知我去过妙因寺边的徐府。
深稳练达的徐铉,他也隐蔽了那场皇宫灾变的实情。在他那部钦定传世的史录中,那场灾变只有轻描淡写的几个字:宫禁失火。
而我分明是在那火光中看到了一种宿命。那正是朱紫薇舍生忘死而必欲掩盖的真相。朱紫薇以一己之死保全合族百十口,那是足可彪炳史册的至孝。天下杜口,以言为讳。身为主控舆情的重臣,朱紫薇秉心贞亮,查秘籍,禁谣传,亦可谓防民防川,守土尽责。国主追赠他的谥号是“文忠”。
徐铉虽在《江南录》中将朱紫薇归入“循吏传”,却又誉其为“烈士”。
世道沉沦,人心已是不可收拾。忠孝两全者稀有,忠孝复又忠烈,朱紫薇不枉徐尚书笔墨!而我决意保持缄默。我虽念其可叹,却也知其可悲。朱紫薇至死都未能见识那真相。
那真相亦非他以烈士之死所能掩没。
马车在清冷的官道上疾行,小长老在驭座上执杖开路。寂寥的夜色中不见人影,只有几条野狗在觅食,又有人家的孩子在啼哭。啼哭声从长干里那边传来。长干里曾经有座长干寺,传说那寺塔中供奉有佛顶真骨舍利子,如今那地带却只有一片粪秽遍地的民居。那粪秽之下会有一个地宫么?那地宫中会有怎样的秘藏?我情愿国主不复他求,情愿他所要的就是我眼前这宝匣。(编者注:历史上长干寺曾数度兴废,数易其名。2008年7月,南京考古人员在明大报恩寺塔原址开掘地宫时,意外发现该地宫实属于宋真宗年间的长干寺,而地宫铁函中的佛舍利乃是今人所能见到的惟一的佛顶真骨舍利子,这枚舍利子如今供奉在南京栖霞寺。)
车过长干桥,那暗处忽然传来一声哀叹:“老天爷!这可叫人咋活啊!”
前方就是那重楼高耸的朱雀门。
“天使回宫,速速开门放行!”那车夫学着官腔吆喝。
我撩起窗帷仰望谯楼上的大鼓,此刻无人擂鼓。我也不想听到那催命的鼓声。
掖门缓缓开启,守卒在旁拱手迎候。小长老合掌颔首,守卒向他交还铜符。马车顺畅地穿过这门券。
城市仍在沉睡中。车过朱雀桥,我朝不远处的太学和贡院望一眼,也朝那乌衣巷望一眼。前方即是笔直的御道。御道的两侧是散从官营和民宅,也有鳞次栉比的坊市,有鸡行、米店和油坊,有酒肆、茶社和药铺,也有花行、丝行和银行。雨后的御道不见积水,砖铺的路面泛着幽光。
车厢在微微颤动。我与耿先生相对而坐,宝匣就放置在两人之间的金漆方案上。车厢如此狭小,我与她之间却似隔着遥远的距离。那个拥抱的感觉早已消失,那只是瞬间的温情。此时此刻,她的神态又复归于那惯常的冷淡。我已说出自己的好些个疑问,而她只以简短的话语作答。岂只是冷淡,这简直就是冷若冰霜了。这问答的间隔便有难堪的静默,马车正在穿过夜色,夜色也是这般的静默。这静默令我感到压迫。我不时地撩起窗帷望着街景,而她也不时地瞄一眼宝匣。宝匣虽有些沉重,匣壁却未必很厚实。这梅芯锁却是异常坚固,我不知谁会有锁匙开启它。
“看好它,或许你就是下一位护法了。”
她低声说出这句话,眼睛并不看我,我却能感觉到她眼神中的阴影,隐约闪现的阴影。我的头皮便立时有些发紧。
“可我……我都不知这是何物……”
“你能找到它,你也就配得到它。”
“我不要得到它。这是我父亲的秘藏。”
“他们也是为防万一。”
我最怕这万一的事情发生。我一时语塞,不知能否以这宝匣换回父亲,也不知该如何说话。她也不再言语。她侧身望着窗外。在这幽暗的车厢里,我看不见她的表情,只有那张苍白冰冷的脸在颤动。
如此难堪的静默,不再有视线的交会,她甚至也不再有那讥讽的冷笑。她说我配得这秘藏,言下之意即是说,她自己早已不被信任,甚或可以说,此时此刻她就是我的敌人。我深知自己仍处在她的掌控中,假使她愿意,她随时可以抢走这宝匣,也随时可以取走我这条小命。虽有这番遇合,我却依然难以辨清她的本相。这昏暗的车厢在晃动,而与我对坐的似乎只是一个人影,只是一袭长发和长袍。
她曾是韩熙载和我父亲的同道,后来她却成了朱紫薇的情人。我亲眼看见樊若水掐死了王屋山,樊若水却说郎县令和陈博士是凶手。大司徒既与王屋山有奸情,却又对其死因不予深究,而舒雅和李家明也是形迹可疑。他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勾当?
我正这样想着,就见她撩动一下长发说:“舒雅宣州人,李家明庐州人,樊若水池州人,张洎滁州人,小长老淮北人。”
我蓦然一震。如梦忽醒,那确是无以名状的惊悸!那一刻我现出的是怎样的一副蠢相!她这读心的神通是从何而来?
“是有那么一党。”她似是在喃喃自语。
“淮党。”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朝官中不少是淮党,这几个又为这宝物而结拜。”
“既已结拜,如何又有这番螳螂捕蝉?”
“小人结党总会如此,那女魔头不是说灭就灭么?”
“王家少妇王屋山?”
“你可知她胃口有多大?”
“学生请愿,也揭发王屋山独揽天下铜矿,就是倚仗大司徒的势要……”
“由是大司徒才要除掉她!她手里把柄多得是,你也知淮党拜盟是在哪?”
“风月楼?樊若水却跟她看似并不熟……”
“这倒不然,他们也是早就有过首尾的,那婊子只是做戏给你看。”
“可樊若水也还是灭了她……”
“那就只怪她多嘴了,其实也是难怪,不过是那么个贱坯……那钓鱼的事也只是樊若水自知。”
“可那李家妹的事又怎么说?”
“你想说是我灭了那粉头。”
“正是!你却将她移尸风月楼……是恐她招人去往藏书楼……”
“你也还不算笨。”我能听出她这语气中讥嘲的意味,但我确也有自知之明,我知自己并非蠢人,我确是说破了她的隐秘。
“你道我何以要有这番事?”
“你以为那里有秘藏。”
“才说你还不笨!其实是因你在那里头,就在那客室。”
我一时错愕无语。如此说来,她暗中杀人移尸是为我。我不曾想到她会这样做,我确是不够聪敏。这却使我愈感到困惑,我难以相信她这样做真是为了救护我,我看不透她究竟是何意图。我直感到自己很蠢笨。我要学会掩饰这蠢笨。我要主动出击。
“你却未必非得杀了她,她也未必是那样的邪货,究竟她只是受了兄长指使……”
“糊涂!他们哪是甚么兄妹!”
我陡然吃了一吓,见她这般声色俱厉,便自知犯了大糊涂。那位陈博士不也说他们本就不是亲兄妹么?那位大司徒不是也曾说,李家妹也为那鱼肚帛书作证么?
“早年也不过是一营妓,装娇撒痴是拿手好戏,弹曲讴歌却是仗着李教坊调教。”
“那画轴上有诗句,像是在说……说我……”
“一个装娇撒痴,一个自作多情。怕是另一个狎客也会想,‘像是在说……说我……’”
我并非狎客,此刻我却无力辩解。我也不在意她的嘲讽。另一个狎客也会那样想。装娇撒痴的伎俩。罪当遭灭。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那个搔首弄姿的女子,那眉眼盈盈处有着怎样的一场旖旎和缱绻?那波荡的芦苇和撩人的琵琶声,那意境可曾勾起我可笑的诗情么?“彼美人兮”,“彼君子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在这个吟风弄月的国度,诗情本是文臣们的专利。他们摇唇鼓舌以显其忠,妙笔生花以炫其才。他们以词邀宠。他们专修的术业是藻耀。“林仁肇攻城夺寨,骁勇无敌,然终不过是一介武夫!”——他们的讥嘲也曾激起我的愤恨,而父亲却只有隐忍和沉默。十二岁我初学骑马跌落,父亲便禁止我走近那球场。父亲甚至收缴了我的雕金双弦小弹弓,就在那样一个天真未凿的年龄,父亲为我指定的去处是书房。读书出仕,那是天下有志者必走的正途。我却见识了那些得志者的嘴脸。父亲是要我做一个曲学阿世的文臣么?文人们无不以辞章谋利禄,我却不愿苦练那吟诗作赋的技艺。我也自知酒量有限,实难应付那些酒社诗坛的唱酬。我注定成不了李青莲,也成不了杜少陵。即或遇到那样一个琵琶女,我脑子里冒出的也还是白香山的诗句。年齿徒增,才学了无长进。我愧对父亲一片苦心。
御街两旁不再有坊市和民宅,代之而来的是一些有牙兵把守的高门深院,这便是诸司衙门和江宁府的官署了。
刑部大狱就设在这官衙里,父亲就在那狱中。此时此刻,父亲是在倚墙而坐么?
这天街的尽头是虹桥,虹桥之后是皇宫。
“若能见着黄保仪,倒也让你长些见识,那可是宫中女学士。”耿先生若有所思地望着我,“那才是绝世姿容,寒梅一品,大小周后也没得比。”
“我再也不想见甚么美人……”
“这也不用说与我听,见不着反倒是好……”
“这黄保仪是何人?”
“她呀,虽是贵为保仪,却因小周后专房苛妒,多年不得进御。可怜她如此青年,却只是为国主掌图籍。虽处冷宫,却也难掩那十分才情。还有她那蔷薇水……”
“我是要见着她么?”
“就恐你把持不住……”
我恼怒地瞪她一眼。此时此刻,对于这样的玩笑,我确是无动于衷。
“她也差人为那命灯添油……”
“家父……见过她么?”
“元宗朝灭闽灭楚,她父亲本为楚将,而令尊本是闽将。父亲国灭身亡,小妮子便被掳来宫里。”
耿先生望着前方那隐约可见的皇宫,那皇宫之上笼着沉重的阴云,那阴云之上是更为沉重的夜幕。我这颗心立时又悬起来。进宫后万一遭遇不测,我还得再次逃命么?
我双手抓紧这行囊。《夜宴图》仍在,我不知留它还有何用。父亲脱难之后,我会郑重地送还他。那时父亲定会对我刮目相看。他会亲手为我斟满一杯酒,而我也将不带愧疚地一饮而尽。
耿先生望着我的手。我的手从行囊里摸到了诗签。这诗签致使我经受了如此一番历练,假如我当初抽到的是另一枚诗签,那又会导向怎样的结局?
她显然已看穿了我的疑惑。她从袍袖中抖出签筒。我接过签筒察看这些诗签,立时便愕然僵住。
这些诗签上皆是一样的诗句!无尽藏女尼的开悟偈!“梅”字右上方也都有一个点!
“那么……那四方神象又当何解?究竟这是怎样的应验?你在我身上写字,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顾闳中死在东边,周文矩死在西边,我来到韩府,也因朱雀在南……”
“我也只是偶然路过,与你祛除那鬼风疹。”她淡然一笑,并不多言解释,似乎那只不过是一种巧合。
“偶然路过么?你向孙二娘问我喝药的事,此前你定是来过了。”
她并不回应我的话,却又旋即正色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岂必大事才是天数,小事便不是么?”
“玄武在北,城北有玄武湖,该是不必去那边了。进宫见了国主,不就万事大吉了么?”我低头望一眼方案上的宝匣。
“但愿如此,此刻也正是在北行,皇宫也正在北边。不过也难说,没准也还得走一遭。”她语带玄机,声音也有些低沉。
“也是……四方神位自是以皇宫为中央,那皇宫就不算是北方……”
“林公子好悟性!”她朗声一笑,我的神志为之一爽。
那笑声转瞬即逝。我忽觉这是我头一遭听到她的笑声,她竟然也会有这样的笑声。
小长老也为这笑声所惊动,他回头朝车厢里张望。耿先生朝他摆摆手,小长老便有些释然。他又指一下自己的额头,那印堂处的紫包是愈发肿胀了。耿先生冲他晃晃手中的签筒,小长老这才放心地转回身。
“如此说来,进宫之后事还没完么?”
“该说的我都已说过了。”
车近虹桥,迎面窜来一伙吹铁笛的巡警。小长老晃动一下金杖,那些无赖巡警就不再阻拦。
前方就是宫前广场了。
死寂的广场。不再有人长跪请愿,不再有人顿足呼号,不再有人引火自焚。那登闻鼓只是一个虚设,国主听不到这鼓声。
夜风打着呼哨,将落叶和纸片刮进虹桥下的河道。那些纸片是白日的残片。
马车驶过广场,驶过虹桥和横街,皇宫的正门前已有一队禁军在恭迎。宫前的铜驼已不见踪影。
“荆棘铜驼,也还是老故事。”耿先生低声自语。
小长老躬身施礼,禁军交还铜符。金钉掖门缓缓开启,马车穿过长长的门洞。
禁兵跟在车后,马车长驱直入。国主深居后宫,这前朝的殿堂制度壮丽,却无一不是朱门紧闭。
前朝的主殿是升元殿。烈祖皇帝登基之日,这殿前曾有群象拜舞、百官嵩呼的盛况。那时有契丹使者以羊马入贡,有渔夫进献天降雨粟,烈祖皇帝仰天祝赞:“吾朝初肇,天赐祥瑞。华夷咸若,骏奔结轨。皇哉唐哉,文德信威。仓颉四目,吾孙重辉。天雨粟兮——”
天雨粟。鬼夜哭。余生也晚,自是无缘见识那上天雨粟的奇景,当今的国主定然亦无真切的记忆。烈祖立国时的新生儿,那个目有重辉的国主,此刻他正在皇宫深处等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