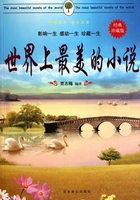我大步闯进这鬼影幢幢的暗夜里。虽有秦蒻兰告诫,我却忍不住还要朝那梧桐树下瞥一眼。
那女尸已不在原地!
我快步跑过那篱墙,一过篱墙又忍不住回头看。那树下确已不再有尸体。
那个狐妖样的女子,她确是那个美目流盼的李家妹么?
不翼而飞,似是为某种神力所挪走。若是有人来搬运那尸身,那只灵敏的小猫怎会毫无反应?
往左拐不远处就是那石桥,那石桥通往湖心岛。
我疾步走过这长长的石桥,我听见胸口在怦怦作跳。我的步速和心跳都是一样的迅急。
这湖心岛似已成荒岛。蓬蒿蔽径,蛇鼠蹿游,又有鸱鸮叫声从四时轩传来。那四时轩曾是韩府无数场夜宴的所在,此时只剩一个枯骨般的框架。
我小心地护着灯笼,生怕这火苗被夜风吹灭。我无须登临那空旷的高台,她说无尽藏就在湖山的东边,就在那琅琊台下。那琅琊台周边山势起伏错落,又有蹬道隐现其间,夜色中望去,像是峰回路转的迷境。我直奔那高台的东侧,那里有一片古松林。
月光暗淡,苍鬣虬枝掩映着一楹粉墙瓦房,那是湖山东侧惟一的房屋。
那瓦房想必就是无尽藏了。
这确是我要找的无尽藏。
借着清冷的月光,我看见门楣上方那块匾额,那是三个醒目的隶体字:无尽藏。一望便知那是韩熙载的手书。那三个大字雕刻在一块石板上,那石板深嵌在墙壁上。
无尽藏。那位传说中女尼的法号,这名字藉由那遥远的传说而存在,也藉由那神秘的诗句而显现,我却难以想象出那女尼的形象。于我而言,这是一个谜样的名字。此刻我站在这座废弃的瓦房前,这座瓦房的名字也叫“无尽藏”。这名字就刻在墙壁的石板上,我却依然难以有真实的感觉。此刻我正走近无尽藏,走近这座废弃的瓦房,走近这个谜样的名字。(编者注:据《景德传灯录》记载,有僧人向行冲禅师问,“如何是无尽藏?”禅师良久无语,然后说道,“近前来。”问者近前,却闻禅师一声猛喝,“去!”)
我屏声静息走近那屋门口,忽见那把铜锁早已被撬开。我心里陡然凉了半截。或许是有人先我而来。这就意味着,我的寻找恐是徒劳一场。
铜锁已被撬开,板扉只是虚掩。我绝望地推开这木门。门轴发出吱呀的怪响,我的头皮一阵发炸。我一腿刚迈过门槛,就被厚密的蛛网糊了一脸。绝望立时变作惊喜。或许先我而来的只是盗贼,或许那盗贼是在更早时光顾此地,不然门扇间不会有如此厚密的蛛网。
蝙蝠惊飞,灰尘飘落,有一股呛人的霉味。屋里空空荡荡,墙角和斗拱上也结着蛛网,地上有一堆堆瓷器的碎片。窗边也有一道柜台,那或许是为发放施舍物品而摆置,抑或是韩熙载与姬妾们佯做买卖时所用。
或许蝥贼拿走的只是放在明处的财货,或许我要找的宝物在暗处。带着这样的指望,我仔细检视每一个角落和每一块地砖。
外边忽然传来一阵闹嚷声,又有人影在墙上闪动。我从门口望去,就见一伙人举着火把奔来。
我慌忙吹灭灯火,身体紧贴墙边缩在门口。
他们吆喝着直冲进来,我闪身从门口溜出去,不料外头还有一人在把守。那人手持火把朝我扑过来,屋里的几个也返身窜出,慌乱间我想起秦蒻兰给我的匕首。
我从膝裤里拔出匕首,又紧攥刀柄冲他们晃动,他们便一时不敢近前。我晃动着这环指匕首往后退,这手臂就忽遭一下猛击。匕首落地,击落匕首的是一根火把。那袭击者就在我身后。
他们一拥而上将我按倒在地,我的双手立时就被反剪到背后。他们狠力地将我捆住,又揪着绳子将我拉起。我的眼前一阵昏黑。
“押往风月楼!仔细江宁县抢人!”
这声音有些耳熟。他们推搡着我往前走。这时我才看清那为首者正是李家明。那发话者显然就是他。
莫非是疑心我害死了他妹子?我并非凶手。我只是一个目击者。我有秦蒻兰作证。情势却似非这般简单,那尸身已不知去向。他说当心江宁县抢人,或许是江宁县的人马也来了。我听说江宁县令是郎粲。郎粲曾是韩公的得意门生,三年前的那场夜宴上我与他也有过一面之缘。郎粲或许是来断案的,只不知他能否记起我。那时我只是一个懵懂少年,而他已是韩公提携的新科状元。
那时他色眼迷瞪地听李家妹弹琵琶,而今他要来查断那女子的命案。
他们押我走在浮桥上。这浮桥通往风月楼。浮桥悠悠颤颤,他们的脚步也都摇摇晃晃。若不是双手反绑,我会从这桥上跳下去。李家妹有李家明,也有郎粲郎县令,而父亲只有我。
浮桥那端聚集着好多人。有的举着火把,有的打着灯笼。那风月楼也是灯火通明,楼上的窗口也有人影晃动。
这时我忽又想到,风月楼主人王屋山已毙命。我倒是能为王屋山的死因作见证,但此刻我绝不想这样做。我不能耗在这里。我应尽快脱身。
那确是前来查案的官人,为首者正是江宁县令郎粲。江宁上元二县县治均在这都城,二者以秦淮河为界分治,城内河北为上元县,河南为江宁县;城外河东为上元县,河西为江宁县。韩府正是处在江宁县辖地盘上。
跟郎县令同来的还有太常博士陈致雍。也有几个捕快围护着他们,但似无李家明纠集的家丁这般凶狠。
秦蒻兰说陈致雍是朱紫薇的心腹,他这显然是为我而来。
李家明的打手摩拳捋袖,执刀逼将过去,郎县令的部从便步步退缩,而在其身后就是那桂花园。就在那月洞门后的石山下,县衙的仵作正在为王屋山验尸。郎县令已是怒不可遏。
“大胆李家明目无国法!本县奉公办案,你竟也如此凶狂么?”
“我道是谁,原来是区区一个江宁县!可这又是哪里来的话?令君莫弄虚头,自古是民不举,官不究。你等不请自来,擅闯民宅,李某倒要有个计较。”
“噜唣!这江宁地方出两条人命,就休说是你家私事!那王屋山也并非是你李家人!”
“好个村泼县令!没处寻死,却来这里现眼了!王屋山也还是韩府人,韩府事自不待外人管!要命的就赶紧从这里滚出去!我在这里住人,你就甭来找茬,也仔细我去江宁府告你们!”
“江宁府尹自是与你有亲,郎某朝中也并非无人。教坊副使李家明你且听好,本县已获密报,勒死王屋山的便是你!”
我疑惑不解地望着郎县令,我明明看见掐死王屋山的是一僧人,那僧人五短身材,也不似李家明这般的衰老。
“混缠!这也可笑的紧了!生生是荒乎其唐!教坊演戏怕也没这般的滑稽!”教坊副使李家明抚掌大笑,他的喽罗们也跟着一起哗笑。
郎粲更是火气直冒:“只怕你是笑得过早了!人证物证俱在,真相已明,你妹子也是死在了你手!”
李家明略一愣怔,立时又变得强气起来:“好没来由!郎状元莫非是要编传奇?家明老矣,却不想在你戏里轧一角,不理你也罢了。”
“这怕是由不得你了。想保命就速跟我回县,明日升堂自有理会。”
“滑稽!李家明奸杀李家妹!浑不成道理!”
“实在你们并非亲兄妹。”陈博士不似郎县令这般光火,说话却是绵里藏针,“你若硬说是,那你们便是有十数载乱伦了。”
李家明登时有些错愕,忽又摇头叹道:“国兴见祥瑞,国亡出妖孽。状元县令草菅人命,太常博士血口喷人。法纪废,纲常乱!好好好,怕你的也不是人了!”
“草菅人命的正是你!”郎粲再次发作,“那孩儿究竟惹犯了甚么?你李家明是要动私刑么?”
“你这糊涂县令总算醒神了,这正是你该捉拿的案犯!”
我这才惊觉自己被当成了凶犯!我正欲叫喊,嘴巴立时就被塞了布团,又有利刃架在我脖子上。
李家明冷笑着瞟我一眼,喽罗们便拧紧我手臂。
陈博士跨前一步说:“李副使,按说我不便插手多言,只是半路遇见郎县令,听说韩府出了命案,就顺道一起来看看,也是凭吊一下韩宰相。就说目下这两起案子,郎县令来拿你,自然是有人证。你却说这孩儿是凶手,那你又有何凭证?”
“陈博士忒絮烦,本来不干你事!但若说凭证,这些伙计便是!他们眼见为实!”
李家明朝身后的喽罗们瞪一眼,他们便叫嚷说是亲眼所见。我已是有口难辩,只盼望郎粲能设法带走我。然而郎县令是与陈博士同来,而陈博士是朱紫薇的人。
“既是如此,郎县令所得密报亦未必可靠。”陈博士似是在打圆场,“李副使既已抓了疑犯,郎县令就该带回推问。”
“世上怕是没这等便宜事。”李家明语气又变得强硬,“带他去县衙,判死不过抵一命;留由我处置,便可一命抵二,我要看他死两回!这也才算是公道!”
郎粲的捕快显然不敢上来抢走我,他们不是李家明这伙恶徒的对手。陈博士对郎县令耳语几句,郎粲便朝那风月楼望去。
正在此刻,那仵作拎着竹篮从楼上跑下,又直朝这小花园奔来。仵作从竹篮里取出一枚小物件递与郎粲看,郎粲便冲李家明高声嚷:“令妹可是身中暗器!你却说她是被奸杀!”
“是咋死的不要紧,最要紧是谁下毒手!”李家明不屑地撇撇嘴,“我说你郎县令也该回避了!我为妹子惩凶,天经地义;你既是她的情郎,倒不怕有徇情枉法之嫌么?你这才是目无国法!”
“陈博士,咱们回!我且要正告这戏子,人在你手上,若是伤他一根寒毛,我就要了你这把贱骨头!”
“骂得我好!这把贱骨头自是奉陪了,我若惧怯,也算不得汉子!只是陈博士也该避避嫌!”李家明又阴测测地冲着陈博士嚷,“这原是有一件大隐私!原本我还纳闷,郎县令查案干你何事?原来你是跟王屋山有苟且!”
“这就走!本官明日却和你理会!”郎粲说罢便转身开步,陈博士便紧跟其后。
“阁下只怕是有来无回了!”
李家明一挥手,几个持刀喽罗跨前几步。
“郎县令可是去搬兵么?”李家明语含讥诮。
“犯不着!官军就在这墙外!”陈博士朗声大笑,“李副使可别犯糊涂!”
李家明望着远处的高墙,似乎立时便有些忐忑。
“区区一个县令,如何劳动官兵!”
“本县乃朝廷命官,非常之事自有非常之策!李副使也曾侍奉先皇,总该知些深浅。”
“果然是朝中有人哇!只怕那靠山也未必有甚品级,只怕我眼角里还不曾见着哩!”
“横竖是大过你李副使!”
他们再次转身欲走,李家明又冲他们叫嚷:“不就一个朱紫薇么?”
他们立时即被震住。我却不再有惊诧感。郎粲和陈博士都是朱紫薇的人。他们是欲从李家明手里夺走我。他们也都曾是韩熙载的门生。
李家明依然不依不饶,呶呶不休:“朱紫薇难比杜紫薇,杜紫薇难比李太白!我家太白是天子呼来不上船,哪比你们这些烂走卒!”
“走卒也是朝廷走卒!不须多话!看我明儿拿你不是!”
郎粲拂袖开路,陈博士和衙役们紧随其后。
“明儿你该是等着摘印了!”
“那夯货休走!我等的你恰好!”
远处猛然传来一声沉喝。他们便都朝那桥头望。一僧人正幽幽走下那浮桥。
那僧人身披袈裟,手执禅杖,如鬼影般自那暗处显现。
“阿弥陀佛!”僧人徐步而来,他一眼瞥见王屋山尸首,便双手合十,连说几声“罪过”。
那女尸仍在桂花园的假山旁,就在那石榴树下的花影里。
膘肥体壮,五短身材,缁色袈裟,沙哑的声音……
我难以追述那时我所经历的那般惊怖。我呆呆地望着那人走近。他就是掐死王屋山的那僧人。
“怎说我并非真和尚?”
“你是在江上钓鱼么?”
那僧人缓步轻摇来到光亮处,双手缓缓托起那禅杖。雕龙金禅杖。
“心识不到处,古路不逢人。贫僧来化血光缘,这韩府竟是无人识得么?老大不知高低!”那僧人扫视全场,神气甚是倨傲,沙哑嗓音中也透着戾气。
“天使大驾光临,虮虱微臣岂敢仰视!只是有眼无珠,这才识得国主金禅杖。”话音未落,李家明已是展背舒身,铺胸纳地,捣蒜也似地磕头。
“这班夯货在这作甚么?究竟是些甚么人?”
“朝廷走卒。”李家明朝郎县令他们瞥一眼。
“太常博士陈致雍!江宁县郎粲!”那僧人金杖戳地,一声暴喝。
陈博士颓然跪地,郎县令和捕快们也低头缩颈,扑身跪拜。
李家明的打手们先是将我按下,接着也都跪地叩头。
“国主供佛,也供有一位一苇法师的,陈博士可曾有闻?”
“不才有闻,还望上师赐教。”
“苦主又是何人?”
“下官是一个,舍妹遇害。另一位是舒雅,舒家娘子被杀。”李家明使个眼色,一个喽罗便往那风月楼奔去。
“韩府连出命案,实非府县蠢官所能了断。老衲俗名樊若水,今奉国主特谕来此,是要作速探个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