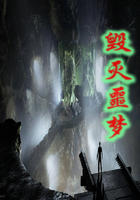这是什么?好可怕!我想都不想就往外冲,拼了命地逃离这个像被诅咒了的房间。不顾其他同学的侧目,我穿过操场,一路跑出校门外,沿着公路狂奔,直到无法再负荷心跳的加速,双腿也开始酸软,我才停下喘气。撑着膝盖连吞了好几口口水,喉咙像被火烧一样干疼。抬起头,我才发现不知不觉我就跑到了大房子旁。大堤上没有人,屋子的窗帘依旧拉得严实,仿佛害怕有任何一丝光会偷溜进去。
吸血鬼!之前的噩梦再次在脑际盘旋开来,一幕幕的惊栗画面涌上眼前。
薛城羽真的是吸血鬼?这些天奇怪的事情都是他做的吧?他想要吸我的血吗?他要把我变成同类吗?
我根本无法以逻辑去思考现下发生的一切,唯有这样去解释所有的事情。
隐约自海面上传来一阵阵并非浪潮的声音,仔细听来,像是马达声。我眯着眼睛朝海面望,看见远处正有一艘快艇靠近。船速很快,在我还没来得及有所反应的时候,已经能看清上面的人的身影了。
是薛城羽,他回来了。就在看清那张脸的同时,我先是有种莫名的兴奋,好似等了他千百年一般,但随即恐惧就像一张挣脱不了的巨网,即使我不相信吸血鬼的传言,却因为他的靠近而不由自主全身战栗。
就在他也看到我的那一刻,我向后退了几步,最后因敌不过恐惧而再次逃走,无视他讶异的表情,我这次一口气跑回家,直接进了房间将门反锁。站在屋子里我不知如何是好,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顾不上奔跑后的口干舌燥和气喘心跳,我立刻关上窗户,一把把窗帘拉上后就躲到床上钻在被子里浑身颤抖。
恐惧并没有消失,但稍稍的放松让我再也控制不住肆意流淌的眼泪,发泄一般,我大声哭了出来。
妈妈在外面拍门,一直追问我怎么了,但这些声音仿佛成了整个世界的背景,而我脑中回响着的却是:用你的血来和我交换永恒的生命吧?当我的新娘吧?
我不记得自己哭了多久,又在什么时候睡着,一个接一个的噩梦让我穿梭在一个个血腥的场景中,不知为何,梦中的我似乎特别能判断一种颜色,血的颜色,即使在醒来之后对那个色调依然毫无分辨力。
我是被一连串的敲门声吵醒的,屋内窗帘拉得严实,以至于我一时间分不清白天黑夜,也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但我很坚持不想离开被窝,至少在这个小小的角落我能有微薄的安全感。
敲门声停下了,好一会儿外面都没有声音,我还以为是妈妈放弃让我开门了,才想翻身继续昏睡,门外却不期然响起了薛城羽的声音。
“留在学校的东西我帮你拿回来了,放在门口,你好好休息。学校的事情我会帮你处理好的,你不要担心,我先走了。”
我睡意全消,转头看着紧闭的房门,仿佛能看到他放下我的书包后转身离开的背影。他那句话很简单,语气平淡得让人感受不到他的喜怒哀乐,但却神奇地扫除了我对他的莫名恐惧。
他怎么可能是吸血鬼?终于,我坐起身子,重新绑了下凌乱的头发,认认真真回想下午所见到的那恐怖的画面。
到底是谁!一次次用这种方式来打击我,这个人用心好险恶,利用岛上的留言蜚语来增加其他人对我的反感。我到底做了什么得罪了他?
想到之前自己失去理智就这么跑回来,还要麻烦薛城羽特地帮我把东西送回来。我起身打开房门,爸妈房里的灯还亮着,一定还在担心我吧,看看时间都已经十二点多了。地上除了我的书包,还有妈妈为我准备的晚餐。心里一酸,我走到他们房门外轻轻敲了敲门,没有打算进去,只是告诉他们说我没事了,让他们早点休息后便把门口的东西拿回房间,再次关上房门。
说实话我一点胃口都没有,但想到妈妈担心的样子,还是勉强自己喝掉了已经凉了的鸡汤。拿过书包翻了翻里面的东西,想看看是不是所有的作业和课本都在里面,却忽然发现之前陈小雅托我转交的礼物不见了,难道是我留在了课桌抽屉里?皱着眉头我又翻了翻,在书包前面的口袋里看到一个浅色的礼盒,包装很精美。
我不记得我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东西,不禁好奇拆开一看,里面竟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昂贵的发箍,银色,有一朵镶着水晶的小花,闪亮闪亮的,看起来文静又不失活泼。发箍下面夹了张卡片,我一眼就认出上面那漂亮的字迹。
“不要老把头发绑得跟村姑一样,丑死了。”
啥?这一瞬间我所有的不安和恐惧全部烟消云散,他薛城羽竟然说我是村姑!还写什么丑死了!哪有他这么送礼的,怎么说我也是女孩子啊,这也批评得太直接了吧?况且我真有那么丑吗?
低头抓起我绑成两根粗麻花的辫子,再摸摸前额那确实有点过时的刘海,好吧,我承认这发型是不时髦啦,但他需要这么刻薄吗!
拿起发箍放在灯光下仔细看了看,瞧这镶嵌的做功,一定不是什么地摊或者小礼品店里的便宜货。品牌我是不懂啦,不过发箍内侧刻了点英文单词,和包装盒上的一致,估计是个什么牌子的饰品。他是大少爷,自然不会在乎钱这种东西,但这个看起来很贵重的礼物对我来说着实很难收下,我该怎么还给他?他会不会生气啊?
陈小雅的礼物最终没有找到,我猜想可能薛城羽拿走了,毕竟上面有写他的名字,这样也好,省下我跟他解释的功夫。说不定此刻他正乐滋滋拿着礼物,又或者已经和陈小雅浪漫约会了。一想到这画面我就火大,什么嘛,我又不是媒婆,郎有情妹有意的干妈把我搅和进去,真讨厌。
虽说心情平复了许多,但这些天来接二连三的状况让我彻底大病了一场。
跑回家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开始发烧,昏昏沉沉连谁进出过我的房间都不知道。烧得太厉害了,隐约记得岛上医院的医生来瞧过我,还给我挂了点滴。几次从昏睡中醒来的时候好象都是晚上,一身的汗似乎都没能降低体温。
我就这么一连睡了好几天,等我彻底醒来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跟石头一样僵硬沉重。又饿又渴,外面的阳光太刺眼,我只能用手挡住视线,从指缝里环视我的房间。墙上的挂钟指着八点十分,我猜想妈妈应该在院子里整理花草。
好不容易适应了光线,我吃力地掀开被子坐在床边,努力让自己的思路归位。先是在学校被人恶整,随后薛城羽回来了,我害怕得跑回家大哭一场,晚上他给我送东西,结果就病了。我已经不记得今天应该是星期几了,也没太在意,反倒是一身的汗臭和嘴巴里干涩的苦味让我很不自在。行动异常缓慢地从抽屉里拿了换洗的衣物,没多想就跑去冲了个澡,出来的时候就看到妈妈一脸惊讶地站在厕所门口。
“你怎么起来了呢?身体没好洗什么澡,擦擦就好了啊,快回去躺着!”
边说边抢过我手上的毛巾,一边擦拭我滴水的头发一边伸手翻找抽屉里的吹风机。
“妈妈我想吃东西,口也渴。”
见我有食欲了,妈妈很高兴,把毛巾披在我肩膀上防止衣服被沾湿,又拿了件外套给我披上后就拿着吹风机陪我到客厅。我坐在餐桌前看她忙碌着帮我张罗吃的,觉得很难过。
“妈妈对不起,让你和爸爸担心了。”
妈妈先是一愣,回头看看我没有说话,直到把吃的端到我面前,拿起吹风机,我边吃她边帮我吹头发的时候,她才回答说:“傻孩子,学校里要是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回来跟妈妈说就好了呀,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怎么行呢?”
妈妈很少会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平时的她大多都是在数落我和爸爸的不是,要不然就是和林阿姨聊别人家的长短,我对我妈妈的感觉一直都是那种非常典型的家庭妇女,每天买菜做饭,洗衣擦地的。然而今天我忽然发现,其实每个妈妈都很温柔,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去爱护自己的孩子。
我底“嗯”了声,默默吃着饭菜,妈妈没有追问我在学校发生的事情,不过我晓得就算我不说她也已经了解了,或许她在等我主动提起吧。
“这两天先别去上课了,病成这样要彻底养好了,要不然以后留病根。”
我点点头,觉得这样也好,反正我现在也不想回学校。又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直到我头发基本吹干后,妈妈又说:“那个薛家少爷昨天来过,说这两天会再来看你。”
我停下夹菜的动作转头看妈妈,很意外她没有露出八卦的表情,只是很平淡地边说边收吹风机的电线。
“哦,好。”
就算她难得没追问,我觉得我还是少提为妙,省得这话题又扯得没完没了。
吃过饭后妈妈硬是让我在床上躺了一整天,我想我这几天是睡过头了,怎么也睡不着,只能睁着眼睛瞪天花板胡乱想心事。
这烧退了理智好像也回来了,没再乱担心那些有的没的,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我一定在学校里得罪了谁。其实这么说实在不够准确,因为我直觉我是得罪了全校同学了,谁都有可能是那个让我难堪的凶手。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引起一系列不必要麻烦的人不就是那薛大少爷吗?要不是他我怎么可能这么招人讨厌。现下流行的那句什么来着,羡慕嫉妒恨,真是再贴切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