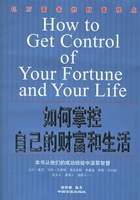廖火炕今天是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他主要负责后勤部办公楼楼道和几个公共厕所的卫生。
在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的办公楼里搞搞卫生,在楼高路宽的北京城里出出公差,当然要比在老家种地轻松得多,廖火炕从新兵连分配到机关以后,不怕出力气,就怕多说话。
新兵训练那几个月,廖火炕见到的最大的官是新兵团团长,那是个肩膀上扛着两道杠两颗星的精干汉子,等来到机关一看,好家伙,两道杠两颗星的首长多得很,两道杠三颗星、四颗星的首长也有不少,老兵们说,他们都比团长的官大。刚到公务班的时候,廖火炕有一次偷偷地问与自己住在同一个宿舍的老兵杨彦军:“我今天看见一个肩膀上扛着黄牌牌的首长,年纪比较大,他犯错误了吧?”
杨彦军奇怪地反问他:“你怎么会想到他犯错误了呢?”
“我在电视里看到踢足球时对犯错误的球员都是‘黄牌警告’。”
“傻帽,扛黄牌的都是高级首长,将军!后勤部干部中最高的军衔。”
杨彦军的嗓门很高,似乎是为廖火炕的无知而生气。
在此后的几天时间里,廖火炕吓得在杨彦军面前一直不敢大声说话。
前一段时间,都是一个老兵带一个新兵干活,廖火炕跟着老兵,多干活,少说话,注意观察老兵的举动,学习老兵的言语,处处小心谨慎,腚眼里有屁都只能慢慢地往外挤,生怕说错了话,办错了事。直到今天下午,班长才给新兵们分派了任务,让他们放单飞。
廖火炕把自己负责楼层几个厕所的坐便器、小便池、窗台、洗手盆都认真地擦拭干净,抄起拖把开始拖楼道的地板。
楼道里的灯光不是很亮,廖火炕认真地盯着地面,把角角落落都拖得很干净。班长说,公务员们每天搞完卫生以后,他都要仔细检查,第二天对检查情况进行讲评,廖火炕想给班长留个好印象。
楼里边靠近电梯的一间办公室里还亮着灯,里边一点动静也没有,白炽灯光从门下面的缝隙里挤出来,在走廊的地面上画出一条光带。廖火炕心想,这么晚了,应该不会再有人在办公室里,肯定是哪位首长下班时忘记关灯了。廖火炕站在门口外边犹豫了一下,觉得自己应当敲敲门,如果里边确实没人,就进去把灯关了,做一件好事。
廖火炕屈起手指,轻轻地叩门声在寂静的走廊里非常清脆。
办公室里一声响亮的“请进”,把廖火炕吓了一大跳。
廖火炕不得已推开门,看到一胖一瘦两个干部正坐在并在一起的两张办公桌上打电脑。
廖火炕只好进屋,声音哆哆嗦嗦地说:“首长,我——”
胖干部对廖火炕说:“小同志别紧张,有话慢慢说。”
“我是想问问首长,需要不需要我干、干点什么。”
“不需要,办公室的卫生我们明天上午上班时自己打扫。我以前没有见过你,是刚分来的新兵吧,哪里人?”
胖干部又问廖火炕。
“首长,我是刚来的新兵,老家是内蒙赤峰。”廖火炕局促不安,放下拖把,立正站好,挺直了腰板回答。
“以后与我们说话不要那么紧张,请稍息!你家在赤峰城里?”
“不,是乡下的。”廖火炕把刚伸出去的三分之二个左脚掌快速收回,依然立正站好回答。
“今年有十六岁了吧,是谁把你‘抓壮丁’抓来的?”胖干部又笑着问他。
“报告首长,我是接兵团接来的,不是别人抓来的,我也不是十六岁。”廖火炕挺了挺腰板,悄悄踮起脚后跟回答。
“不是十六岁!那您老人家高寿?”
“我今年十、十八岁!”
“十八岁?十八虚岁,而且是虚两岁吧!”
“首长,我、我真是十八岁,入伍前就已经工作了。”
“干什么工作?”
“在城里的工厂打工。”
“打了几年工?”
“两个半月。”
“嗬!那也算是老师傅了。你在乡下长大,当过工人,现在又参了军,工、农、兵都干过,不简单呀!”
“是,首长!”
“我不是首长,以后不要喊我首长,我与你一样,是‘脚’长,在机关跑腿办事的。”
“是,首长!”
“怎么还喊首长?”
“是,脚、脚长!”
“‘脚’长可不好听,你以后喊我郝助理就行了。”
“是,‘好’助理。”
另一个身材瘦一些的干部也停下敲击健盘的手,抬起头,笑着对廖火炕说:“小伙子,别那么拘束,你干活累着了吧,来,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乐意在机关当兵吗?”
廖火炕没敢挪地方,更不敢往椅子上坐,笔直地站着回答:“乐意,不过,我更乐意当海军。”
“为什么?”
“我爷爷说了,海军打仗是用炮,陆军打仗是用枪,打起仗来打炮比打枪过瘾。我爷爷还说,美国人现在有航空母舰,咱们以后造航空公舰,日他个狗娘养的。”
胖干部和瘦干部都哈哈大笑起来。瘦干部问廖火炕:“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我?文化程度?高中毕业!”
“我知道,你们当中的有些人,特别是偏远农村来的,不管是小学毕业或是初中毕业,入伍时‘文化程度’一栏里都填‘高中毕业’。”
廖火炕红了脸,没敢吭声。
“文化程度低没关系,到部队以后还可以再进行文化学习。”
“是,好助理。”
“你怎么喊我也喊‘郝助理’?”
“我们班长说,部队机关里司令部的参谋多,政治部的干事多,后勤部的助理多,我觉得后勤部的助理都是好助理,没有孬助理。”
“他姓郝,你喊他郝助理。喊我要喊阎助理,我姓阎,阎锡山的‘阎’,知道阎锡山这个人吗?”
廖火炕摇摇头:“不知道!”
“前一段时间电视里有一些很火的相亲节目看过吗?其中有一档节目里有一个女孩子叫闫凤姣,这个人你应该知道,阎助理与她是一家子。”姓郝的助理在一旁对廖火炕说。
廖火炕点点头说:“相亲节目我们都爱看,但是班长让我们每星期只看一次。我知道闫凤娇这个人,她长得很漂亮,就是太傲气,谁都看不上,听别人说她还是个模特。”
阎助理打断郝助理和廖火炕的对话,不满意地对郝助理说:“你以为我们姓阎的没好人了,我说我姓阎锡山的‘阎’已经够难为情了,你把最近争议很大的其他姓氏的人也往我们阎姓里边拉,不是让我更没有面子了吗!”
郝助理反驳阎助理说:“我略懂一些姓氏方面的知识,《说文解字》里有‘阎’无‘闫’,‘闫’是后世俗字,严格起来讲它并不是单独的姓,只是‘阎’的误用简化字。”
廖火炕看到两个助理员在那里打嘴仗,都没有注意自己,捡起拖把就想悄悄地溜走。正在这时,公务班班长蒋正平在办公室门外边喊他:“廖火炕,你这边的卫生搞完了吗?”
“班领导又亲自到第一线检查工作来了,进来坐一会!”郝助理听到外边是蒋正平的声音,便停止与阎助理的口舌交火,笑着招呼他。
蒋正平走进办公室,朝两个干部点点头,笑笑说:“谢谢郝助理,我们今天的卫生还没有搞完,以后有时间了再来坐。你们正在加班,就不打扰了!”
蒋正平说着,扯着刚刚退到门口的廖火炕的衣袖,把他拉出了办公室。
班务会一般都是在蒋正平的宿舍里开,蒋正平的宿舍里放有并在一起的三张三屉桌和七八把椅子,算是宿舍兼会议室。
蒋正平个头不高,身材削瘦,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从外表看,他对班里的战士都一样,不冷也不热,恒温三十七度。用老兵杨彦军的话说,他的优点是工作认真,一丝不苟;缺点是说话随便,有时不着边际。
“今天的班务会,我先讲四个问题——”
蒋正平看到全班九个人都到齐了,坐好了,便开始讲话。
“班长同志,今天的班务会能不能简单一点。”
说话的是中士杨彦军,中士就是以前的二级士官。
杨彦军是公务班战士中的元老,已经在公务班工作了三四年。他本来是机关汽车队的小车司机,因为车辆事故受过处分,发誓一辈子不再开车,才被“下放”到公务班搞卫生的。公务班只有他敢于在蒋正平面前发表不同意见,还时不时地与这个比瘪谷子还要小几级的直接领导出点难题。
“咱们开班务会,我一没有让全体起立,二没有让奏音乐唱国歌,还不够简单呀!我知道你是希望班务会早点开完,好回去给女朋友打电话。”蒋正平对杨彦军今天在几个新兵面前打断自己的讲话不太高兴。
“女朋友的电话早打晚打都没有关系,我主要是觉得大伙工作一天比较累了,开完会好早点休息。”杨彦军狡辩。
“身子累了歇一歇就可以恢复体力,心太累了就会影响工作。杨彦军同志,不是我说你,你和你那个女朋友的关系不要发展得那么快,互相多了解了解没有坏处。我有个老乡,来北京打工五年,在一家公司从送货员干到销售经理,他把老家的女朋友甩了之后,与附近宾馆餐厅的一个女领班好上了,那个当领班的女孩子长得不错,我与她见过一面,一说话脸上就有两个小酒窝,声音甜得让人听了心里发腻。我那个老乡对她,先上眼,再上心,接着上床,最后才知道上当。那个女孩子认识我那个老乡之前,就同小张、小王、小李、小赵、小刘、小马——注意,排名不分先后——等七八个男孩子交过朋友,她的那一份虚情假意,都被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零售掉了,到我老乡这里也只是剩了库存尾货。敢情人家压根就不是要与我的老乡搞对象,而是‘逗你玩’,她把我老乡积攒的六七万块钱花光以后,连手都懒得挥一下,就‘拜拜’了。”
“蒋班长,你看问题有些片面,很多事情不能一概而论,看人也是这样。”杨彦军有些不满地说。
蒋正平听不进杨彦军的话,不屑地说:“现在有些城里的女孩子,从外表看很单纯,其实心眼多得很,跟马蜂窝差不多。她们见了钱不仅仅是眼开,连嘴巴都张得大大的,恨不能从嗓子眼里再伸出一支手来,她们喜欢白马王子,更喜欢‘宝马男’,因为‘宝马’比白马值钱。还有些女孩子虽然真心实意地想找个男朋友,不同于玩弄我老乡感情的那个女骗子,但是态度也很不严肃,朝秦暮楚,见异思迁,今天想着跟姓张的谈,明天想着跟姓王的恋,后天又想着跟姓李的爱,整个脑袋壳就是一个男生集体宿舍,她们不会为我们这些穷当兵的在那种宿舍里安排一个床位。”
“班长同志,不要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你现在对有些问题的认识水平,最多只能与领导我们搞搞卫生相适应,你还是先讲讲今天准备讲的四个问题吧,讲完了我们好回去休息。你讲话时我不再插嘴,我们谈女朋友时你也不要‘插足’。”
“什么是插足,你以为我是在破坏你们的恋爱关系或者是侵犯你们的隐私吗?不对!作为班长,我要知道你们是不是在谈恋爱,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干什么工作,以及对你们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样才能在政治上给你们把住关。我们班现在分心走神的好像还不是杨彦军同志一个人,林长青同志,我最近发现你总是在接女同志的电话,是不是也在谈朋友?”
身材胖胖的林长青是个下士,下士也就是以前的一级士官,由于资历较浅,他在蒋正平、杨彦军等几个老兵面前比较客气。听到班长问话,连忙红着脸说:“报告班长,我与来过电话的那个女孩子说不上是谈朋友,她来北京打工时间不长,我与她是老乡们在一块吃饭时刚刚认识的,只是互有好感而已。”
“什么而甲而乙,互有好感了还不是谈恋爱,我听别人说她姓林对不对?”
杨彦军在旁边忍不住小声嘟囔了一句:“克格勃!”
“对,她叫林玉洁。”林长青诚实地回答。
“你姓林,她也姓林,你们俩是‘同姓’恋呀!她与你是一个县的老乡?”蒋正平穷追不舍,认真地又问。
“我们俩是前后村,相距只有三里地。”
“你们现在不但是‘同姓’恋,看来以后还准备‘近亲结婚’,她是干什么工作的?”
“美发厅的材料组组长。”
“嗬,大小也是个领导干部,你与她一结婚就成了干部家属。”
“不,不,班长,她没有你的官大,也没有你手下的兵多。”
“我这个士官的职务虽然也带个长,但本质还是个战士,不是官。我手下的兵也不多,把你们的名字都刻在木头块上,还不够做一副象棋用的。”
杨彦军听到班长的话越扯越远,夸张地抬起左胳膊,看了看手表,接着又大声地叹了一口气。
蒋正平不满意地看了一眼杨彦军,又一本正经地说:“我过问你们的个人问题,只是想告诉你们,按照部队的规定,战士不准在驻地谈恋爱。我对这条规定的理解是,‘不准在驻地谈恋爱’是指不在驻地与当地的异性谈恋爱,而你们在当地谈的都是从家乡来北京打工的女孩子,这应该是没有违反部队的规定,但是谈恋爱不能影响革命工作。同时我要提醒你们,在婚恋这个问题上要特别慎重,不要过高地估计自己,我们现在虽然在首都北京工作和生活,但是在这里只是‘三无’产品:一无户口、二无资金、三无关系,地方上的公务员,人家那是国家干部;部队的公务员,不过是个勤务兵,干杂活的!”
蒋正平看见杨彦军在不耐烦地皱眉头,便给下滑的话题踩了一下刹车,不情愿地说:“好啦,其他的话不再多说了,现在开班务会,我先讲第一个问题——”
廖火炕这两天心情有些郁闷。
在前天晚上的班务会上,蒋正平严厉地批评了他。“工作时间进办公室与干部聊天”是班长给他定的“罪名”。
廖火炕战战兢兢地解释:“我搞卫生时看到有一间办公室里边的灯亮着,以为是哪位首长忘记关了,就敲了敲门,心想,如果里边没有人,门又没有锁,我就进去把灯关了,结果——”
“问题就出在这里。”蒋正平打断他的话说,“我们的任务是搞好楼道和厕所的卫生,没有义务去管办公室里边的事。没有特殊情况,我们不能随便敲办公室的门,以免干扰干部们的正常工作。如果你发现有的干部下班时确实是忘记关灯或者是忘记锁门了,一般情况下,要先想办法告诉这个办公室的干部或他们的同事,他们如果委托你进屋关灯,你才可以进入办公室,把灯关掉,把门关好。这件事假如以前没有给你们讲过,那是我的责任,记得你们刚来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一次,如果你们的脑袋患了消化不良症,没有理解我讲话的意思,不按我说的去做,对不起,那就要挨批评了。”
“班长,你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听,是我的不对。”廖火炕认真地检讨说。他胆怯地看了一眼蒋正平,又接着往下讲:“不过,我没有与干部聊天,是他们问我话。”
“他们问你话,你可以认真地回答,也可以礼貌地拒绝,前提是不能影响正常工作。我们虽然和干部们都在一个机关工作,但是工作分工不同,地位作用也不一样,他们是栽在盆里的花,我们是种在地里的草。他们的工作时间也是我们的工作时间,他们的空闲时间,有时候还是我们的工作时间,‘战士’这个称呼给予了我们太多的义务,要求我们必须时刻努力做好工作。当然,它也给了我们应有的权利,这我就不多说了。”
蒋正平的话,廖火炕有的听明白了,有的没有听太明白。昨天,他本来想找班长谈谈,请他指点一下自己在其他方面还要注意些什么问题,但是看到蒋正平这一天有点倒霉,用蒋正平自己的话说是“严重的霉气中毒”。早上运气不好,不知是谁在刚拖干净的楼道里扔了一个香烟头,秘书处长看到后,批评他卫生搞得不彻底;中午手气不好,与杨彦军下军棋是下一盘输一盘,被杨彦军戏称为“常败将军”;晚上脚气不好,两只脚丫子痒得他心烦意乱,到处找达克宁;全天的脾气都不好,看到公务班的人就想发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