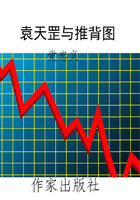听到这个消息,首先着急的是乐化镇大烟馆,因为“徐克扣”欠他们有七百两银子烟债。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他家要是真败了,找谁要钱去?开烟馆的人可不会讲什么情面善心,尽管烟馆老板知道“徐克扣”中风昏迷,还在抢救之中,他也不顾,准备当晚亲自带人到徐家逼债。
夜晚,一盏油灯发着惨淡昏暗的光芒,徐家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欢乐。
徐克扣半死不活半躺在床上。
徐张氏、徐王氏、徐秤砣、徐大宝守候在旁边。
郎中起身收拾起药箱,说:“老太爷是惊吓中风,已经瘫痪,暂时也不能说话。”
徐张氏:“啊!”
徐王氏:“那还能治好吗?”
郎中:“他年纪大了,身子骨又不好,病情很难说啊。”
徐张氏:“啊!”
郎中:“最要紧的就是他再也经受不住惊吓,也不能受气发怒。”
徐张氏点头。
就在此时,烟馆老板和潘管事带两个打手走进来。
潘管事:“有人吗?”
徐张氏和徐王氏走出来。
徐张氏:“哦,是潘管事,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
潘管事:“你说呢?我来要账啊,这还用得着说吗?”
徐张氏:“家里现在确实没有钱啊。”
烟馆老板说:“徐老太太,你家老太爷欠的七百两银子烟债,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你家要是真败了,我找谁要钱去?”
徐张氏:“我家老头子中风昏迷,还在抢救之中,你们现在不能来逼我啊!”
烟馆老板哪管这些,嘴里不干不净地威胁说:“妈的,没钱抽什么鸦片啊?三天之内,还钱便罢,不然,就用你家的房子抵债!”
打手们也在一边吹胡子瞪眼睛。
徐秤砣不服气地说:“你,你怎么能强行霸占别人的房屋?”
烟馆老板说:“借债还钱,杀人偿命,这是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事!嘿,你算什么东西?这儿有你这个奴才说话的份吗?”
徐秤砣气急:“你……”
烟馆老板讥讽地说:“怎么着?你是想替东家还钱吗?那就请你把银子拿出来啊。徐秤砣,舌头打个滚,说句好听的话给东家听,讨主人喜欢,不累人是吗?”
徐秤砣无奈地蹲到地上。
徐张氏只能哭着苦苦哀求:“大老板,潘管事,你们高高手,我明天出去借,一定尽快还账,求你啦。”
烟馆老板说:“好吧,三天,就等你三天,没钱就拿房子抵押!”
烟馆一伙人走后,珠宝商老板又来讨账了。
在客厅,徐王氏无奈地摘下金簪、玉镯、耳环等首饰放到桌子上,对珠宝商说:“我没钱,只能退货。”
珠宝商老板:“你都用过了,那有退货的道理?”
徐王氏:“你要是不要,我也没办法。我家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但要钱是没有的。”
珠宝商老板只好认倒霉,拿起那些金簪、玉镯、耳环等首饰走了。
室内,躺在床上的徐克扣眨了眨眼睛,醒了。
他已经被惊吓得嘴歪眼斜,也不能说话,只能用手指着桌子上的大烟枪直哆嗦。
守候在徐克扣床边的徐大宝看了看他爷爷,急忙喊起来:“奶奶,我爷爷醒啦!”
徐克扣是大烟瘾犯了。
他不能说话,但心里明白,虽然为家中的变故惊惧、恼恨,但不能过大烟瘾的滋味更叫他难以煎熬。五脏六腑,跟虫咬猫抓似的,又是流泪又是淌鼻涕,心内难受得要死。
他说不出话,只一个劲挣扎着把头往床框上死命碰撞。
徐张氏、徐王氏急忙走进屋,来到徐克扣床边。
徐王氏看了看徐克扣,惊疑地问徐张氏:“娘,爹这是怎么啦?”
徐张氏心里清楚,便说:“他是大烟瘾犯啦。”
徐王氏:“啊!”
徐张氏:“我也不忍心看着重病中的老头子受此煎熬,媳妇啊,你还是出去设法借点钱,给你爹买点大烟救急。不然的话,眼看老头子的老命难保啊!”
徐王氏:“娘,如今家中遭难,谁还愿意借钱给我们?我现在到哪里去借啊?”
徐张氏:“孩子,我知道这是难为你了,可救人要紧啊。”
徐王氏无奈,万分为难地出了门。
徐王氏明白,平时自己不拿正眼瞧别人,早就被人嫉恨,现在能到哪里去借?
可是婆婆的话也不能不听,她万分为难地出了门。
此刻天已黄昏,徐王氏走在街上,人们都用异样的眼神打量着她,在她背后指指点点。徐王氏前两天还是个趾高气扬的知县夫人,转眼就变成了羞于见人,见人也无地自容的犯人之妇,那种自卑、耻辱,难以名状。她六神无主走在街上,不由自主地走到原先自家的杂货铺门口,刚想转回,但又停下来。
无奈之下,她只有忍受屈辱,准备向缪大华借钱。
缪大华坐在他的杂货铺里在吸水烟。
缪大华四十多岁,以贩卖耕牛为生,后来盘下徐家的杂货铺经营。他住在徐家隔壁,人长得是相貌堂堂,高大魁梧,可品行却十分下作,白天是人,夜晚是鬼。他对徐王氏的姿色,早已垂涎欲滴,苦于人家夫妻形影不离,他美梦难成。三年前,徐映台外出赶考,有天徐王氏来他家有事,要找缪妻帮忙,不期缪妻恰好外出不在家。缪大华岂肯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就在家中对徐王氏百般纠缠调戏,直到徐王氏翻脸,方才罢休。从此,徐王氏再不理睬缪大华。徐映台放任浙江平阳知县后,缪大华着实不安了一阵子,怕徐映台报复。后经察言观色,知道徐王氏没有把这事说出去,才放下心。为讨好徐家,他又贴钱盘下“徐克扣”的店铺自己经营。
缪大华正准备打烊回家,他放下烟袋,收拾一下货物,一抬眼,楚楚动人的徐王氏来到面前。
缪大华又殷勤又关切地问:“大妹子,唉,你家徐老爷是怎么回事啊?”
一句话问到徐王氏的伤心处,她强忍住没让眼泪流出来,叹口气说:“唉,一言难尽。缪大哥,我想请你帮个忙,不知你肯不肯?”
缪大华:“大妹子,我肯,你哥哥肯,你尽管说。”
徐王氏一声“缪大哥”把缪大华心都喊稣了。他那一双色咪咪的眼睛在徐王氏的奶子上扫来瞄去,目光恨不能穿透她身上的衣服。
徐王氏被他看得甚不自在,她羞丑地低下头:“我想跟你借点钱用。”
缪大华略一愣,随即大方地问:“啊,你要借多少?”
徐王氏感到难以张口,但还是说了出来:“我也不知道,够买抽一顿大烟的就行了。”
缪大华:“够买抽一顿大烟的?哦,我知道了,是不是你们家老太爷的烟瘾犯了?”
徐王氏又羞涩地点点头。
缪大华:“嘿嘿,娘婆二家都讨饭,他还有闲心来裹小脚!都到什么时候了,逼债的把你家门槛都给踏破了,他还要抽大烟?大妹子,你这往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啊?”
缪大华的话,戳到了徐王氏的真正痛处,她不由就流下泪来。
徐王氏叹道:“唉,可不是吗,可我一个妇道人家有什么办法,总不能眼巴巴看着老公公在床上撞头拼命寻死啊?”
缪大华眼睛眨了眨,说:“我看这样吧,大烟馆也不是你们女流之辈们能去的地方,你在这里坐一会,等我,我去给你家老爷子买点大烟,如何?”
徐王氏想了想,苦楚地点点头。说:“是啊,我连大烟馆的门朝哪里?大烟是个什么价钱都不知道,就是有钱也不会买啊?”
缪大华走出柜台,准备到大烟馆去。
他出了店铺,看看街上四下无人,想想又转回身来,嬉皮笑脸放肆地在徐王氏胸前摸了一把。
徐王氏脸一红,忍气吞声没有敢发作。
缪大华心中大喜,哼着小调美滋滋去给她买大烟去了。
几天过去,“徐克扣”的病情丝毫不见好转,反而逐渐加重,大烟馆催债却日见凶狠。
老奶奶徐张氏无奈,媳妇不是管家的料子,她只得自己强撑着当家理事。她一面把家里的两个下人打发走,让孙子徐大宝也停了学,一面叫徐秤砣出去干活挣钱,聊以糊口。
徐王氏何曾过过这样的苦日子?每日里只躲在屋里暗自伤心啼哭。
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
三月初九日,徐映台的女儿徐芳哭哭啼啼回来了。
徐克扣室内,徐克扣半死不活躺在床上,徐张氏、徐王氏、徐芳坐在床沿上。
徐芳哭着说:“当初我嫁在樵舍镇吕家,是因为吕家是看到我爹当了官才托人来提亲的。如今吕家看见我爹下狱,家里欠这么多债,就变了脸,我在吕家毫无过失啊,可他们家居然一张纸把我休了!奶奶,我这还有什么脸见人啊?!”
徐张氏又气又怒:“啊!这吕家怎么能这样翻脸不认人,一点情面都不讲啊?”
躺在床上的徐克扣翻了翻眼,但他说不出话。
徐芳哭泣道:“奶奶,吕家不但翻脸不认人,还想方设法羞辱我。爷爷,你看这叫什么话啊!”
徐芳哭哭啼啼拿出一张休书,展开给爷爷徐克扣看了看。
休书上写的是“徐家人,斜人多于正人”,是以以“徐”字的字体形状来侮辱徐家。
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的徐克扣一看,只气得眼一翻,一口气上不来,顿时一命呜呼。
徐张氏大哭。
徐芳惊惧地大喊:“爷爷!大宝快来,爷爷不好啦!”
外面徐大宝、徐秤砣一起跑进来,见状齐声大哭。
徐家如今是一败涂地加一贫如洗,若非徐克扣的棺材是老早备办的,家里连买棺材的钱也没有。因此徐克扣的丧事,办的也就极其草率。
大烟馆料定徐家是败家了,再也不容拖延,他们把徐家三代的三个女人与一个孩子逐出正房,卖掉徐家的屋子抵了债。
徐张氏带着媳妇、孙女、孙子,无处可去,只好都挤到徐秤砣住的下房里居住。
好在徐秤砣是个老实本分人,又自小在他家长大,生活上各自虽然有诸多不便与尴尬,但总算还能相互照应。至于那些“男女授受不清”的规矩与街坊的闲言碎语,就统统顾不得了。
这一切,缪大华都看在眼里,他觉得把徐王氏弄到手的机会已经到了。
一天,他带了点大米送到徐家,跟徐张氏说:“老太太,你这一家人的日子,今后难道就这样过?你有没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啊?”
徐张氏流着眼泪说:“家门不幸,我是走投无路,六神无主了啊。”
缪大华关切地说:“唉,人到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依我看,你还不如把芳丫头给秤砣做媳妇,他是个老实可靠的人,他要是娶了徐芳,你老人家与小孙子将来也有个依靠,你们在一起住也没人说闲话。”
徐张氏觉得缪大华说的也是个办法,孙女徐芳已经是被别家休弃之女,再难找到好的婆家。而不给徐秤砣一点好处,将来也拢不住他的心。她心里很清楚,徐家现在是一天也离不开徐秤砣。把徐芳嫁给他,倒不失是个两全之策。
只是这不老不少、不能吃苦做事的媳妇徐王氏不好安排。首先,住的地方就难办,白天尚可凑合,夜晚起夜小解都在巴掌大的一间屋内,实在尴尬不堪。
徐张氏是怎么想的,缪大华清楚得很,他进而言道:“徐妈妈,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讲究,你老人家应该及早安排他们小的圆房,你是老太太,你带孙子跟他们一起住,谁也不会说什么。可大宝妈跟你们挤在一起住,难免别人说闲话啊。”
徐张氏无奈地说:“我知道啊,可我又能怎么办呢?”
缪大华慷慨地说:“我先借间屋子给她住。日后你儿子能回来更好,若是不能回来,她愿意守就守,不愿意守随她自己做主。我看她在家除了吃,什么也不会做。我这是为你老着想,老邻居嘛,你一家人这样活受罪,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还能怎么办?现在只剩这条路还能走。因此,老太太徐张氏还十分感激缪大华能急人之难,在雪中送炭。
嘉庆十四年春,景禄、吴俊、舒灵阿、张润四钦差离开温州,经过两个多月的行程,在四月底回到了京城。
嘉庆很快在乾清宫召见了景禄、吴俊、舒灵阿、张润四钦差,特克慎与刑部尚书亦遵旨旁听参议。
景禄把平阳县徐映台私加田赋,温州府杨大鹤谎报“民变”,总督阿林保行文平乱,后发现有误又复查纠错,杀庄以莅、许鸿志以平息事态,以及林钟英家的冤情和告状经过,滴水不漏地向嘉庆禀报了一遍。并把对涉案人犯的判决,与对失职官员的处置也一一作了禀报。
听完复奏,嘉庆气得半晌没有说话。
众人谁也不敢先开口。
正好这时候内侍禀报:“启禀万岁,闽浙总督阿林保在宫外候见。”
嘉庆听后,轻轻哼了一声。说:“不见,叫他后日早朝在太和殿听宣。”
看了一眼身边忐忑不安的几位大臣,嘉庆没好气地说:“你们也跪安吧。”
众人大气也不敢出,小心翼翼地退了出来。
来到在宫外,特克慎正要上轿,却被景禄喊住:“中堂大人请留步。”
“侍郎大人有何见教?”
“能否借个地方说话?”
特克慎说:“那就到我家去喝杯清茶如何?”
“恭敬不如从命。”
特克慎的府邸离皇宫不远,不一会就到了。
在特克慎书房里,景禄拿出林钟英要他带给特克慎的那方砚台,说:“下官有方宝砚,要请中堂大人鉴赏。”
特克慎一看,立即爱不释手:“好东西,好东西啊!你的?”
景禄笑而不答,故意问道:“好在哪里?”
特克慎不悦,道:“前朝末年南京秦淮名妓柳如是之砚,她写的铭文,她丈夫钱谦益亲笔书写,落的有款,你还能不知道?问我?”
景禄笑道:“果然是大家法眼,佩服佩服!既然大人喜爱,那就送给中堂大人,也算是物得其所。”
特克慎自然不相信有这样便宜的好事:“真的?”
景禄干脆得很:“真的!”
“不许后悔?”
“不会后悔!”
特克慎玩笑道:“那我可就不客气了,笑纳。”
景禄却认真说:“那我可就要告辞了,慢送。”
这下,特克慎却急了:“哎,哎!别慌走啊,你真舍得送我?”
景禄一笑,说道:“本来就是人家送您的。下官只不过是受人之托,代为转递而已。”
“谁?是谁人叫你把这方砚台送我的?”
“林钟英。”
“林钟英?!”
“对。他十分感激大人为他家伸张了屡告不通的冤情,下官临行时,他托下官带来这个砚台,要我转送于大人,聊表他全家的感激。”
特克慎连忙推辞,说:“不可不可,平冤除恶,我之职分,焉能受礼?谢谢他的美意,请你将原物退还给他。”
“林钟英说了,这东西留在他家,只能给他带来灾祸,执意要送给您这位大恩人。”
“不可,此例不可开。”特克慎正色道:“侍郎大人,我不收此砚,受理他家的案子是为公,问心无愧。收下此砚,便是怀私,就玷污了我的清白!”
景禄早就想到这层,说:“中堂大人别把话说得这样严重,下官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请教。”
“此物价值不薄,放在林家未必是件好事。日后谁也不敢说就没有宵小见财起意,铤而走险杀人越货,反会给他家带来祸端。依下官之见,中堂大人可以把这方砚台买下来,既领了林钟英的情意,也给他家以实惠。因为是买的,那您就是心迹双清,任何人无可非议。”
“嗯,嗯,有道理,好办法!你别着忙走,你得给我做个见证。我这就把钱给你,你再把钱交给林培厚,由他转交给林钟英。”
景禄笑道:“好好,您不就是要我做个证吗?下官乐意做这个见证。”
特克慎正色说:“这事当然要有证人!不过,历来这种东西也没个正价,咱们也别麻烦请人估价了。我给他家三千银子,他要是说多了呢,权当是我的馈赠。他要是嫌少呢,给个数目,我愿意再补上。”
“好好,就这样办。您啊,也太认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