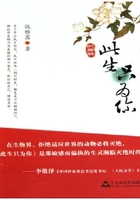钦差们刚刚把林钟英一案诸事安排停当,在堂上与朱理和廷潞商谈善后事宜。
景禄对朱理和廷潞说:“二位大人,林钟英一案,基本审判完毕。我等不日就要返京,向皇上复命。遗留案犯对林家赔偿一事,还要请二位大人帮忙操心督促办理啊。”
朱理:“这些事情,钦差大人尽可放心。”
廷潞:“钦差大人,廷潞一定将功折罪!”
景禄:“好,那就辛苦二位啦。”
正说着,一衙役进来禀报说:“启禀钦差大人,朱宇泰不服判决,要面见钦差大人陈情。”
景禄:“不见。”
衙役:“是!”
衙役退下后,景禄说:“刚才在堂上,看杨大鹤的模样,似乎像是疯癫了啊?”
吴俊:“是啊,假如他要是疯了,就得改判啊。”
舒灵阿:“可历来获罪后的那些官员们就有装疯卖傻,企图蒙混过关的例子,谁现在能敢断定杨大鹤是真疯假疯呢?”
张润:“算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们就认定他是装疯。”
此时,刚才那个衙役又进来禀报说:“启禀钦差大人,朱宇泰在押回的路上大闹,说有要事大案,要面陈钦差!”
景禄无奈,说:“带朱宇泰!”
朱理与廷潞说:“大人,我等告辞回避。”
景禄:“朱大人与知府大人但坐无妨,有些善后事宜,还须要与二位大人商量。”
两衙役押朱宇泰进来,把他按跪在地。
景禄看着朱宇泰,厉声喝问:“朱宇泰,你为何不服?有何要事大案要向我们钦差陈诉?说!”
朱宇泰看看朱理,一咬牙,恶毒地说:“启禀大人,犯官查抄林家,实乃是按察使朱理大人私下授命唆使!”
众位钦差情不自禁同时惊讶地“啊”了一声。
意外生变,钦差们与廷潞闻言,都大吃一惊。
倒是朱理微笑着端坐在一旁,似是此变已在意料之中。他十分庆幸自己已经老早做好了防范,否则,这一下必定要栽在朱宇泰这只疯狗身上!
景禄把惊堂木一拍,对朱宇泰厉声喝道:“大胆!朱宇泰,诬陷朝廷命官,罪加一等!”
朱宇泰是打算破罐子破摔,准备临死拉个垫背的,所以也不害怕。他阴测测地说道:“钦差大人有所不知,只因按察使朱理朱大人看中林家一方古玩宝砚,他欲占为己有,便命下官查抄林家,为他夺得此砚。犯官身份卑微,不敢不遵命办事。”
景禄厉声问:“你有何证据?”
朱宇泰:“林钟英家的那方砚台就是铁证!”
景禄:“啊!此砚现在何处?”
朱宇泰:“就在朱大人家中。”
朱宇泰话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疑,钦差们一时也难辨真假,把目光一起集中在朱理身上。
景禄看看朱理,只见他神色自若,不像象是心虚理亏的样子。便问:“朱大人,对此你有何话说?”
朱理坦然言道:“朱宇泰言之凿凿,下官已是被告。只请众位钦差大人问问原告,我如何授命给他?又怎么唆使于他?是私下口授?还是命人传话?抑或是行文?各位大人只管秉公审讯,大可不必再问下官。”
景禄点点头,问道:“朱宇泰,你说是受朱大人之命,有何为证?”
朱宇泰:“朱理私下亲口交代于我,没有证据。”
这一下,真使钦差们为难了。
朱理笑道:“下官以为,众位大人可以问问他,我是在何时何地跟他说的?怎么说的?”
“着啊。”吴俊这时忍不住问道:“朱宇泰,我来问你,朱大人何时何地交代于你?说!”
朱宇泰不假思索地说道:“时间是在查抄林钟英家前四五天的时候,地点是在驻温州的臬司衙门里。”
朱宇泰把话说得有鼻子有眼,叫人不能不信。
朱理笑笑,说:“众位钦差大人,下官能否说话?”
景禄道:“朱大人请讲。”
朱理道笑:“呵呵,按朱宇泰刚才所说,那就是十二年六月初、五月底的事了?众位大人,当年六月初五月底的时候,下官清楚地记得我当时是与巡抚清安泰在一起,遵照工部的行文在巡视钱塘江大堤。我们两人足足在大堤上忙了半个多月,巡抚清安泰大人即可为下官佐证。温州与杭州相隔千里之遥远,下官分身无术,怎可同时出现在温州?再说,在下也是一方大员,公干行踪具有记录,请众位大人调集臬司衙门案卷,一查便见分晓。”
朱理有力的驳斥,已经使朱宇泰头上冒出冷汗。
但朱宇泰依然狡辩说:“那要么就是我记不清时间了,反正就是你亲口交代我的。”
朱理依然是一副微笑:“朱宇泰,你是在六月初犯事的,可本官只在当年六月底与八月中受巡抚清安泰委派来过温州两次,这两次时间都是在你事发之后!第一次来,是来襄助百龄复查所谓‘民变’之事,被百龄坚辞,我当即就转回杭州了。第二次是八月间为林家祖孙二人验伤,这两次都有案可查。在这之前,本官当年没来过温州,与你素不相识,别说亲口交代,就是面也没见过。朱宇泰,你不觉得你这样说太愚蠢吗?”
朱宇泰索性一口咬定:“反正林家的宝砚现在就在你家,那就是铁证!”
景禄问:“你说林家宝砚在朱大人家中,有何证据?”
朱宇泰:“是我亲手交给他的。”
朱理正色道:“钦差大人,下官尚未回家,为正视听,请众位大人速速派人到下官府邸搜查,以明辨是非。”
景禄说:“朱大人,莫要动怒,此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会问个明白的。”
朱理道:“全赖大人做主。不过——下官倒是听闻,说朱宇泰多次在人前吹嘘,说他家中藏有一方非常值钱的古砚,只是我并不以为然。现在看起来,说不定他还真有此宝,只不过他说的那方古砚,想必就是抢夺林家的了?”
景禄命道:“来人!”
众捕快:“在!”
景禄:“速去朱宇泰家中搜查,仔细看看有无林家的古砚!”
“是!”
众捕快领命而去。
朱宇泰冷笑着说:“搜吧,搜不出来怎么说?”
吴俊喝道:“放肆!不问不许说话!”
不大一会,众捕快便获赃而回。
班头手捧一个布包禀告说:“启禀众位钦差大人,小的们在朱宇泰家中搜出古砚一方。”
朱宇泰一听,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景禄:“打开验看。”
班头何常贵打开布包,里面果然是一方古砚!
朱宇泰再一看,几乎气得晕死过去,原来此砚正是自己从林家抢来,后又送给朱理的那方柳如是的砚台!
吴俊:“林钟英走了没有?”
何常贵:“没有,正在前面账房跟钱谷始业验对失物清单呢。”
吴俊:“好,速令林钟英上堂认证。”
何常贵传令:“林钟英上堂认证啊!”
林钟英走上堂一看,跪见钦差:“学生林钟英拜见钦差大人!”
景禄:“起来吧,你看看这方砚台,是不是你家的东西。”
林钟英一眼就认了出来,他对景禄说:“这正是学生家的古砚,是被朱宇泰抢去的。”
景禄喝问:“朱宇泰,你还有什么话说?”
朱宇泰大叫:“朱理栽赃!朱理栽赃啊!”
景禄大怒:“来人,将朱宇泰狠狠掌嘴五十!诬陷朝廷命官,罪加一等,将其家产房屋,全部充公!”
众衙役上前,七手八脚立时把朱宇泰打个死去活来,拖了下去。
景禄:“林钟英,你可以把这个砚台带回家了。有关索赔事宜,以后就由温州知府廷潞大人督办,有事情你找他就行了。”
林钟英:“多谢钦差大人。”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朱宇泰哪里能料到,朱理早就暗地里安排好人手,悄悄把这个祸根,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回到朱宇泰家里去了。
朱宇泰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家产房屋充公,家人的生活立即就没了着落,这也是恶有恶报。
林钟英手捧如是砚,喜滋滋回到家中。
他家里大多数的家具都已复还原位,只是客厅中堂供桌上新供奉一个“皇恩浩荡”的牌位。
林温氏带着孙女林咏莲正在在烧香。
林钟英放下手中的如是砚,对母亲笑着说:“娘,今天钦差将如是砚交还给我了,还说以后理赔的事情可以直接找知府廷潞。”
林温氏:“皇上圣明啊。”
林钟英笑道:“娘,你现在不敬菩萨敬皇上啦?”
林温氏严肃地说:“钟英,皇上、菩萨都要敬的。”
林钟英笑笑,说:“特克慎大人是我家的第一大恩人,我家也没有什么可以孝敬他的东西,他喜欢写字,娘,我想把这个砚台拜托钦差景禄大人转送给他,你看行吗?”
林温氏:“行啊,是应当好好谢谢人家啊。”
林钟英:“这个砚台值很多钱,又是祖上传下来的,你不心疼吗?”
林温氏:“有什么可心疼的?”她一把搂住小咏莲,含着眼泪说:“世界上,只有亲人才是最值得心疼的啊!再说,留着这个砚台在家,说不定以后还是个祸害呢。”
在温州知府衙门大堂里,景禄、吴俊、舒林阿、张润四钦差即将回京,正在安排朱理和廷潞善后。
四钦差坐在左上首,朱理、廷潞坐在下方。
景禄说:“按察使、知府大人,我等钦差已经办好了皇上交下来的差使,想早日回京向皇上交差。留下的一些善后事宜,就交给你们办理啦。”
朱理道:“钦差大人放心,这是我们应当做的。善后事宜,由温州府廷潞大人督办即可。”
廷潞说:“卑职一定尽心竭力。”
景禄:“好,请知府大人按照林钟英提供的清单与四邻证词,与案犯朱宇泰、蔡廷彪、黄升等三人逐一核对,强行向他们索赔。三犯有物退还,无物赔钱,没钱就变卖案犯家中的物品返还给原告,决不能姑息手软。”
廷潞:“是。”
一衙役进来禀报说:“林钟英在外面求见钦差景禄大人。”
景禄:“叫他进来。”
衙役:“是。”
不一会,衙役把林钟英领进来。
林钟英来到堂下,拜见说:“学生林钟英,拜见各位大人。”
景禄客气地说:“免礼,起来说话吧。”
林钟英:“谢大人。”
景禄问道:“林钟英,我等即将回京,你还有什么未了之事吗?”
林钟英感激地说道:“学生家中之冤,感蒙天恩,与四位钦差大人的垂怜公断,万死也难以图报。惟有每日烧香磕头,祝福各位大人康寿,祈祷圣安国泰而已。只是特克慎大人与学生素不相识,他能不嫌弃学生卑微,以大局为重,秉公执法,不计得罪权贵阿林保,接状后上呈御案,才使学生家中冤案,得以伸张。学生感恩戴德,无以为报。我家中也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这方砚台也是失而复得的身外之物,学生想把它送给特克慎大人作个纪念,望钦差大人成全。”
林钟英说罢,从怀里拿出那方柳如是的砚台呈上。
景禄含笑点头,说:“你之美意可嘉,只不过我们都知道,特克慎大人一向不收任何人的礼物,这事却有点难。万一我们把这方砚台带到京城以后,他要是坚辞不受,我等奈何?”
林钟英道:“大人,学生知道特克慎大人喜爱把笔临池,区区文房之物,能算什么礼物?这不过是学生的一片心意。特克慎大人要是不收,岂不是拒绝了学生的感激之情?再说,此物在学生家中,只能遭人觊觎,引来灾祸。特克慎大人的笔尖,能横扫妖魔鬼怪,能超度冤屈良善,它摆在特克慎大人的案头,物归其主,还望大人成全。”
景禄见林钟英说得恳切,笑道:“好吧,你既然如此执著,我就送去试试。万一特克慎大人拒收此物……”
他想了一下,接着说:“我就把它交给你族兄林培厚,请他再转交给你,你意下如何?”
林钟英闻言大喜:“如此甚好,学生不胜感激。”
嘉庆十四年正月底,景禄等四钦差在百姓们敲锣打鼓的欢送下,踏上归程。
廷潞此时哪里还敢怠慢,按照林钟英提供的清单与四邻证词,多次与朱宇泰、蔡廷彪、黄升等三犯核对,强行向他们索赔。三犯有物退还,无物赔钱,没钱就变卖案犯家中的物品,三下五除二,就把林家索赔事项办理得头头是道。
办公闲暇,张敬凯对廷潞感慨说:“这朱理大人可真厉害,林家的案子在他手上推委堂塞了几年,这次居然他能毫发未损。”
廷潞:“敬凯兄,我最不明白的一件事,就是朱宇泰怎么会突然咬起他的堂兄朱理朱大人呢?”
张静凯点破说:“我心里琢磨着,他们根本就不是一家人。”
廷潞:“嗯,有可能。”
张静凯:“当初朱理维护朱宇泰,一定是因为他收了朱宇泰从林家抢来的那方砚台。后来事情被林钟英弄大,居然惊动了皇上,派钦差大臣来办案了,这样,朱理怕生出事端,引火烧身,显然在事先做了手脚,偷偷叫人把那方砚台放回到朱宇泰家中。”
廷潞:“哦,有道理。”
张敬凯:“而朱宇泰本来就是条疯狗,看到朱理保不了自己就乱咬,但他根本料不到朱理早就做了补救。否则朱宇泰也不会那样蠢笨,明明东西在自己家里,他焉能当堂指证是在朱理家里?他岂能不知道诬告反坐的道理?”
廷潞这才恍然大悟,原先对恩人朱理的百般崇敬,转眼化为乌有。
他叹道:“唉,这官场真正可怕,人心难测啊。现在看起来,当初总督阿林保对我说‘平阳的事要息事宁人’是指‘民变’的事情,而不是指林钟英家告状的案子。”
张敬凯:“是的,他才不会把一个老百姓的冤案放在心里呢。”
廷潞:“唉,真没意思。乌纱帽下,如履薄冰啊!”
张敬凯:“自古官场如战场啊。”
廷潞对张静凯说:“张先生,说实话,别说我现在是在降级待参,就是上峰继续还叫我做这个知府,我也不想再做这个官了。”
张敬凯:“怎么?大人心灰意冷了?”
廷潞:“是的,别看我表面上严厉,但骨子里很胆小。说实在话,我已经心灰意冷,有了退隐之意。”
张静凯对廷潞的灰心丧气并不感到奇怪,便说:“怎么说呢,历来官场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想做好官,就别做好人,要想做个好人,就做不好官。”
廷潞:“是啊,但当官是一时的事,做人却是一辈子的事。咱别在这肮脏的地方混长了,到老了不会做官不说,最后连做人都不会了!我看,还是急流勇退的好。”
张敬凯:“大人有什么打算呢?”
廷潞:“不如做个生意,心里踏实。我家里原来就是开饭馆的,我在军营时管的也是火头军。我想辞官不做,到杭州租赁个地方,开个饭店,图个心里清净。”
张敬凯:“大人已经想好了?真不留恋官场了?”
廷潞:“我想好了。”
张敬凯:“也好,你当掌柜,我做账房,在哪我都帮着你。”
廷潞:“好啊,就这样说定了。”
徐映台一获罪,身边原先还指望他能东山再起的几个狐朋狗党,立刻树倒猢狲散,谁也不再去关心他的死活,纷纷各自离去。只有他从老家带来的仆役徐秤砣忠心不改,几次想来看他,奈何被狱卒挡驾。
嘉庆十四年二月初这天,徐秤砣又来到大狱探望徐映台。
在大狱门口,徐秤砣再三向狱卒求情。
徐秤砣:“大哥,求你了,就让我进去看看他吧。”
狱卒:“不行,要想看徐映台,除非你有银子。”
徐秤砣:“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那有钱给你啊。”
狱卒:“那就别看他。”
徐秤砣:“大哥,我是个孤儿,从小被徐家收留长大。如今主人犯法,就要被流放到关外,我也不能跟着他去,只得准备转回江西老家。大哥,我是来向主人辞行啊,你行行好啊。”
狱卒动了恻隐之心,说:“唉,好吧,这年头,你这样的忠厚老实人也少见啦!”
许秤砣:“谢谢大哥,我家主人在哪个号房啊?”
狱卒:“进门向右,第十三号。”
十三号牢房里,徐映台蓬首垢面,狼狈不堪。平日养尊处优已成习惯,一下变成苦不堪言的阶下囚,徐映台只求苟活不死。
铁窗下,他每日以回味往昔与爱妻在一起恩爱承欢的情景,来自欺欺人地打发时间。
一见徐秤砣,徐映台心里也后悔以前不该不听他的规劝。
地对徐秤砣说:“唉,良药苦口,可惜,现在悔之晚矣!”
徐秤砣苦幽幽地说:“老爷,我在温州已经无亲无靠,又不能跟你去关外。老爷,我要回南昌老家啦。”
徐映台:“唉,好吧,秤砣,你赶紧回去告诉我家里的人,要他们无论如何要务必速速派人到乌拉给我送点钱和棉衣。关外乌拉天气甚是寒冷,我手中没钱,日子将怎么过啊?”
徐秤砣:“我回去向老太爷说就是,但他们又哪来的钱啊?”
徐映台:“有有,家里还能没钱吗?我不是带回去好多钱吗?”
徐秤砣:“好吧,我回去说就是。老爷,你要多保重啊!”
徐秤砣大哭。
徐映台:“去吧,去吧,流眼泪又流不出银子,哭管什么用啊?”
徐映台的老家在江西南昌乐化镇。
自从徐映台取得功名放了浙江平阳知县后,这个小镇上的普通商人之家立刻就被人另眼相看。
他的父亲徐可畴原先在镇子上开个杂货铺,在买卖上喜欢克斤扣两,人送外号“徐克扣”,可如今人们都尊称他为徐老太爷。徐映台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爱妻徐王氏,也不折不扣是个知县夫人了。
全家的那种得意,不言而喻。
徐映台在上任当年,即嘉庆十二年,曾经叫徐秤砣专程送三千两银子回家,把一家人乐得眉开眼笑,心上开花。他父亲“徐克扣”为了与自己现在老太爷的身份相符,也不做生意了,把经营了几十年的杂货铺盘给了邻居缪大华,自己在享起清福。
徐映台的爱妻徐王氏则在家挑绫罗、拣绸缎,整日介做衣服,涂脂抹粉打扮自己。儿子徐大宝刚进学堂,母亲徐张氏虽是个勤俭过日子的人,却不当家,家里一切是“徐克扣”说了算,没她说话的份。因此,徐映台家里的日常开销,钱花得像流水似的。
嘉庆十三年这年,徐映台整整一年就没带钱回来。“徐克扣”几次带信到平阳找儿子要钱,但徐映台仅带回寥寥几文,根本不抵用。
“徐克扣”为了炫耀身份,在缪大华等一帮小人引诱哄骗下,也赶时髦学会了抽鸦片,没几次就上了瘾,以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
鸦片烟可是一般人抽不起的玩意,许多人为此倾家荡产,“徐克扣”依仗有个当县官的儿子,每日在芙蓉膏下麻醉销魂,欠下一身烟债。此时,他并不知道徐映台已经革职待参,只以为是宝贝儿子公务繁忙,无暇顾家。因此,全家照旧过着只花钱不算账的美日子,没钱就借、就赊账,别人也不怕他不还,毕竟他家还有人在外面当着县官呢。
只不过那徐王氏正在如狼似虎的年龄,暗地里有些个按捺不住,但她也不敢越轨,只能隐忍等待丈夫回来。
嘉庆十四年二月中旬,镇上大烟馆潘管事来到徐映台家。
室内,徐克扣正躺在床上拿着烟枪吞云吐雾。
潘管事走进来,对徐克扣不客气地说:“徐老太爷,你不能老是让我为难啊?你什么时候还钱?给句准话行不行?”
徐克扣不屑地说:“瞧你这认钱不认人的样!我给,我就是卖房子典当衣服,也还你钱,行不行?这话算不算是个准话?”
潘管事被徐克扣抢白的有点不好意思,说:“徐老太爷,不是我说话不中听,我们做小生意的人也难,这你是知道的,你担待点啊。”
徐克扣把眼睛一瞪:“你潘管事的意思,是本老太爷原本就是个做小生意的人?是吗?”
“不敢不敢!”潘管事伸手“叭”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说:“徐老太爷你千万别多心,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徐克扣说:“好啦,好啦。过两天我儿子一带钱回来,首先我就先还你的烟账,好不好?”
潘管事:“好,好!”
正说着,徐秤砣背个包袱,疲惫不堪走进来。
他一进门,便跪倒在地上,悲戚地说:“老太爷,秤砣回来啦!”
徐克扣吐口烟雾,也懒得起身,只抬抬头,把眼皮眨眨,说:“秤砣,你回来啦,回来的正好,你家老爷让你带了多少钱回来啊?”
徐秤砣放声大哭:“老太爷,哪里还有钱带回来啊,我这一路都是要饭回来的啊。老太爷,老爷差点就没命了啊!”
“啊!?”徐克扣这一惊非小,一翻身,坐了起来。惊问:“怎么了?你家老爷怎么了?”
徐秤砣:“老爷他犯事啦!正月初六老爷就被巡抚大人派兵给五花大绑抓到温州,现在被皇上派来的钦差给判了重刑,已经给发配到关外乌拉终身充军去啦!”
潘管事大吃一惊:“啊!”
徐映台的母亲徐张氏和妻子徐王氏也急急走进来。
徐克扣闻言大惊失色,他惊慌地问:“为什么?!”
徐张氏和徐王氏只吓得面面相觑。
徐秤砣:“究竟是为什么事,我也不十分清楚,只听说是为了私加皇粮田赋与什么谎报民变的事,现在已经被发配到关外戴罪充军。还听人说,皇上没砍老爷的人头,已经是万幸!”
徐克扣听罢,头一歪,眼一翻,屁股一撅,当场口吐白沫,浑身颤抖,霎时间被惊吓得不省人事,昏了过去。
徐秤砣急得高声大叫:“老太爷!老太爷你醒醒啊!”
徐王氏一听,愣了一下,“哇”地大喊一声,跌坐在地下。
她又拍胸脯又捶腿,呼天喊地大哭起来:“天哪!这怎么得了?这以后还叫我怎么活啊!”
徐张氏:“秤砣,快,快去请郎中!”
潘管事眼珠子转了转,急忙走了。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只半天工夫,整个乐化镇都知道徐家那个在外当官的儿子犯了大法,已经被发配到关外充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