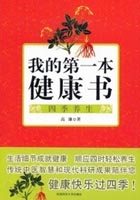“坐吧!”明珠拍拍炕沿,又摆手示意命性德退下,忙问道,“到何桂柱府去会文了?施愚山他们怎么样?李光地和老何是邻居,也该顺便去瞧瞧嘛!”
徐乾学“啪”地打火,呼噜呼噜抽了几口烟,方笑道:“何桂柱夫人殁了,前头的丧事办得热闹,后花园里也会不成文,说了一会子话就散了。这两位先生不比大佛寺的那两位,施、杜二人倒是挺欢喜的。还说:‘便是取不中也不枉来京师这一遭’——这还有什么说的?晋卿那里倒是去了,架子大得很,不见!说是杜门思过——其实我心里也有数,陈梦雷已经交大理寺审过,估摸万岁还要御审他们二人这件官司,他不过是躲躲嫌疑而已。”
“好嘛,当了大学上,只等着入上书房宣麻拜相了!”明珠撇嘴儿一笑,“万岁的口风怕是不再审了。不过他想杀陈省斋倒是真的,须知天下不如意的事多着呢!告诉你,皇上已密地召见了陈梦雷。又问我该怎么处置。你想,他和晋卿两个人的事,死无对证,人是好乱杀的?陈省斋那么好的学间,皇上素来爱重,我请皇上发落他去奉天,过两年风头过了再调回来就是了。”“这案子是没法审。”徐乾学眯缝着眼笑道:“大理寺审他,听说只问了一句就退堂了。”明珠诧异地问道:“那怎么会呢?”
“他们问,‘陈梦雷,你为什么要在耿逆精忠叛军中做官?’”徐乾学道,“陈梦雷说,‘是皇上于康熙九年十月十日当面派的差使!’——再往下还怎么问?”
“于是乎就散了?”明珠不禁纵声大笑,徐乾学赔笑道:“他们总不能把皇上提到大理寺对质吧!”
两个人正说笑,老王头抱着一大叠红拜帖进来,恭恭敬敬呈放在桌子上,却身慢慢退了出去。明珠知道这都是馆选官吏不知通了多少关节才送上来的,此时他不想看,因见徐乾学要辞,使道:“把这些帖子带出去璧还了他们。要捐官的成千上万,谁不想补缺?都这么来求我,我就是千手观音也办不及——告诉他们到吏部去挨号儿候着!”
徐乾学接了帖子,颇有些犯嘀咕:这些捐官人不知花了多少银子才走到这一步。只求明珠见一见都不成。我何必去做恶人他沉吟着,将一封封帖子在手里倒换着看。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竟有父母给儿子起这样名字的!徐乾学读书多年,却没这样的见识,真乃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明珠接过来看时,只见这份帖子上端端正正写着“徐毯毛恭叩明相万安”的字样,不禁也捧腹大笑,便叫老王头出去传话:叫这姓徐的进来,其余的半个月后再见。徐乾学生怕明珠再给什么难办的差使,一躬身辞了出去。
片刻,一个方面阔口的官员摇着快步走来,穿着八蟒五爪袍、缀着白鹇补子,水晶顶戴,在天井里打了马蹄袖,叩了头,报了职名。
“嗯。”明珠半仰在椅上,强忍了笑,双手把玩着他的帖子,扯着官腔说道:“进来吧!你是捐的官?”
“是。”那官员敛容答道,“卑职康熙十四年捐的县丞,渐次进为知府衔……哦,这次进京,家父命家兄带了一方好砚,敬献中堂,伏望哂纳……”那官员一边说,一边从怀中取出四四方方一个红凌包儿呈上来。
明珠接过来,手被压得往下一沉,心知必是黄金所铸——却并不急于打开来看。只漫不经心将“砚”放在桌上,说道:“知府的出息已是很好的了,为什么还要钻刺门路?”“中堂明鉴:下官图的是能光宗耀祖,为皇上出力!”明珠笑道:“你这人看来还伶俐。不过我看还得加上一句,也得在任上好生替百姓做点好事,补缺的事嘛,等吏部司官送上票拟后自然会有消息的。”
“谢中堂!”
明珠见他端杯呷茶,知道他要退下,便笑道:“你不要忙。我看你像是读过点书的,为何取了这么一个名字,这怎么能进呈御览呢?”
“卑职排行属‘球’字辈儿,因命中缺水,所以家祖特为起名‘球壬’。”徐球壬莫名其妙地说道,“不知为何不便呈交皇上?”
明珠听了,方知他原叫“徐球壬”,但不知是谁在“球壬”二字上各添了一笔,变成了“毯毛”,当下也不便说破,只笑了笑,问道:“这帖子,你是交给哪个书吏呈进来的?”
“不是书吏,”徐球壬忙躬身赔笑道,“是府上一位姓高的先生正好到书吏房,接了卑职的帖子……”
一切都明白了,又是这个高士奇在捉弄人!送走徐球壬,明珠不由一阵阵光火。什么“羯鼓四挝”、什么“高出杜上”,他竟是逢人就捉弄;必定是高士奇接了徐某的银子,又恐自己心绪不好不肯接见,才一弄出这个笑话儿来。想着,不由一阵寒森森的冷气直袭明珠心头。他倒不在乎自己挨骂,叫人心寒的是此人如此洞悉自己的脾气,玩弄自己于股掌之上!想想此时也无良谋整治高士奇。明珠的眼神黯淡下来,一言不发将帖子撂在一边,咬着牙自语道:“我偏不给姓徐的补缺,等着他咬你吧!”
高士奇却不知道他离府这一天多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在南西门花市支走徐乾学和性德是有缘故的。因为他见到芳兰带了个丫头正到槐树斜街白衣观去烧香。大约家中生意好转的缘故,芳兰出落得越发水灵标致了。上身着一件盘蝴蝶结扣儿绣花水红小袄,外套杏黄丝绵坎肩,下头着的百褶裙子却是葱绿。高士奇眼巴巴瞧着小竹轿一悠一悠地过去,自己在后边不远不近地跟着,心里暗忖:“论身份,当然不及陈天一那位;说到风流小巧,却足强过一百倍!呸,什么大家闺秀,国色天香,哪及得上这样小家碧玉么?”
眼见芳兰在庙前旗杆旁下了轿,一主一仆在阶前水盆里盥了手,高士奇几步抢过去,不等丫头泼水,慌忙就着残水也洗了手,却似忘了带手帕,扎煞着湿淋淋的手发征。
“这不是高先生么?”芳兰一转眼,见是高士奇,又惊又喜,忙蹲了个方福,抿嘴笑道,“您吉祥!这些日子不见,您比先前气色好多了——梅香,把我的帕子拿给高先生擦手!”
这几声莺语燕呢、娇婉春啼,再加之笑靥如晕、流眄似波,几乎酥倒了高士奇。他一边打着主意,一边慢慢擦着手问道:“你怎么……也到了这里?”因读书人极少到观音庙凑香火,这句话本该是芳兰问的,高士奇抢先这么问,倒把芳兰问了个怔。眼见高士奇擦完了手,将帕儿抖抖,竟塞进自己袖子里,芳兰不禁腾地红了脸,心头突突乱跳,慢慢低下了头,半晌没言语。那梅香却嘴快,在旁代答道:“刘掌柜的把姑娘许了东门胡家,才过了聘就听说胡家少爷得了痨病,催着姑娘过门冲喜……姑娘过来是给观音菩萨还愿的……”
高上奇听到“许了胡家”,头“嗡”地一响,后头的话已一字不入,便是一桶冰雪水淋下,也没有这般的冷。他打了个寒噤,半晌才回过神来,勉强笑道:“……那也是该当的。你们且去求佛,我到那边随喜。一会儿出来我还有话说……”
看着她们进了庙,高士奇在石阶上坐下,抱膝仰脸想了半日,仍觉得事情棘手,妙计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