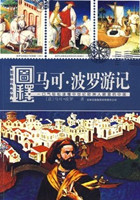他需要一个敢为枝上枝头铤而走险的婢子,以这点来说,他喜欢她。
他也知道必须尽快说服自己恩宠绢儿。最好是如他作出的伪象那般,真心宠溺她。
如此一来,假的变成真的,他也不必觉得对这每一个人都要演戏的自己——很是凄凉。
“你们便等着看,安康城的好戏……”
黑暗中,陈齐将自己裹于锦被中,不让真心之言传出去。
“谁说享王不能问鼎九五至尊之座!”
“孤要让你们看看……我也能当上皇帝!”
红尘中种种纷杂,逃不过天上两双眼。
冥虚冠人与雪睨冠人透过冥虚幻镜,一整日观察紫荆行径,见得此事全貌,却不想听到了惊天秘密——早就不问世事的雪睨冠人,竟是后陈之乱的起因。
因而,冥虚冠人对陈齐那一句“成也因她,败也因她”啧啧有声。
“成也因她,败也因她,亏那小子说得出口……可见世人对女子何其苛责!”
“师妹不必如此!”
雪睨冠人眼里波光潋滟,语气却是极为不耐。“我是倾国祸水!天下总有人因我而受罪,师妹何必替我开脱!”
言罢,她站起,转身要走。“师妹,告辞。”
“师姐留步!”
冥虚冠人追上前去,扯住雪睨衣袖,道:“你不等紫荆回来?”
待仰头对上雪睨双眸,她不由一愣。
雪睨那如古井般幽深的黑色瞳孔,已转为翠色!
翠绿的眸子经由岁月沉淀,已不是六百年前的天真明媚,而是……
极尽妖冶。
冥虚冠人伸手抚上雪睨面颊。“师姐……你生气了?”
雪睨垂下眼。“清修之人怎会大喜大怒?”
胡说。冥虚冠人暗想,明明气得连施于眸上的术法都维持不住了,还要故作镇静。心里一痛,握住雪睨手腕,声音拔高了许多。
“师妹,你须好好想想,那一堆乌七八糟的事里,你又做错了什么?世人待女子苛刻,待貌美女子尤其苛刻!你无心纷争,那些人却要以你之名争个头破血流!后陈开国之君是,当今国君也是,还有当年那设计你拜入天机教的……”
话未说完,雪睨反握住她的手,一点点用力。
雪睨的手很凉,正如她此刻冰冷的心境。
“我晓得……自然不会为难自己。我先回洞府,若是紫荆回来,劳烦师妹相送一二。”
冥虚冠人再也说不出什么,只得让雪睨离去。
不多时,冥虚冠人回到石桌前,看着幻镜中的紫荆,轻声叹口气。
“不知我的好师侄,接下来又会遇到些什么。”
紫荆躺在享王府的客房里,睁眼瞪着帏帐发呆。
她在想:今天真是漫长的一日。
这一日,她由九天回到红尘,见到许多人,听到许多事——陈齐、孙家兄弟、绢儿、享王妃。
还有南齐之乱、后陈建国秘闻、北疆之乱、皇储之争、以及北狄的异常与享王妃腹上依附的怨气……
一日之间,大幕拉开,黑的白的灰的,各方角色粉墨登场。就连她自己,也成了这红尘大戏台上的戏子。
每一件事都不能看清全貌,整个人如坠迷雾之中。可她并不厌恶这份迷惘。
因为,这即是真正的红尘,人人都在迷雾中前行,不只她孤身跋涉。
纵是今夜,算计的、担忧的、失落的、跋扈的……世间种种人为一己的立场与得失辗转反侧。但至此时,紫荆仍为世外之人,她仍是睁眼眼,好奇地等着,这尘世又会呈现出什么。
所以她只有困惑,没有忧思。
纵然……前路漫漫,吉凶未卜。
她闭上眼,不过片刻,沉沉入梦。
紫荆在享王府内住了数日,每日皆是被锦衣玉食好好伺候着,让她生出许多不自在。伺候她的婢子却道:幸亏紫荆是道门中人,若是真正的王府女眷,少不了还得学好命妇礼仪,那才真不自在。
紫荆听了,暗付自己运气还好,仅是途中假扮绢夫人,待入了安康城,那位享王殿下想必不会太为难自己。
这其间,孙成虎与孙成燕见了被暂时安置于城内的鱼锦乡民,问及鱼锦乡民近日有何异状,为何引得刺连部追击不止。乡中老者抚须沉思片刻,道乡中并无不同,只是听说乡里唐氏大族收留了一名年轻人,似是来路不明。
孙家兄弟又找到唐氏族人的集居宅子,这回不消他们问,众乡民拥着一个年轻男子出来。
那年资身着澜衫、头束方巾,宽阔的袖子随着宜营城内的风沙飘动。许是书生般文雅的打扮,孙成虎却觉得,他并非一介寻常书生。
或许是此人面皮不够斯文,狭长的桃花眼透着几分邪气,肤色精悍如蜜,又或许他与孙成虎见过的书生甚至于儒商相比,身上到底少了些气韵沉淀。
孙成虎不由又打量他几眼,书生桃花眼一眨,目光直直落到貌若好女的孙成燕上,咧嘴嘿嘿一笑。
“早听说宜营城内美人多,果然名不虚传!”
这腔调,更不像书生了。孙成燕暗自蹙眉,孙成虎却正觉得那男子面熟,一听这句,陡然记起——他就是几日前,守在宜营城门口,一睹紫荆真面目后,称赞紫荆不但心善人也美的书生。
那时他心中烦闷,挥鞭相向,险些伤到此人。
孙成虎当下生出几分不快,瞪那男子一眼,对方也是一愣,随即又笑道。
“将军可曾记得在下?当日将军的鞭子好威风!”
“休要插科打诨!”孙成虎喝道,随即又扬了扬手中长鞭:“听说你不是鱼锦乡民?”
那男子并未露出惧怕之色。
“在下唐致远,并非真名,因为在下患了失魂症。一月前被唐家乡亲收留,蒙族老照顾,得了此名。”
“失魂症?”
“对,姓甚名谁、家住何方、有无功名在身、是否婚配一概不记得了。”
现名唐致远的男子挑了挑眉,勾魂的桃花眼往周围溜上一周。
“故而,在下如今还是形影孤单,少了佳人在侧啊。”
便有些妙龄少女掩袖而笑。
孙成虎与孙成燕却皆是听得眉头一跳。失魂症,即为丢失了过往记忆。当下之际,这可疑男子的“失魂症”是不是来得巧了些?
“哼!”
孙成虎一扬手,长鞭直直挥向唐致远,待他硬生生受了这一鞭,才冷冷一笑。
“你这失魂症,是真丢了魂,还是装作丢了魂?”
唐致远只得苦笑。“是真的,不过将军定是不信。”
孙成虎道:“我自然不信!来人,将这人押回军中!”
回到军营,两人又多番审问唐致远,其间也用了些刑罚,唐致远被整治得叫苦连天,仍是一口咬定自己得了失魂症,前尘过往一概不记得。
孙成虎与孙成燕也暗自盘查过唐氏族人,皆言唐致远是一月前被唐氏偏枝里的一幼童在村边的官道上捡到。那时唐致远身上衣着是南齐式样,后脑似是受了重物击打,血流如注,待醒来,神色悲苦茫然,倒不是现下这般轻浮的模样。
后脑勺受了伤,确实可能患上失魂症。宜营城一带又是交通要塞,南齐、后陈子民彼此来往,一个南齐人去往乡间并不少见。此人更早的来路,却不是鱼锦乡民清楚的。
孙成虎以为线索就此中断,抿着嘴极为不悦,半晌才对唐氏众人道:“若有隐瞒,定斩不赦!”救下唐致远的唐氏幼童被那煞气颇重的模样吓了一跳,随即怯怯道了一声“还有一事”,交出一块玉佩。
玉佩雕成鱼纹状,式样倒是常见,质地却是上等墨玉。
孙成虎抚摸着冰凉莹润的玉身,忽然窥得一丝光明——墨玉千金难求,只产于南边小国,后陈尚无几人佩戴,南齐持有者只怕更是聊聊无几。一个戴着墨玉玉佩招摇过市之人,想必在南齐有些名声。
去南齐,或许能查出些什么。
孙成虎猛然合掌,将玉佩握于掌中。再观那小童,满面愧色,心下了然。
这孩子当日定然被玉佩吸引,救下唐致远之时便将它偷偷取下,后来又见他想不起往事,更是昧下了玉佩。
孙成虎也不愿在些旁枝末节上多加追究,只命唐氏族人退下,又唤来孙成燕。兄弟两商议一番,将玉佩纹样绘下,命细作去南齐境内探查。玉佩则由孙成虎带在身上,待入了安康城,到瑞王面前拿出来一晃,说不定能起些引蛇出洞的效用。
又过了一两日,绢儿的册封金旨总算到了王府。陈齐大喜,对着宣旨内监掩袖“哀哀哭泣”,只道北疆不平,他“惶惶难寝”,宫里人却是来得正好,他怎么着,也要随内监一同回安康城。
于是翌日,享王的车马浩浩扬尘,孙成虎这被享王“强行驾来”的守备一脸不愿地充作镖师,顾看着众人起驾。
享王府的车鸾分作三驾。第一驾由陈齐独享,内有老内监福达伺候;第三驾坐着些王府内有些脸面的仆从;第二处却是由享王妃与“绢夫人”共乘。
此举并不合身份尊卑,享王妃是陈齐正妻,又怀有身孕,即便不与陈齐共乘一车,也应单独僻出一个车厢。陈齐却以“逃难之行,不必太过讲究”为由,让享王妃与“新宠”共乘一车,若非孙成虎知道车厢内的“绢夫人”另有其人,也会腹诽陈齐宠妾灭妻之觉做得太过。
说来享王妃也生得貌美,只是脾气大些。这对夫妻为何貌似神离?
孙成虎暗自思索,双眼不由自主瞟向享王妃的车厢,恰逢紫荆挑起车帘,淡然问道:“敢问孙将军,我们何时启程?”
享王的“新宠”,自然是穿金戴玉,极尽奢华。
车帘之下的少女,唇间朱砂嫣红,云鬓之下峨眉淡扫,一身玄衣衬得蜜色肌肤爽利又不失贵气。
华妆之下,黑白分明的清澈双眸,隐隐透出几分凛冽。
“大概、大概就快了……”
孙成虎曾想过,紫荆打扮起来不差,却想不到,竟是如此的……如此的……
勾人。
尽管,那仍然是一个不够柔媚的少女。然而她的正气与高贵,使得周边人与物黯然失色。
紫荆却狐疑地注视着他。
“孙将军怎么有些着紧?”
孙成虎慢慢回过神来,额上汗珠隐约可见。
“绢夫人。”他特意咬牙切齿念出这三字:“请勿说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