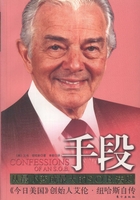大道上,“三苏”并马而行,巢谷从后面追来,边追边喊道:“伯父,等等我。”“三苏”停了下来,巢谷很快就追上了:“伯父,带我一起去吧。”苏洵说:“你是背着师父来的吧!”巢谷嘴硬,说:“没有没有,师父答应我了。”苏洵笑着说:“你啊,从小就不会说谎话,说了也不像,我就知道你是瞒着吴道长偷偷跑出来的。你是吴道长的徒弟,既未禀过师父,老夫怎敢私自带你!”
巢谷虽然学问不及大小苏,但机智却毫不逊色。一来是他天生聪明,二来是他自小和苏轼兄弟厮闹在一起,也学了不少应变之方。他知道苏洵的弱点,机智地说:“我以为伯父无所畏惧,原来怕我师父!”苏洵果然中计,道:“什么?谁说我怕那牛鼻子老道了?”巢谷一脸无奈地说:“哎,刚才伯父明明说‘怎敢私自带你’,岂不是怕了吗?”
苏洵虽是文章大家,但机智却未必赶得上年轻人。不过,他生性洒脱,也有一套应付的办法。他一拍脑袋,道:“我说了吗?好,老不和少争,就算我说了。那日那牛鼻子不帮我劝说轼儿、辙儿,反倒拂尘一扬,云游去了。哼,我就偏偏带走他的徒儿,这叫一报还一报。”
巢谷跳了起来,喜道:“太好了,太好了!我又可和二位哥哥在一起了。要是伯父路上遇着劫道的强人,我也好替伯父打发了他们。”苏洵说:“嗯,好。说不定你也考个武状元回来,你那牛鼻子师父怕是要气疯了。”众人大笑起来。
经过月余的跋涉,苏洵四人从陆路来到汴京,暂时寄居在兴国寺。
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秋天,汴京贡举院的大门缓缓打开。随着沉闷的吱吱呀呀的声音,贡举院内外的古树上,众鸟受惊,呼啦啦地飞走了。
宋代礼部考试,有锁院、誊抄等繁复的制度。就说誊抄吧,举子的亲笔试卷都必须经过抄手的抄写,再编号上送,以免考官认出了考试的笔迹,内外联通作弊。此时的贡举院里,一群带刀侍卫紧盯着长案前的两排抄手。这些抄手一个个鹄首鸠面,多是屡试不第的书生。他们在进来时都换上了统一的服色,等出去时再换上自己的衣服。抄手后面立着带刀士兵,神色肃穆。抄手们一边疾书,一边还惊恐地看着身后的军士。他们虽是读书人,但此刻形同囚徒。
终于,抄写编号完毕,一军官大声喝道:“誊抄完毕,起立!”抄手们齐刷刷地站起。军官又说:“封卷。”于是,士兵们向前将各自面前的原卷和抄写卷封好,并贴上封条,军官收起放入箱中。抄手离场后,军官指挥士兵,将装有试卷的大箱子抬向阅卷处。
此时,刚刚考完的考生们也鱼贯而出,很多人都惊魂未定,脸色还没有缓过来。但以刘几为首的一群太学生走在前面,他们的表情与众不同,多数洋洋自得,面有骄矜之色,仿佛已经高中了。
随后又出来了一群年轻人,他们大多二十岁左右的年纪,面色平和,谈笑自如。其中一位相貌精干的青年向其他人抱拳,客气地说道:“诸位兄台,一定都考得不错吧!”他叫章惇,字子厚,出身汴京富家,但性格果毅,为人朴实,与纨绔子弟大不相同。本来,大家都没有直接谈及考试的事,既然章惇率先开口,曾巩就不能不先接下来,因为他是欧阳修的学生,年龄较大,在举子中文名最盛。曾巩客气地说:“哪里,哪里,在下意迟笔拙,定然不及子厚兄。”章惇开朗地笑道:“兄长客气了,谁不知你的大名,即便不中魁首,也……”曾巩好像十分敏感,急忙用手势打住了章惇的话头。章惇立即会意,就转向了旁边的苏轼:“子瞻兄,素闻你才华卓异,想是方才已作了一篇好文章吧。”苏轼当然也十分客气:“呵呵,西蜀鄙人,怎可与子厚兄相比!”章惇一笑,又转向旁边的苏辙,说:“子瞻兄竟如此自谦。子由一表人才,想来也不会落于乃兄之后!”苏辙急忙说:“惭愧,惭愧,苏辙哪里敢与众位才俊相比。”
这时,刘几等一众太学生在前面喧哗起来。他们与章惇、苏轼等人虽然不熟,但都有耳闻,尤其对曾巩,太学生们更是熟悉。他们见曾巩等人走在后面,好像故意找茬似的,大嚷起来。刘几高声说:“哎,终于是考完了,就等着发榜之日了。以我十年太学精深造诣,欧阳修虽然是知贡举,又能对我如之奈何?”一个太学生立即迎合说:“以刘兄才学,定为此次大考魁首。”众人急忙唯唯称是。刘几故作自谦地说:“不过欧阳修如今得势,却也不可轻视。”另一位太学生附和道:“刘兄无须多虑,还是先到哪里一聚吧,我等早已等不及了。”刘几说:“好哇,所谓饮酒之醉,美色之欢。这种时候,当然是去西池了。”说着,刘几向一个太学生使了个眼色。
那个太学生随即转身,拦住了后面苏轼一行人的去路,傲慢地说:“我等这就去西池摆庆功宴,倒想听听,你等秀才会去哪里呀?”章惇秉性峻急,并不相让,反唇相讥说:“啧啧,好大的排场,出手真是阔绰啊!尔等不愧是纨绔子弟,岂是我们这些穷酸书生所能比,可以坐吃老子山空呀!”那位太学生涨红了脸,指着章惇说:“你,你,你敢侮辱我等斯文……”
刘几走上前来,用手拦住他,说:“哎,不要着急,我等的一言一行都要给太学院增光,我们讲的是以文会友,莫要学这些市井小民,出口粗俗,学那欧阳修的什么新文体,失了读书人的体面。”太学生们一听,立即齐刷刷地站到刘几身后,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
曾巩虽然为人沉静,但他再也不能沉默了,大家都知道他是欧阳修的学生。他走上前,厉声说:“哼,体面!久闻太学生不学无术,以堆砌华丽辞藻为能事,故而吃饭也要找个华而不实的地方!”曾巩的话虽不多,但每个字都指向了刘几的痛处。刘几有些恼羞成怒了,大声吼道:“曾子固,不要以为你那老师欧阳修做了知贡举,今年你就能中榜。依我看,你就是那屡试不中的命,你若不归太学,我料你今年仍是不中。”众太学生觉得挽回了面子,哈哈大笑起来。曾巩毕竟是老实人,气得两手发抖,说不出话来。
章惇却是口齿便给之人,当即反讽道:“哈哈,刘兄,依我看,此次该是太学的招牌挂不下去了。刘兄如今该自悔当初错投师门,只可惜大比已过,想要临时抱佛脚,却为时晚矣。”张璪一直跟在章惇的后面,没有说话,他听了这话,也呵呵一乐。这一乐,更加激怒了刘几。
刘几说:“哼,我太学精深,岂是尔等井底之蛙所能窥见?区区一个欧阳修,就能撼动我太学百年基业,螳臂当车,可笑不自量。曾子固,我告诉你,不要以为你是欧阳修的得意门生我等就会服了你,有本事我们各施才华,一决高下,看看究竟是你们欧阳体厉害,还是我们太学体高深!”
曾巩说:“哦,怎个比法?”刘几说:“汴京城内有一汴河酒楼,专以对楹联为趣,如能过三关,不仅酒肉自便,还有美女相伴。今日你我就去那里一决高下,你敢不敢?”章惇是个好事的人,他倒是有些乐了:“什么敢不敢,难道怕你不成,谁输谁请客!”刘几道:“好,一言为定!”
苏轼站在人后,正欲随曾巩、章惇等人离去,却被苏辙拉住。苏辙说:“哥哥,别忘了父亲叮嘱过的话。”苏轼遗憾地说:“也罢,那就回兴国寺去吧。”
苏轼与苏辙走过龙津桥,离开了众人,方显得意气风发。苏辙问苏轼说:“哥哥,今日考的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是如何写的,快说给我听听。”苏轼神秘地一笑:“父亲不是说我们回去之后,即刻将文章抄写给他观阅吗?子由,你那时再看不迟!”苏辙觉得苏轼表情有些奇怪,狐疑地望了望苏轼,正待追问,巢谷却突然从旁边闪了出来。巢谷拍手叫道:“等你二人许久了,这时候才来!”
东京的御街上,苏轼、苏辙和巢谷三人兴致勃勃地走着,说说笑笑,左顾右盼。他们来汴京后,一直准备考试,还没有心思好好看看汴京的风物。
苏辙说:“巢谷兄,你陪我们赶考,这一路上,见了甚多景物风情,我看都比不上这汴京的繁华景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这么多的街道店铺,车马行船,好不热闹!”巢谷说:“是啊,子瞻、子由,今日咱们该找个地方好好大吃一顿!成日吃这兴国寺的斋饭,我这嘴巴都淡出鸟来了!”苏辙摇头说:“不行,不行,父亲还在兴国寺等我兄弟二人,须得赶紧回去。”巢谷不悦地一撇嘴,瞅瞅苏轼,苏轼笑而不语。
此时一书贩当街叫卖:“卖文章了,卖文章了,苏洵苏明允的大作《六国论》,历陈六国覆灭之根本,针砭时弊,十文一篇,快来买啊。”苏轼、苏辙、巢谷听了,自然走了过去。苏轼问:“店家,这《六国论》卖得好吗?”店家说:“不瞒你说,前两天供不应求,可这两天总有人捣乱。这不,刚才有几位公子想买,又来了一群太学生偏不让他们买,双方争执不下,听说是到汴河酒楼比对联去了。”
苏辙气愤地说:“哥哥,一定是曾巩、章惇与太学生刘几他们。”苏轼微一思忖,对巢谷说:“哈哈,巢谷兄,听说这汴河酒楼专以对楹联为生,如能答对,还能免费吃饭。”苏轼知道巢谷是个极实在又极好事的人,才这样逗他。巢谷说:“这可难办,巢谷会看对联,却不会对。”苏轼毫不介意地说:“巢谷兄,今日自有我来管你吃个痛快。那些人如此霸道,不让别人买父亲的文章,岂能不去问个究竟?走,我等三人去汴河酒楼吃酒去!”
三人走了不久,来到汴河酒楼门前。门楣之上,首先映入眼帘的一副对联是:常对能对妙对引来八方才士,八折五折零折送尽四海美味。横批:凤鸣京华。
此时,汴河酒楼里,众太学生趾高气扬,显然已占了上风。曾巩、章惇、张璪、曾布等人则心有不甘。刘几说:“怎么样,尔等可输得心服口服?这楹联一事,最见真实功夫,来不得半点花言巧语。”张璪辩解道:“你们太学生专攻楹联,以己之长,对人之短,赢了又能如何!”刘几说:“哼,赢就是赢,输就是输。一个小小的对联都对不上,还有什么资格“登堂入仕”,趁早回家去吧。”众太学生放声大笑。曾巩、章惇等人脸上无光,但又无可奈何。
酒家门口,几个太学生拦住了苏轼三人。一位太学生上下打量着他们说:“今日这汴河酒家被我们包了,你等吃得起吗?”巢谷说:“岂有此理,你们这些太学生,偏这么霸道,不让卖书,也不让人吃饭,这汴京是你们家的吗?我偏要进去,看你能把我怎么样!”说罢便要往里闯。苏轼急忙制止,“巢谷兄,不要乱来。”一位太学生将苏轼打量一番,轻蔑地说:“看样子你是个读书人,该是学那欧阳体的穷书生吧。你进去可以,要先过了我等这一关。”苏轼淡淡地说:“哦?请出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