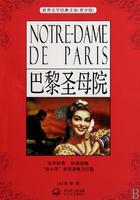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
“我就说这一件绝对最适合你!”更衣室里,谈晶一边替盛夏拉起拉链、整理褶皱,一边得意扬扬地自卖自夸,“这款刚到店里时我就眼前一亮,这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
盛夏听着她自吹自擂,不由笑了:“谈老板,你怎么不直接说这件是你自己设计的?”
谈晶自是听出来她的揶揄,没跟她计较,手一挥,道:“好了,快出去给你家顾映宁好好瞧瞧!”
推门而出,盛夏走向不远处坐着的男子。
也许是因为到了傍晚,偌大一个店里竟没有多少顾客,所以,在宽敞的落地窗旁坐着的那名男子就显得格外醒目。
白色手工定制衬衫的领子立着,两粒扣子也解开了,领带随意地拉到襟扣以下,一边肘弯上还搭着黑色西服。似乎听到轻微的脚步声,男子抬起头,脸庞在傍晚赤橙的黄昏色下仿佛镶了一圈模糊的金边。
精神的短发,英气的剑眉,长长的睫毛下眼睛双得很立体,而挺立的鼻梁下紧抿的薄唇和如同鹰隼一般的目光,更是凸显出他的冷峻。
盛夏施施然走过来的那一霎,一抹不易觉察的惊艳在顾映宁眼中一闪而过。
深吸一口气,盛夏有些忐忑地问顾映宁:“这一件……好不好看?”
眼前的女子浅笑中带着一丝紧张,双手不由自主地绞在一起。
顾映宁心知盛夏的不安与期待,慢慢站起来,尽管还是那副面无表情的模样,目光却柔和了不少。
将一缕发丝理到她耳后,执起盛夏的手,顾映宁开口,嗓音低沉而富有磁性,仿佛徐徐演奏的大提琴:“很好看,就这件。”
站在不远处的谈晶一听,顿时眉开眼笑:“我就说嘛,听我的准没错!小夏,这款婚纱衬你最好看了!”
是的,婚纱。
盛夏微微低下头看向自己穿着的婚纱,颈子洁白如瓷。
香肩裸露,精致而小巧的锁骨清晰可见。弧扇形的抹胸,最上面还滚了一圈淡杏色的蕾丝边。收紧的腰腹处紧贴秾纤合度的腰身,亚克力钻之下是豪华而精致的手工珠绣,而如同立体花朵一般的亮厚缎褶皱则是整件婚纱的独特之处。四层轻纱的裙摆和胸口呼应,也绣着一圈淡杏色的蕾丝边,后面轻盈飘逸的拖尾正是欧洲婚纱最佳长度的两米。
这样简洁却又透着灵气与奢华的婚纱,真的好似量身定做的一般,意外地极其契合盛夏的身材和气质。
顾映宁的“一锤定音”让盛夏安心了不少,但她还是微微皱了皱眉:“拖尾……会不会太长了?”
谈晶刚欲疾声说不长,顾映宁却已经先一步出声,沉稳道:“不会。这样子,刚刚好。”
既然如此,盛夏便也不再说什么,轻轻应了一声,说:“我去换衣服。”顾映宁点头,随即松开了她的手。
谈晶一边给她打下手,一边感慨道:“小夏啊,依照你家那位的脾性,若没有你的游说,怕是一定要去欧洲量身定制婚纱的吧?”
盛夏但笑不语,谈晶却明白,笑嘻嘻地拍拍她的肩,道:“够姐们儿,有了长期饭票也不忘咱老姐妹啊!”谈晶想了想,又道,“不过小夏,你家这位真是个深藏不露的主儿,够喜怒无色的,什么时候见着了都是一张面瘫脸,估计也只有你能受得了他。”
盛夏扫了她一眼,嘴角勾起一抹笑:“小晶子,你说这话就不怕得罪了金主?”
谈晶仍旧嬉皮笑脸:“不怕不怕,有我们家小夏还怕什么!”
盛夏听了直摇头叹息,倒不是因为别的,只是觉得谈晶说的话欠妥,“再这么粗鲁豪放地讲话,小心白马王子都被你给吓跑了。”
从谈晶的婚庆店出来,白色的加长保时捷早已停在门口。
暮色已经四合,候在一旁的江镡恭恭敬敬地打开车门,一手按在门框顶,让盛夏先坐了进去,顾映宁紧挨着她上了车。西装放在一边,顾映宁头靠着椅背闭目,低声道:“滨江饭店。”
保时捷在路上疾驰,周围的风景飞快地流动倒退。一排排橘黄色的路灯仿佛连成了一道柔和的光链,让盛夏忽然想起了冰心曾经写过的那篇《小桔灯》,那光亮虽然微弱得多,但要是许多盏连成一片,大抵也差不多如此吧。
正想着,保时捷的速度慢慢地减了下来,直到停车。
江镡依旧是先毕恭毕敬地下车开车门,顾映宁锃亮的皮鞋率先迈出,弯腰从车里出来站定,然后转身对着车内伸出一只手:“小心台阶。”
不得不说,顾映宁在细节方面真的是一个很体贴入微的情人,让盛夏就算想不泥足深陷都不可能。
滨江饭店是顾映宁旗下的产业之一,他素来喜欢到这里用餐。
罄竹优雅,小桥流水,草翠花香,确实是环境极佳的用餐场所。
固定的包间,常吃的那几道菜,只是顾映宁今天还叫了一瓶红酒。
他的胃不大好,对于喝酒向来是能避则避。因而盛夏很诧异,轻轻摇晃着酒杯,问他:“今天发生什么事了,这么高兴?”
顾映宁却没有立刻回答她,眼中闪过一丝笑意。他摇了摇酒杯,又凑在鼻尖嗅了嗅,轻啜一口,然后才低低说道:“没什么,你就要嫁给我了,算不算好事?”
盛夏愣住了,饶是知他如她,也没有想到顾映宁会说出这句话来。
他们在一起三年了,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类似甜言蜜语的话,哪怕是前天求婚的时候也没有。她一直以为,为这场婚礼欢欣喜悦的只有自己,原来他竟也是高兴的。
正欲说话,顾映宁的面色却已经沉了几许,眼眸中的笑意也一去不复返。将红酒杯放下,顾映宁起筷,那姿态正是不愿再讲话的淡漠。
盛夏怔怔地拿起筷子,心底不由得暗自嘲讽,刚才自己果然是想太多了,为这场婚礼欢欣的到底还是只有自己。像顾映宁这样的男子,场面话从来都讲得极好,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罢了。
一顿饭吃得食不知味,两人都静默无声,只听得汤勺筷子和碟碗相碰的声音。
正抹嘴,盛夏忽然听到简短的一句话:“回家就把电子喜帖发了吧。”该通知的亲朋好友其实早已邀请了,电子喜帖不过是给远方亲友的一种形式罢了。
盛夏下意识地应了声“嗯”,应完却又顿住了,没有再说一个字。
他永远都是这副模样,淡淡的一句话就决定别人的生或死,仿佛他就是天生的王者,优雅而疏离。在他和她之间,自己似乎很少有置喙的余地,现在是这样,甚至连求婚那天,也是如此。
其实那次,根本都不能算作是求婚。
寂静的黑夜里,黑白条纹的窗帘拉得极严密,连一丝星光都投射不进来。屋内的温度暖如阳春,似乎还盘旋着男女相拥的独特气味,一室的旖旎。
盛夏躺在顾映宁的身侧,黑白分明的双眼睁得很大,乌亮的发丝更是软而密地散落在了顾映宁的肩臂上,弯成一道水亮的弧度。
脸上绯红未褪,气息也还没有平稳,盛夏刚想起身,却被身侧的人按住了。
她回头,黑暗里他的眼睛闪过明亮的光泽,手掌慢慢抚过她的脸颊。顾映宁开口,温热的呼吸让整间屋子里的温度陡然间又攀升了不少。
“盛夏,我们认识多久了?”
有些意外,盛夏微微蹙眉想了想:“三年零六个月。”
“三年多了啊……”他轻轻喟叹了一声,而后抚了抚盛夏的发丝,“不知不觉,都已经这么久了。”
黑暗中看不清顾映宁的表情,盛夏只觉得他似乎还有话没有说完,不由得身子也侧转过去,屏息等他说下去。
“既然如此,”他顿了一顿,似乎在斟酌又似乎在犹豫,片刻后才启齿,暖暖的热度洒落在盛夏的额头,“不如我们结婚吧。”
他说得这样云淡风轻,又在这样一个场合,盛夏难以置信地惊讶不已—结婚,他竟然说结婚。
在盛夏心中,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定义自己和顾映宁的关系。似乎从一年半前两人都喝醉酒有了第一次肌肤之亲后,她就无法理清了。若是普通朋友,不会时不时地发展到“坦诚相见”;若是男女朋友,他们又从没说过一句跟“爱”、跟“喜欢”相关的话—虽然,盛夏后来渐渐发现,自己已经真的爱上了顾映宁。
眸子转了又转,盛夏忽然“腾”地坐了起来,“啪”的一声打开灯,双唇紧抿,和顾映宁波澜不惊的目光对视了半晌后,她清清楚楚地吐出一个字:“不!”
顾映宁的墨瞳骤然紧锁,剑眉拧起,犀利的目光宛若要将盛夏灼伤。他压低声音,却压不住其中隐隐的怒气:“理由。”
盛夏张了张嘴,却倏然语塞。明明顾映宁早已成为融入自己呼吸的一种存在了,但在刚刚她却下意识地回了一个“不”字。若是因为他的求婚这样随意就像讨论天气一样,若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句“我爱你”,这样的理由,是不是显得太矫情?
没有等盛夏从怔忪中回过神,顾映宁已经翻身坐起,沉声道:“既然说不出理由,那就这么定了。”
婚事就这样一语敲定。之后他从容不迫地下床,抄起地上的衬衫向浴室走去。没有抬头看他,盛夏屈着腿将头深深地埋进自己腿间,到底心里是苦还是甜,一时她竟有些分不清了。
从滨江饭店出来,江镡坐在驾驶位上目不斜视,平平板板地问道:
“老板,是先去清茶花苑吗?”
顾映宁从喉咙里几乎闻不见闻地“唔”了一声,于是保时捷再次平稳地行驶起来。
其实两年前盛夏就已经搬到了顾映宁的别墅里,但清茶花苑里自己的那套公寓也一直没有退租。眼下要结婚了,按照本地的习俗,新郎新娘双方在婚礼前是不应该见面的。若真要盛夏和顾映宁连续一周不见面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便折中了一下,盛夏住回自己的公寓里去。
开到清茶花苑门口的时候,已是繁星点点。墨漆色的苍穹仿佛最上好的天鹅绒,上面镶嵌着一颗颗闪闪亮亮的金色钻石。
顾映宁送她到保安室门旁,稍微拉了拉盛夏的衣领,淡淡道:“夜露重。”
盛夏望着顾映宁熠熠的双眼,起初略带迟疑,道:“映宁,我……我进去了。”
顾映宁移开手指,重新插回口袋里,点点头应声说:“回去吧,记得把喜帖发了。”
她微微一笑:“好。”
花苑里还是盛夏熟悉的一草一木,那株参天的凤凰树和那株桃树也依旧沉默地比肩伫立。
从前每到花开时节,人间四月芳菲尽,而楼下的桃花始盛开。
粉色的花朵一簇一簇,春夜喜雨之后格外鲜嫩。桃花凋落之后,就是凤凰树舒展筋骨的时候了。一闭上眼,盛夏就能想象出它开花的样子—高达十几米的树上,青翠欲滴的羽状复叶层层地重叠在一起,那些红花烈火一般,一团团、一簇簇地在树冠上鲜艳夺目。
那时候她还住在清茶花苑,经常早晨一下楼就发现顾映宁正站在树下等她。因为有他,连凤凰树都黯然失色—沉淡于他的气宇非凡,沉淡于他深寂缱绻而又犀光点点的眼眸。顾映宁素来宠辱不惊,也很少笑,总是那副淡漠疏离严肃认真的模样。但盛夏就是知道,每当和自己在一起时,他周身的气息总会柔和许多。
盛夏一边想着一边不禁露出一抹笑,既然他说要和自己结婚,必定多少还是喜欢自己的吧。
正要转身进楼,忽然发觉身后阴影处似乎有个人影。盛夏一惊,一秒之内脑中已经转思百遍,最后决定加快脚步赶紧冲进电梯。然而没等盛夏迈出下一步,身后的那个阴影竟已经先行出声。
“阿夏。”
有如晴天霹雳,亦有如背后一棒,只是短短的两个字,盛夏却已经惊得脑中刹那空白,双眼陡然间睁大,仿佛被人施了缚身术一般手脚都无法动弹!
这嗓音……这嗓音分明是—许亦晖!
张爱玲曾经说过,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朵白玫瑰和红玫瑰,女人其实也一样。若是说现在顾映宁之于盛夏是心口上的一枚朱砂痣,那么许亦晖就是曾经照亮盛夏的床前明月光。
那个时候盛夏刚升入大三,宿舍里俞珂薇、元静都准备复习考研,盛夏便跟着一起去了图书馆。谈晶是一向的优哉悠哉,每天都鄙视盛夏装斯文。
那天早晨,盛夏抱着一堆书迷迷糊糊地到了图书馆二楼,眯着眼看见靠窗那边似乎有个空座,便毫不客气地将书一放,坐下来之后倒头就睡。一个梦还没有做完,忽然觉得有人在轻轻摇晃自己的肩膀。盛夏慢慢睁眼,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只修长的手,再往上看,是一张年轻干净的脸。
许亦晖穿着白色的棉质衬衫,袖口扣得很整齐,他微笑着对盛夏轻声说:“同学,你坐了我的位子。”
盛夏愣了一会儿,回过神后缓缓地环视了下人头攒动的四周,然后说出了一句连自己都觉得讶异的话:“这会儿我坐着了就是我的。”
她并不是一个喜欢耍赖的人,因而此刻在脑子一片混沌的时候竟说出这样的话来,她自己也怔住了。许亦晖自然也微怔了片刻,但他却没有发脾气也没有生气,只是兀自笑了笑,长而细的手指翻开盛夏胳膊前的那几本书,扉页上清晰地写着“许亦晖”三个隽秀的字。
他不愠不恼地耐心解释道:“同学,我只是去打了杯开水,人太多,所以排队费了点儿工夫。”
明明许亦晖才是有理的那一方,但一瞬间盛夏竟觉得委屈起来。
也不知道那一刻自己究竟在想些什么,她不讲理道:“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刚刚趁我睡着把书放这儿的?”
许亦晖语塞,照盛夏这样的胡搅蛮缠他就是有理也说不清了。
索性不再争辩,他收拾起自己的书本,依旧笑笑,打算转身离开。
盛夏却又不乐意了,一把抓住许亦晖的袖子,迅速站起身来:“不许走!”
周围的同学早已开始侧目,盛夏装作没看见,抱起自己的书气势汹汹地冒出几个字:“你坐,我走!”说罢昂首挺胸地从许亦晖身边擦肩而过。她用去一整天的时间逼自己忘记这段太过丢脸的插曲,却愣是记住了睁眼那刻看见的脸庞和那三个隽秀的字。
让盛夏意外的是,接下来的五天,不晓得究竟是不是巧合,每天她都会在图书馆和许亦晖碰上一面。有时是在茶水间倒水时,有时是在阅览室门口舒展胳膊腿时,还有时是在上下楼梯错身而过时。
终于,当第六天再次相遇后,许亦晖放慢脚步停了下来,眼角眉梢的笑容舒展而温和。他说:“同学,明天需要我帮你占个座吗?”
就这样,他们正式认识了。没多久,当许亦晖第一次牵盛夏手的时候,她觉得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那么理所当然。或许就是因为一切太过顺利,于是盛夏以为她和许亦晖会顺顺利利地一起毕业、一起工作,待时机成熟时会结婚,拥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庭。
偏偏,老天总爱跟人开玩笑。并且不开则已,一开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