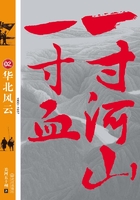桑青十五岁那年,子梅成立了巡山队,保护森林和动物的措施更加严格,扎西成为巡山队员,每月固定领工资。扎西正直,严肃,在整个贡嘎山乡是第一批被挑选去当森林警察的男人。政府给他发了两套衣服,一杆火枪。扎西热爱森林和火药的味道,丝毫不畏惧危险,他总是把枪擦得闪亮,亲吻枪筒,祈祷平安。
按照木雅藏人的习俗,阿妈在村里点燃篝火,宰杀一只羊,庆祝扎西得到这个工作。
整个子梅村的人都来喝酒,村长也来了。村长是个硬朗的小个子男人,能像岩羊一样灵活地攀爬山路,他和大哥并肩坐在篝火旁边,用同一个杯子饮酒,讨论荣誉和未来。
桑青走到他们身边,村长拍拍他的肩膀,说了句祝福话,让他坐下来一起喝酒。
桑青喜欢这高山之上明晃晃的火焰,喜欢男人们身上散发出的高山栎和烈酒气息。火光照耀着木雅男人朴实的脸,磨亮的腰刀,腰刀上的古老花纹,也照耀着他们脖颈间用羊毛绳系在一起的绿松石和雪白狼牙。桑青几乎和大哥一样高了,他将成为他们中的一个,加入这个男人的行列。他希望这篝火边的谈话能够延续下去,直到他长大。
森林静默如谜,生息着纯朴的木雅藏人,也生息着各种各样的植物动物。
雪豹、黑熊和水鹿各有领地,它们华美的皮毛引来偷猎者。
偷猎者狡猾而危险,和子梅的居民一样熟悉贡嘎山,他们善于隐藏,忍耐饥饿,持续几十天在高寒之处追踪雪豹和山猫,几分钟之内干掉它们,剥下一张完整的皮。
桑青听大哥说过,偷猎者大部分从北方来,他们有一条绵长的路线,从青海到四川再到云南,先是偷盗,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买更好的车、更好的枪,和正义公开宣战。在可可西里的红土地上,发生过追捕,偷猎者和保护站队员枪战,还死了人。
每隔几天,大哥会和队员们一起骑着马去巡山。
他用一只手搭在桑青的肩膀上,说这世界上有光明,就有恶人。记住,人必须站在光明这一边。在这座大山里,所有的石头和树木都会看着你,恶人没有能力把名字传下去,但光荣的人可以把名字刻在石头上,子子孙孙都会看见。
一个偷猎者被抓获了。
天快黑的时候,巡山队员将他绑在马背上带回子梅。
村里人开始叫喊,桑青跑去看。大哥和另外三个人拽着偷猎者,把他拖进村长家的院子里。是一个消瘦的青年男子,长着一张粗暴的脸,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一定经过了搏斗,他眉毛上方裂开一道口子,血滴答落下,脸和衣服都很肮脏。
扎西拖着他的肩膀,把他丢在地上。他不出声也不动,什么都不央求,甚至一点儿都不惊恐,这让桑青非常吃惊。一个被抓住的小偷,他应该感到耻辱,应该扑倒在人们脚边,抓紧大哥的双脚哀号,即便张牙舞爪也好啊,可是他什么也不做,看起来他根本不想理睬这些人。
村长让另一个男人骑着摩托车,赶去八十里外的贡嘎山乡打电话,他需要请示镇政府,决定怎样处置这个小偷。巡山队员还带回来了一些证据:两张雪豹皮、四只熊掌、水鹿角和其他一些皮毛。偷猎者是在回帐篷的时候被抓住的——他不是一个人,这个团伙有枪,比我们的枪好。
村长靠着石头墙抽烟。
一支烟抽完,他走向蜷缩的男子,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你们一共几个人?
偷猎者抬起头,那张脸被血迹和泥土弄得一团糟,他什么也没说。
村长接着问:你叫什么名字?
他翻翻眼睛,恶狠狠地啐了一口唾沫,唾沫里夹杂着血星儿,他咧开嘴,笑了。
忽然刮起了盛气凌人的风,也许是什么地方有大雨——村长这么判断。
去打电话的人还没有回来,村长让大家提高警惕,他解开了盗猎者手上的绳子,给他饭吃。青年男子毫不羞耻,他吃下一大碗,吃相难看,之后将半个身子倚在石墙上,似乎正要在自己家里的大床上沉沉睡去。
村长犹豫了一下,没有更紧地捆住他的手。事后他才知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枪声是在黎明时分响起来的。
一只死鸽子直愣愣地栽下来,村子里的狗发疯一样地叫,增加了吓人的气氛。人们接连不断地赶往村长家,桑青跑得像一颗子弹,他心脏狂跳。
战斗已经结束了。
凌晨四点多钟,盗猎团伙包围了村长家。他们共有六个人,每个人都有一杆枪。盗猎者的头目是一个疤痕累累的中年男人,脖子短得像牦牛,鼻梁被打断过。他根本不尊重村长和闻讯赶来的巡山队员,口气强硬地要求释放自己的同伙,双方谨慎地对峙着。
一个盗猎者试图接近大门,扎西从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威吓,警告他退后。
就在这时,角落里飞出一块石头,砸中了一个年轻巡山队员的额头,年轻人惊恐地跳起来,开了第一枪,接下来就是所有枪支都加入进来的对射。
天空泛白,狗闻见了血腥气,一只死鸽子从空中掉下来。
桑青冲进院子,现场一片狼藉。盗猎者突然销声匿迹,地上躺着三个重伤的人,其中有一个巡山队员和两个盗猎者,还有一具尸体,一条受伤的狗卧在尸体旁边。
死者是扎西。他身中五枪,和他的枪躺在一起,脸上依然保持着严肃和正直的神情。
死亡来得非常突然。
杀死他!
不知道是谁喊出了第一声,人们围过来,异口同声地这么叫喊。
被羁押了整整一夜的盗猎者已经精疲力竭,是他弄松了缚住手腕的绳索,从角落里扔出石头。他并没有料到,这块石头砸出的第一滴血会引发一片枪声。枪响之后,肮脏的青年男子害怕了,他吓得瑟瑟发抖,这里已没有他容身之地。
用斧头砍他的脖子!用刀子划开他的脸!
人们似乎已经看到了猩红的血迸溅出来,在仇恨的煽动中,每个人都显露出嗜血的疯狂。
真的有人拿出匕首,逼近青年男子,在他脸上划开一道口子。盗猎者开始哭泣,手脚抽搐。人们咒骂他,朝他吐唾沫。小姑娘吓得呜呜哭,一只鸟在尖叫。
大家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直到阿妈终于出现在院子里。央金搀扶着她,孩子们被留在家里。两个女人看上去都摇摇欲坠,央金脸上全是泪水,阿妈穿着黑色棉袍,棉袍下是一个年迈、消瘦的女人。
人们让开一条路,几个女人伤心地跪下来,念诵祝福。
阿妈走过去,抚摸贴在儿子脸上的黑头发,她再也没有力量站直,屈膝跪坐在冰冷的大地上。
人们停止了骚动,伏在石墙上、门框上,等待这个头发灰白、双眼黯淡的母亲开口说话。
阿妈说:叫他们回家去吧。
现场鸦雀无声,人们睁大困惑的眼睛,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看在我的份上,看在我没有了命的扎西的份上,你们回家吧。阿妈的泪水滚滚落下:我儿子已经没了,这个孩子,他还有妈妈,他还有一辈子。
桑青伸出手,抱着母亲,不让她坠倒。
叫他们回家去吧。阿妈努力站起来,又说了一遍。
阳光苍白,照着沉重的窗框,屋顶与屋顶之间是一道道黑影。
人们开始移动了,望着自己的父母,望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望着自己的狗。驯服的脚步声、马的喷嚏声渐渐远了。
阿妈扶着桑青的手臂站起来,再也不看那个盗猎者一眼。
他表情狰狞,伤口还在流血,蜷缩在地上一动不动。
忘掉他。忘掉仇恨。忘掉悲苦。
阿妈的手是干燥的,她走得很慢,既无怨怒,也无希望,那是她面对佛像跪拜时的神情。
阿妈的声音像是从极远的地方叫着他:桑青,这是命运,无论好坏,我们只能接受。
他的牙咬紧了,眼神很凶。
明妙,你可看出命运的老谋深算?
它先给你一点甜头,一旦你渐渐拥有更多,它会在一夜之间和你翻脸,不惜拿走一切。
桑青捏着拳头,骨节咔咔地响。
扎西彭措的葬礼很隆重,他是子梅村第一个因公殉职的烈士。
这一年夏天,村长骑着摩托车,突突地跑过来,说:知道吗?子梅村发生了一件大事。
出什么事啦?
那个孩子了不起。
哪个孩子?
桑青,他考上大学了。
啊!路边的女人捂着嘴叫了一声。
报纸上也要登他的名字。
多大的字?
登得清清楚楚:桑青彭措,十九岁,考取西南民族学院外语系。
村长说:子梅出了第一个大学生啊。真可惜他父亲死了,他大哥死了,看不到报纸。
子梅村人把桑青家包围起来,人人都很高兴,一口一口的闷气呼出来。
等到太阳落山,桑青也没有回来,男人们都喝醉了。
那天傍晚,桑青策马登上子梅垭口。他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这是他与命运的第一场较量,干得不错。
垭口是两座山峦之间的凹陷之地,站在这里,再也没有山冈能够遮拦视线。
贡嘎山呈现出丰富的色泽,翠绿、赭石黄、群青色的山峰延绵雄伟。在这贡嘎山的背后,还有城市、平原、大海和其他地方,辽阔世界的心脏正在蓬勃跳动,而这人迹罕至的子梅,它隐藏在深山之中。
桑青大声呼喊:我要离开你!我不属于这里!
十九岁的男子第一次在心中生起豪情:命运是不公平的,我不会等在这儿,任由命运欺负,我不接受这安排。反抗吧,神也应该敬畏强大的对手。
他找到一棵枯死的高山栎,整个儿地点燃它。猎猎风中,树木熊熊燃烧,火光冲天,像一支巨大的火炬。
桑青纵声长啸:来吧,看看谁更厉害。
他的马前蹄腾空,长声嘶叫。
他们反抗命运,反抗世界的残酷。
这样的人拥有独一无二的性格,他们将被爱和恨撕裂,他们终将找到彼此。
但此时此刻,命运并不揭示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