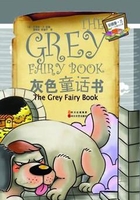这一年春天很奇特,它似乎意味着毁灭的开始。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骚乱,人群同警察发生冲突,裹着白色头巾的男子在围墙上涂写拜伦的诗:我看过你哭,一滴明亮的泪,涌上你蓝色的眼珠……很多颜色的眼珠在同一时间哭泣。一架从华沙飞往俄罗斯的专机坠毁,包括波兰总统和第一夫人、波军总参谋长等,96人遇难。在中国南部,小镇降落巨冰,玉树州则发生了一场7.1级大地震。
一场高烧之后,我重返结古镇。
这里满目废墟,寺庙倒塌,黑鸟栖息在高大的格萨尔王铜像上,伤亡者不再歌唱,他们远离亲人和家乡。在一排排临时搭建的绿色帐篷外,人们垒砌四处散落的石头,支起丑陋的大锅,熬制酥油茶,炸青稞饼。火苗舔舐着石块,石头上破碎的六字真言依稀可见。
飞马铜像消失了,广场消失了,踢着牦牛骨头的康巴汉子们是否安然无恙?
从这里出发,我再度前往土登寺。
沿着通天河向北,这条山路紧贴悬崖,道路颠簸狭窄,人烟断绝。运气好的时候,也要四个多小时的车程,才能抵达土登寺。
这是一个小而偏僻的寺庙,秋英多杰仁波切十岁时在这里跪拜十万佛塔,剃度受戒,开始他一生的修行。这被认为是个非 常黑暗的时代,世界智慧在某种意义上褪色,禅修的传统正在断绝,人们醉心于心灵的傲慢。一本供奉在藏地白塔里的传记这样写道:在巴颜喀拉山的岩洞里,一位大修行者从未放弃过信心,他不间断地修持,获得了极高的证悟,他被称为秋英多杰仁波切。
从那时候起,秋英多杰仁波切的名字开始在藏地和汉地被传诵。
地震降临前三个月,秋英多杰仁波切对弟子说:卡萨扎瓦所说的事情,在我身上都一一应验了,他预言我这一世的寿命是六十九年,我认可这个观点。
卡萨扎瓦是藏地最着名的占卜者,二十年前,他写下一首道歌,预言了秋英多杰的一生,包括他的死亡。弟子们非常悲伤,他们感受到了仁波切身体上的一些变化。
这一年的3月18日,在诵经声中,秋英多杰仁波切圆寂。
和尚和金子,烧的那天见真伪。这是一句古话。
秋英多杰仁波切说:以什么方式离开人世,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但假如我走得过于平凡,会有人信心动摇,诽谤佛法。
因此他留下遗言:
七天之内,在闭关房中不见任何人;七天之后,你们打开房门,我已经离开人世。
房门开启,不管我的坐姿如何,都无须修整。
将我的遗体秘密送回土登寺,不做任何处理,放置一年。
一年后,众人可以进入白塔,你们将亲眼目睹一个非凡的转化。
究竟会发生什么,仁波切没有解释。
二十三天后,玉树州大地震。
一切都在动荡中,谣言四起。
有人说仁波切所言的“非凡转化”是指全然的黑暗,年轻人将不再被爱,地球无依无靠。另一些人不信,斥责凡夫俗子的想法难以纯洁,仁波切将会证明奇迹。
他们剧烈争吵,连土登寺的僧人也开始不安,到处都是窃窃私语。
江阳堪布并不回答疑问,他用铅笔记下这个日期,点燃六十九盏酥油灯。
通天河在黑暗中流淌,时间一直向前。
我答应为秋英多杰仁波切拍摄一部纪录片,为此工作了两年。
桑青失踪之后,我发誓不再去高原。我只想待在繁华的城市里,吃一粒药,睡着,第二天醒过来,也许一切都能回到从前。
我真的乖乖吃下一粒药,没有吐掉,苦的,睡着了,第二天,一切都在改变。
我收到土登寺寄来的一张影碟。我打开它,惊愕地听到了歌声,是江阳堪布在唱歌,歌声温暖,可是十分悲伤,这让我伤心了好久。
我和江阳堪布通了一个电话。
明妙,你有问题吗?
我点点头:是的。我没有告诉他,沮丧的感觉几乎把我击穿了。
你什么时间再来土登寺?
我应该断然拒绝,我发过誓,不再去了。
我回答他:春天就去。
我实在没勇气说不干了,无论多么糟糕,都不能逃避。
春天,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我再次飞往那片孤高之地。
旅途中,我持续昏睡,醒来就喝一种植物叶子浸泡的热水,用来对抗高原反应。在北部一个小城市转机的时候,我买了黑巧克力,还捡到一面桃花心木的镜子。镜面模糊,有一条狭长裂痕,像被闪电劈过。我举起它,里面映照出一张女子的脸,眼睛缺乏睡眠,嘴唇干裂,镜子能说出更多,在更远处,一双男人的眼睛正盯着我。
那是一个陌生男子,坐在角落,身穿黑衣,他长着一双细长的黑眼睛。
我把镜子攥在手心,它凉爽平滑,像是我的另一层手心。
我转过身,走向那个黑衣男子,直到在他的瞳仁里看见我的脸。
旅客们拖着行李箱轰隆隆走远,时间像沙漏里的沙子那样流逝。
他很平静:你记得我吗?
我仔细看看他:你做过什么让我记得的事情?
我们还会见面,我可以带给你永生难忘的经历。
什么是永生难忘?
他不再回答,细长的黑眼睛泛起光芒。
我差点儿就相信了,然后转身走开,不再回头。
不要把时间花在永生难忘上,因为生命太短了。
在巴颜喀拉山的缺口处,牧放牦牛的人们认为蛇是长生不死的,蛇蜕皮就能重生;还有鸟,鸟毁坏蛋壳,第二次诞生;水也是永恒的,它自己饮下自己。
那么人呢?
桑青说:人可以变成舍利。
我问他:那是什么?
他回答:自由。
说这两个字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
这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可我愿意相信他,相信他让我觉得幸福。
为了得到这颗舍利,我与桑青结伴,一起拍摄纪录片,一起阅读佛经,将白海螺和绿松石研磨成粉,一次次前往土登寺。
深入之后,土登寺已经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地名,不再是地图上的小黑点。秋英多杰仁波切曾说:这不仅仅是一片土地,它活着,饱含各种命运。
也许这正是命运写好的剧本,如果没有桑青,我心中不会再升起灿若星辰的悬念。
他教会我用刀,这可是一个别出心裁的礼物。他追踪雪豹,与人斗殴,贩卖一种冬天是虫,夏天是草的奇异植物。对我来说,他交朋友的方式至今是个谜。不知道他是怎么搞来钱的。他一直很穷,也很慷慨,这让他一度是结古镇上最有名气的人物,拥有很多朋友。
他做过很多职业,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摄影师,拍摄所有飞翔之物,热爱动物,决心得到一颗舍利,甚至背叛了一个美貌的女子。
这个春天太残忍了,到处弥漫着呛人的毁灭气息。
我觉得非常孤单,因为桑青失踪了。
江阳堪布,那永生难忘的经历,简直令我忍无可忍。
我和他在海拔三千六百米之处相遇,又一起去往海拔更高的地方,行动非常困难。
桑青说:困难的出现,只是为了被克服。时不时来这么一下,让人保持力量。
我当他开玩笑,心里却认定了这是真话。
如果不是那个釉青封面的笔记本,我会以为这些都是幻觉,桑青根本不存在。在他失踪以后,我始终带着这个笔记本,旅途中小心翼翼地保护它,尽管这样,几页纸张的边缘也破损了,有些笔迹变得难以辨认。
翻开第一页,最上方写着一行字:男人的屁股怎么这么凉啊。
——明妙这是一个日本女人的发现,我笑起来,意识到这是真的。
对应的地方还有一行字:我活着,就是为了你。
——桑青这两行无关紧要的对话,短得可笑。
一看见这字迹,我瞬间就回到了结古镇。
每一次,老鹰在空中盘旋,动物骨骼白得发亮,呼啸而过的大风吹动经幡。桑青向我走来,用腰刀对准我的鼻尖,记忆总是以相同的方式拉开序幕。
自从我初次走进这里,就再也无法离开。
人虽然创造了一切,但有些重要关头是不容分说的,必须重新作出安排。
就从釉青笔记本的第一页讲起吧,拥有这两个名字的人:李明妙,目前居住在上海,为一家杂志社工作。
桑青彭措,一个带刀的木雅藏人,他的家在子梅。
没遇到桑青之前,我从未听说过子梅村——它在哪里?
一直走。桑青望向远方:一直走到四川甘孜州的贡嘎乡,走到城市消失,没有路的地方。在海拔四千米之上,居住着木雅藏人。整个子梅村只有十户人家,分布在冰川融化而成的狭长河谷里。没有电网,没有通讯,没有公共交通,没有卫生排水系统,没有农药和化肥。道路是土质的,大雨后会被淹没。
这就是桑青出生的地方。
子梅村有六十几个居民,他们种植青稞和土豆,养育马匹、犏牛和山羊,还有几只猫。每年夏天,高山草甸上琉璃草盛开,大片蓝紫色花朵,金色阳光照耀着海拔七千五百五十六米高的贡嘎山主峰,雪豹埋伏在灌木丛里,捕杀前来饮水的小动物。
子梅人秉性纯真,信仰虔诚,接受清苦的生活,也不畏惧缺乏氧气的环境。
桑青说,人为了获得一切,便要失去一切。
他以这种方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