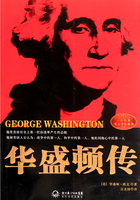这个从未得到善待的女子,曾经在黑暗中疯狂地纠缠他,亲吻,尖叫,厮打,只是为了挽留他。他生气了,用力掴她,打得她跌倒在地上,又慢慢爬过来,抱住他的腿,哀哀哭泣,说你不要走,我会听话。
他像野兽一样呻吟,咆哮,整个人跌坐在椅子上,靠着椅背,两手磨搓过脸庞,又磨搓过头发,累坏了一样。她害怕了,不再挣扎,缩成小小的一团,抱着他的腿,显得很可怜,这让他的坏脾气又冲上来,从地上拎起她,拖进浴室,捏着她的下巴,强迫她仰起脸对着一面镜子。她的眼泪刷刷地淌下来,他说:像你这样撒野,哪个男人也受不了你,滚开!
他拒绝见她。
在两个人的战争中,她从未赢得他。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她躺在这儿,再也不用祈求,呈现出一种他不曾想到的高贵和冷淡,竟然令他陡然间心生爱慕。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她一直想要深植在他心中,办不到,宁肯死给他看,也只有像她这样充满黑暗气质的女子,会不顾一切地死了两次,直到把活生生的一切全变成死亡。现在他终于注意到了她的存在,一具死尸赢得了他的心。
他这样的男子,心如宝石,坚硬名贵,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风流韵事不断,也相对喜爱过某个女子,他也并不愿意承认,那个不管不顾杀掉自己的女子,如同一道闪电,竟然在坚硬的宝石表面留下了一道明亮擦痕。经历越多,他就越是明白,再没有一个女子能够像她那样,那么动情,拿命去换,被这样的人爱着实在太美了,他再也没有遇到过。
是在她死后,他才真正开始惦念她。
他得到一张黑白照片,她的,坐在花坛边,双手端端正正放在膝头。他喜欢这个样子,他把照片放在钱包里,保存多年。
事情并不复杂,你怕什么,它就一定会来。
男人站起来,摇摇晃晃,可能很快就会倒下去。
听我说——他舌头有点发硬——我见过很多美人儿,你和他们不一样,我可不愿意你变成别的模样,也不愿意别的男人来围着你,男人都像公狗一样。
明妙脸色发白,男人鼻子里喷出酒气,让她紧张:
我不认识你。
他靠近一点,张开手掌,想要抚摸她的头发:你怎么气鼓鼓的?别这样对我,她比你漂亮,可是你更年轻,我喜欢你的脸。
明妙挡开他的手,抵御不了这强大的羞辱:别碰我,你的手很恶心,如果我也死了,就不必讨厌你。
他脸色一沉,旋即轻浮地笑起来:你难道不是我的宝贝吗?你不该对我这么放肆。
他压低声音,俯下身,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
这对峙不知道怎么收场。
男人突然伸出手,一把搂住明妙的腰,对着她的耳朵说:我得好好管教管教你。说着,他的另一只手熟练地伸到她胸前,握住她,狠狠捏了一把,没等她叫,他猛地推开她,端起桌上的酒杯扬长而去,看也不看她。
明妙耳朵里嗡地一响,心里有什么东西抽搐着,像要昏厥过去。有人拉了她一下,让她坐下,递过来一杯水。她低下头,看见红酒渍溅在胸前,衣襟上留下几枚脏污的手指印,一时有点不能相信。
小提琴的演奏声破窗穿云,酒杯正在碰撞出美妙的声音。
明妙,你什么都可以做得到,别忘了你是女人。小姑这样说过:对付男人们并不难,他需要你的时候给你下跪也干,什么都肯听你的;如果他不需要你,最好别理他,离他越远越好。要记住这个秘诀:你要让他需要你,难以离开你,直到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怎么才能办到?
小姑咯咯地笑出声音,很放肆,把手里的烟头一下子扔得好远,直勾勾地看着她,说:首先,你得吸引他。
明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慢慢地看清楚了眼前的一切:灯光璀璨,穿制服的人端着银盘,圆桌中央有青色莲蓬散发芬芳,几个人在旁边调情。明妙露出一抹微笑,细若游丝,她缓缓转动桌子,把一盘黑胡椒牛肉粒端到面前,用手捻起几粒牛肉,放进嘴里,手指上沾满了浓稠的酱汁。然后她站了起来,端着盘子,边走边吮吸手指,走向宴会厅中央。
宴会的中心位置摆着一张大桌子,那个男子坐在一侧,拍着身边同僚的肩膀,正说着什么,几分酒意,几十年的神气,令他得意扬扬。明妙走过去,站在他身后,想了一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男人停下来,迟缓地转动身体,不等他转过头,明妙已经想好了,她举起盘子,瞄准他的头顶倾倒下去,浓稠的黑胡椒汁液滚滚而下,如同熔岩喷发,粗暴地覆盖了他。
有人惊呼一声,打翻了酒杯,整个大厅瞬间悄无声息。
众目睽睽中,女孩放下手里的盘子,褪掉身上薄如蝉翼的衬衫,径直丢弃在地上,头也不回地走出大厅。她显然什么都没准备好,赤裸着身体,也丝毫不感到害羞,因为反抗的力量那么强烈。
夜色微凉,路灯在阔叶树木之间发出温暖的光芒。
真年追出来,大步跑到她背后,脱下外套,裹住一意孤行的女子。她微微颤抖,手臂抱在胸前,不看他,也不停下脚步。一只巨大的蝙蝠从半空中掠过,明妙抬头看了看,他趁机审视一下她小小的脸,没有泪水,没有感激,也没有表情。两人无声无息地往前走。
一直走到道路分岔处,那里有一株高大的紫藤,沉甸甸地伸展着花枝,如同黑色瀑布直泻而下,呈现出过分庄严的景象。明妙停下来,一言不发,盯着真年的眼睛。
真年也停住脚步,并不靠近她:让我送你回家。
她摇摇头,呼吸平静。
树木投下浓郁的暗影,他们对视了一会儿,真年并不让步。
明妙转动眼睛,忽然说:我们来玩捉迷藏,你从一数到十,来找我,找到了就让你送我回家。
真年有点惊讶,不得不听从她,背转身,沉稳地从一数到十。
夜色暗沉,风在树木上显现出它的形状和力量。等到真年转过身,只看见松枝簌簌摇动,枝桠上挂着他的外套,明妙已杳无踪影。
树丛中小径分岔,条条道路都让人对这个世界产生一阵阵想象。
真年从松枝上摘下外套,手伸进去摸索,她什么也没留下,连身体的温度都不在这里。真年一向认为自己了解女人,能够吸引她们,但他竟然无法猜测这个小女孩的心意,这让他心跳加快。他把鼻子埋进外套里,深深吸了一口气。这个夜晚犹如一把斧头,迎面劈开了真年内心冻结的海面,那呼啸而来的,是早已存在的渴望,它隐藏在时间里,一经显现,便再也不可遏制。
电台直播间在长走廊的尽头,由于各种屏障的限制显得格外幽深。
明妙站在窗口,翻看一份报纸,报纸刊登着:宝藏猎人布洛克·洛维特和他的探险队搭乘俄罗斯考察船,前往北大西洋,他们寻找一艘沉船——泰坦尼克号。明妙闭上眼睛,想起电影中的一幕,杰克缓慢地沉入冰冷的海水之中,萝丝活下来,完成他的心愿:无论人生多么艰难困苦也不要放弃,勇敢地活下去。她做到了,在没有他的时光里,爱了八十四年。
红色的字一跳,直播间门上的“录音中”变成了“休息中”。
胡老师推门出来,一眼看见她:姑娘,你来啦。
胡老师的口气饶有趣味,她招招手,示意明妙一起进入办公室,在狭窄的写字桌前坐下。
明妙第一天来到电台,就跟着胡老师学习。她有一种纯朴的气质,容易感动,容易和人亲密无间,明妙觉得她皮肤上的气息像妈妈,她总是叫她“姑娘”。
姑娘,这些天你在干什么哪?
胡老师伸出孩子般的小手,抚摸了一下明妙的脸颊,这个亲昵的动作唤起了明妙温柔的笑颜。
自从颁奖宴之后,明妙接到通知说不用再来电台,她有两个多月没有见到胡老师了。上课之余,她又接受了几个广告公司的文案,还有动画片的配音,常常睡眠不足,眼圈有点乌青。
她老老实实回答:我在赚钱。
胡老师觉得非常可笑,瞪圆了眼睛,终于忍不住笑出来:姑娘,你可一点儿不像个年轻人。你赚什么钱啊?没钱就跟爸爸妈妈要,坐在爸爸腿上,缠着他,女儿是爸爸的小情人呢,他才舍不得你受苦。
明妙有点发呆,想起一些旧照片和自己写在硬皮日记本里的话。
八岁,明妙想要成为一个潜水员;九岁,明妙怀疑神明,相信鬼;十一岁,她写道:这世界上的某个角落,一定有我真正的亲人,他们也在找我,他们会非常爱我。父亲看到这段话,怒不可遏,他绞着双手,关节嘎巴响,明妙如果是男孩子,一定会被他抓住打个半死。
女孩害怕极了,在晃动的电灯下,她冲父亲大喊:你抱过我吗?她痛哭着跑出去,在黑夜里流浪。她躲在大树背后,听见母亲四处寻找,呼唤她的名字,脚步焦虑地从树下跑远。她不作声,也不知道想要怎么办,泪水早已干透,脸上的皮肤紧绷绷的,如同濒临破裂的茧。
僵持到子夜时分,小女孩又饿又累,无处可去。她返回家,想要在楼梯下面的角落里睡一会儿,摸索着爬进去,手上头发上沾满尘埃,却发现有个疯女人早已睡在那儿。小女孩惊扰了她,疯子冲出来打她,咒骂她,力大无穷。有那么几分钟,明妙几乎丧失了全部记忆,她歇斯底里地尖叫,直到发现自己被父亲抱在怀里。
她哭得奄奄一息,父亲的脖子被她抓出几道血痕。他抱着她,走到没有灯光的僻静处,轻轻拍着她的背,说没事了没事了,小女孩在抽泣中渐渐睡去。
他们谁也不再提起这件事。
明妙十三岁那年,小姑回来了。有一天晚上,父亲忽然叫明妙一起去散步,静静地走了很长一段路。回来的时候,父亲对她说:一个人没有多少东西属于自己,但眼泪是别人没有的,所以很金贵。有时候你忍了好久,就是忍不住,非哭不可,那就事后再哭,一定不要当众哭出来。明妙,你长大了,你要记住,除非和深爱你的人在一起,你才可以想哭就哭,否则决不要哭出来。
这世界上不可能有那么多爱你的人,别人看见你哭反而会笑,会更加欺负你,如果你非哭不可,那就不要让别人看见。
一直以来,明妙和父亲之间的交谈非常稀少,他从未一口气讲过这么多话。
明妙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摸了摸父亲的手背,指尖在那里停留了一下,又翻转过来,握住他的手掌,贴在自己脸上。父亲微微发抖,她从未这样表达过对他的感情。
十七岁生日,父亲送给明妙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父亲清俊严肃,站在公园里,怀抱着明妙,旁边的花圃里开满热烈的花朵。明妙大约一岁半的模样,梳着羊角辫儿,吃手指。父亲只说了一句话:你是我唯一的女儿,我怎么能没有抱过你呢?
这句话,他记了六年。
她也牢牢记住父亲说过的话,决不当众哭出来,在特别快乐或者特别难过的时候,别人看着她,她只是微微笑。
胡老师不断地凝视着明妙,打断了她的回忆:姑娘,你知道吗,所有的人都在议论李明妙,连传达室的大嫂都来问我:扣盘子的女孩是哪个啊?胡老师,你徒弟是生猛海鲜,可了不得啦,这算怎么回事儿?
胡老师模仿着传达室大嫂的样子,边说话边挤眉弄眼,不等明妙回应,自己先咯咯地笑得不行。她一只手叉着腰:姑娘,你把一盘子菜扣在人家头上,真没礼貌。和你比起来,我们根本都是迟钝的人。你不得了,敢想敢干,还敢就这么光溜溜地走了。
听她这么说,明妙有点害羞,又觉得松了一口气,脸颊微微发烫。
胡老师,你没生气啊,我有没有给你惹麻烦?
她皱皱眉毛,眼睛里快速闪过一抹光亮:
姑娘,你天生就会干怪异的事儿。这些天我一直替你担心,不知道这事儿算不算收场了,可是昨天有个大人物打电话到电台,专门提到你,说年轻人喝酒胡闹,只当是个玩笑。主任就把我叫去了,让我通知你回来工作。
明妙有点蒙,手脚微微发凉,不懂她在说什么。
胡老师观察着她的神情,只好又说了一遍相同的话。
明妙同样只是哦了一声。
胡老师急了,把卷起的袖子又放下来:姑娘,你还真是糊涂呢,这事就算过去啦,哪个大人物帮了你的忙?要记得感谢啊。
明妙认真想了一会儿,有点苦恼地承认:我不知道。
又过了一周,明妙见到真年。
他特意来接她,并不出现在电台门口。明妙下了节目要去乘公交车,去车站的路经过松园——松园在古老城墙一隅,种满松树和竹子,开着一扇小小栅栏门,常有京剧票友们在竹林里排练,咿咿呀呀唱一段《空城计》。
真年站在栅栏门旁边的角落,已经是深秋了,他穿着黑色羊绒外套,里面是烟灰色的背心。
竹叶微黄,在风里沙沙作响,他望着明妙微笑:欢迎你回来。
明妙心念转动,直截了当地问他:是你帮我吗?
电话不是我打的,我只是恰好认识一些人。
明妙傻傻地哦了一声,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脸上红红的,好半天憋出一句:要谢谢你。
不用,我喜欢你。他根本没打算掩饰。
明妙更傻了,小小的脸庞木呆呆的。
真年看了一眼庭院里摇曳的竹子,走过来,拉住明妙的手腕:跟我走。
他来接她,等她,不容置疑地照顾她,他认为这很自然。
年长令他拥有一种特权,他握住她的手,说怎么这么凉,我帮你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