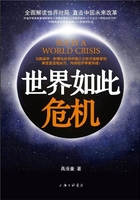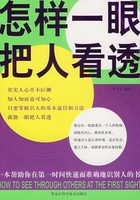当然不仅是那些具有强烈统治欲的掌权者需要一场战争,这场危机及未来世界的快步发展都需要一场战争。诚如国泰君安的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所认为的:从1945年二战结束算起,全球无大战事已经66年了,而一战与二战之间仅隔21年,长期维持世界或国内和平同样会堆积矛盾。国内维和的两种典型,一是莫巴拉克的强权统治,二是希腊的高福利,前者导致政治危机,后者导致现金流危机。
李迅雷对希腊事实上也是整个欧美世界的现状,描述得很到位。福利主义之父霍布森主张国家制定干涉计划,他强调必须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社会福利问题是改革的中心点。国家要发挥积极作用,制定全面的福利政策,兴办多种福利事业,实行失业救济、免费医疗、老年抚恤和业余教育,改变不合理的财富占有和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实施强有力的干预缓和社会矛盾。对此,李迅雷将高福利支出而带来的现金流危机、债务危机称为“太平盛世的代价”。
这种内在不稳定、硬靠福利制度维持而造成的昂贵的“太平”,事实上已让世界各国接近破产边缘。按照目前的治理之法,如果没有一场世界性的大战来对当前的这种恶性循环机制予以结束,那就必然是以各国政府破产而告终。
从历史上看,承平日久,国内国际都会产生矛盾,战争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甚至化解很多问题。但战争本身重建不了新的世界秩序。它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性,却可以促使人类思考。而正是这种思考,为未来世界秩序的重建提供了可能,因为变革只能产生于价值观念发生改变和经济上有必要之时。当个人价值和社会利益结成同盟时,社会变革才能开始。只要社会利益上的动力还没有出现,关于共同努力的新价值观念都会被视为傻气十足的。
在毁灭中反思
在大灾难面前,当人们终于意识到自己所遵循的透支行为,自己所坚持的消费主义只会给自己带来毁灭时,他们必然会像抛弃一个罪恶的统治者那样,抛弃掉那些该死的价值观——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的终结
谁在统治我们,也许你会对这样的问题感到愕然,然后稍作思索答道“我们的政府啊”。从政治结构来说,我们确实是由政府所统治;当然也有一些激进的反西方人士认为,真正统治我们的是那些西方帝国主义政权,他们能指出千百条理由;也有人会告诉你统治这个世界的是诸如骷髅会这样的秘密组织;更有诸如宋鸿兵者,他会告诉你真正统治这个世界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
但我却认为当前真正统治这个世界的是消费主义。它远比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甚至各种各样的宗教更有市场,对人们的影响也更为深刻。事实上它已完全超越了目前我们所能够界定的国界、文化界限,它在世界几乎每个角落里生根发芽,它的生命力和繁殖力就像细菌一样惊人。
在美国,经济学理论指出,家庭、企业和银行如需借更多钱,偿还前一笔借贷的本金和利息,就是层压式骗局参与者。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引用数据,指出美国家庭的债务占收入比率15年前仅为65%,到2008年已升至135%。对此鲁比尼认为美国已经沦落为典型的偷来的层压式骗子之国,对于美国人而言“麦道夫就是我们,骗徒就是我们”,至少鲁比尼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应该在镜中看清楚自己:贪婪的骗徒就是我们”。
而这种人显然并不仅仅只出现在美国,同样也出现在欧洲、日本、中东、中国,在我们身边,甚至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所有的人只能在香水、皮包、手机、汽车的消费中寻找到自己的灵魂。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隐藏的诱因》(the,Hidden,Puesuaders)一书提到百老汇一幕剧的场景:主人公的儿子呼喊着“我要的东西很多,简直要疯了……金钱就是生命”。
或许有人要为自己辩护,他们会认为我们获取的只是便捷性而并不是财富。但用亨利·乔治的术语来说,工业化给我们带来的全部好处,可涵盖在“财富”这一概念内。在这种定义下,虽然你不是资本家,你追逐的也不是金融产品,但你所追求的便捷性事实上与贪婪的资本家所追逐的金融产品具有同一的特性,那就是贪婪无度的对未来财富的索取。因为你的动机已经忽视了其他人的福利——你的儿孙们的福利。除非你做丁克,否则,你一定在偷吃儿孙们的蛋糕——那些本属于他们的有限的自然资源,并强行给予他们那些本不该属于他们的,因我们透支消费而来的大量的账单。我们与我们的儿孙们、我们与我们的未来已经全面失衡了,这正是当前乃至未来最大的危险。而造成这种恶果的,正是统治着我们心灵的消费主义,它像灵蛇一样唤醒了我们身上每一个贪婪的细胞。
在这里我所谓的失衡,泛指的是贪婪的人性所支配的消费欲望的无限与自然资源的有限之间的失衡、当前的繁荣和世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失衡。套用汪丁丁教授的话说,那就是“我们为增加自己的便捷性、自己的稳定,让自然环境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支付代价。”
休谟曾说过:“社会动乱的最大根源在于人们互相争夺财产的无限欲望。”互相争夺的无限欲望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固有的弱点、人性固有的弱点。环境的危机、能源的危机、信用的危机——实际上都是人性的危机、是心灵的危机、是人性贪婪引起的危机。这些危机被当前统治我们的消费主义无限地放大了。
人类正患着一种叫“欲望的亢进病,”,像“甲状腺功能亢进病”一样,“欲望的亢进病”也存在着三多一少,即多占、多耗、多污染、少资源。地球的空间和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有限的资源无法填满无限的欲壑。即使环境恶化不是人类造成的,资源枯竭却是即将到来的事实。这也就决定了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是不可持续的世界,人类会自取灭亡。而当今人性的最大弊病就是:破坏了当代,更严重地透支着未来。
现行的欧美经济发展模式,就是一种典型的鼓励消费或者说是一种典型的鼓励贪婪的社会体制,它的各种政策,譬如以低利率为表现形式的货币政策,都只是为这种体制而服务的。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被怂恿、诱惑去购买更多新的商品,去不断地浪费社会资源。这种浪费和贪婪造成的过度消耗,加重了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统治我们的不是政府,而是鼓励我们贪婪、纵容我们透支的消费主义。
每一次世界大战,都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更意味着一场根本性的系统重建的开始。随着人类因为自己的罪孽而酿就的灾难越来越具有破坏性,人们会发现,如果不做一次革命性、根本性的系统重建,人类就将彻底毁灭。为了生存,人的思维将再次无限至上。我们可以一次次从灭顶之灾的边缘抽身出来,同样我们也会再次做到。在大灾难面前,所有人,必然会开始反思人性。
所谓的反思人性就是批判人性中那毫无节制的欲望和贪婪,审视自己是否就是那个我们在诅咒的“格林斯潘”“麦道夫”,并进一步地检讨当前以“物”为表现形式的经济模式是否合理,是否能够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基于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世界终有一天是会归于毁灭,但我们期望的是我们能够尽量活得久远些)。
然而,就如同个体的人一样,要摒弃一些有悖于现存的核心价值的过程将是一个令人痛苦的过程。而到什么时刻,一个人又会视个人生命于不顾呢·现代世界,有数百万人面临这样一个抉择,为了活命,是出卖亲朋好友,屈服于独裁者的淫威之下·还是背井离乡,流亡海外·国家和社会又何曾不会面临同样的抉择呢?
所有这些决定都含有赌博的成分。当前的这些核心价值观固然会带来毁灭,但简单地摒弃这些价值观就一定能带来生存的希望吗?
新旧交替时,阵痛和彷徨自然是难免的。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成败的关键在于知道哪些核心价值观应该继续尊崇,而哪些价值观则应随着时代的变化予以摒弃,并去探寻适应新时代的新的价值观。
在人类可持续发展这一问题上,整个世界都面临着类似的抉择。所有这些发生在过去和现代社会的重估价值观的行为尽管艰难重重,但它们都实现了。英国人在17世纪,在原有的体系和传统中重估价值观,并勇敢地做出了根本性的系统重建,以此为后世开创了全新的发展模式;同样,中国能够在1979年后,在政治与经济一片狼藉时,在毫无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的前提下,勇敢地做出了根本性的系统重建。那么有什么理由怀疑我们再次勇敢地对系统做出根本性重建的能力呢!,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对未来灰心。抛弃消费主义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消费,也不意味着我们像苦行僧那样刻薄自己。亚当·斯密在其《论国民与国家的财富》里指出“消费是生产的唯一目的和宗旨”。对我们而言,当前和今后所要做的是节制,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有节制的消费观,我们需要的是考量地球的承载力和我们欲望能否平衡的消费观,而不是一味地放纵的消费主义,正如休谟所论“一个文明社会也必须对这种天然的欲望加以制约”。
民粹主义的黄昏
所谓的民主,在政治学的表述中,其核心就在于选择。但商品交易中,事实上很多消费者并不能确知自己到底需要什么,而促使其消费的,往往是企业的诱导。在政治领域这点同样成立,我们的公民,事实上对其所需,往往亦不能有一个确切的认识。他们的选择,跟消费者一样,完全是在政党——政策提供商的诱导下做出的。
当然政治又与纯粹的商业还是有些区别的,譬如一家电影公司可以完全无原则地迎合观众的趣味,哪怕那种趣味是多么的低级,因为通过市场,受影响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但作为政策的提供商的政党,如果其施政纲领仅仅只是一味迎合民众,这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根据民主原则,当某些政纲被公民的选择确认,它将会成为政策,影响的是所有的公民。从这点可见,今日被人归为暴政的政策,应该归罪于政党——那些政策提供商更为正确,正是他们一味迎合公民的民粹做法,误导了公民。
洛克曾指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天然的政治,没有谁天生就是统治者,而另一些人天生就该被统治。按照自发秩序论的观点来看,政治就跟语言、货币、法律一样,不是天然的东西,它是一种社会的产物;这种社会产物不是被发明的,而是在现实生活中逐渐发展出来的;从没有政府的社会(所谓“自然状态”)到人们愿意生活在一起,并服从固定的权威,再到建立政府,形成政治关系,用休谟的话来形容那就是历史的演进。
休谟甚至认为,政府根本不是必需的,在一个原始野蛮的社会中政府完全没有必要存在,只是在较为发达的社会才成为需要。他说:“起初,每一次首领行使权力的活动都是特殊的,它所针对的是具体的紧迫情况。由于他的干预带来了可以感觉得到的好处,这种权力的行使开始变得日益频繁;这种频繁性逐渐在人们之中导致了一种习惯性的,甚至是自愿的(如果你喜欢这么说的话),因而也是不稳定的默认。”
人们为什么会接受政治呢?货币的出现是因为人类天性的便捷性诉求,而人类对政府的诉求则来源于互利和安全。休谟认为人类没有任何服从权威的自然天性,却有追求自身短期利益的自然倾向。自身安全和利益受到的直接威胁,迫使人类放长眼光,看到了服从权威是相对有利的。建立政府的目的不为别的,只为互利与安全。从这点我们可见,休谟对政治的理解是:权力的双脚只能站在保障互利与安全的职责范围内。在这个范围内,它的正当性是可以证明的,超出这个范围则不然。
正如上所论,民粹主义有其积极的一面的。它强调平民大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它把平民群众的愿望、需要、情绪等当做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它肯定了平民大众的首创精神。但民粹主义过分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哪怕这种情绪和意愿,从长远看明显不利于社会进步,它也坚持这种极端平民化的主张。因而,从社会发展和平民大众的长远利益来看,它又无可争议的具有莫大的消极作用。
因此,如果长期保障我们互利和安全的政府,没有走出人类个体的局限性——不放长眼光,只片面地追求自身短期利益,为了选票,哪怕民众的情绪和意愿从长远看明显不利于社会进步时,也还是会一如既往地绝对顺从——那么这样的政府本身就缺乏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政府需要做的,首先是彻底摒弃只知道一味迎合公民趣味的民粹主义,我们的政客们需要进化为真正有思想有抱负的政治家,进化成创造性的领导者,并且能诉诸社会,以带动大众。只有这样我们的文明才能进步、社会才能发展,经济才能繁荣,人民才能安康。
回归资本主义
也许有读者在看到这个标题时不免要诧异了,难道美国、欧洲不是资本主义吗?为什么有学者亦将我们中国也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我在这里所讲的“社会主义”与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差别很大,这里有必要对此加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德国和奥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时计划经济体制、罗斯福新政……总之,一切具有国家干预倾向的思想和政策,我们统将其按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认识,归于“社会主义”名下。基于相近观点的还有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刘瑜,刘瑜就曾指出:社会主义不应仅仅只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结合,它还包括广泛的福利制度。这一观点也得到了美国知名政治系家李普赛特的认同。
缩减福利支出
福利制度,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追根溯源,让我们从认识现代福利制度之父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Atkinson,Hobson,1858~1940)开始。霍布森,英国政治思想家,经济学家。1858年7月6日生于英格兰一个富有家庭,1940年4月1日卒于汉普斯塔德。毕业于牛津大学,毕生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积极投身于英国社会改良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