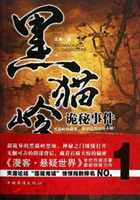冯伯义说得一点不错,乔仲正此时的确在皇宫里逛来逛去,一个晚上的圈子兜下来,越兜越是得意,自忖凭他那些训练有素的太监的身手,再加上这般布置,实可谓天罗地网,滴水不漏,到时候只须再拿下几个紧要人物,全朝文武必定乖乖俯首听命。眼见这边布置妥当后,乔仲正掸了掸衣袖,带着两名得力手下,慢慢向万昭宫走去,那惠妃娘娘可是个棘手的货色,若非她当初多管闲事,冯伯义怎么可能活到现在来与他为难?不但如此,她还装腔作势大唱空城计,打个风平浪静的幌子出来障人耳目,暗地却指使冯伯义坏他好事,想到这里,乔仲正恨恨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不由加快了脚步。
进了万昭宫,乔仲正一本正经道:“奉圣上之命,听闻惠妃娘娘玉体有恙,特来拜望。”说完便抛下面面相觑的众内侍,与两名手下径向沾衣卧室而去。快接近沾衣卧室之时,乔仲正示意两手下停步把风,自己则轻轻走上前,把门拨开一条缝向里偷望,只见沾衣坐在窗前,手托香腮,偶尔拨弄一下旁边的瑶琴,多数时候兀自出神,不知在想些什么,或在等什么人。乔仲正见沾衣对他毫无觉察,不禁窃喜,暗暗运气,突然推开房门向沾衣扑过去,风一般晃到沾衣身后,瞬间便用金针刺入了她背后的数个要穴!
沾衣还没来得及出声便倒在地上,她盯着乔仲正,眼神又惊又怒,乔仲正嘿嘿奸笑着,又用金针刺进她的胸腹几大要穴处,末了仍不忘点了她的哑穴,道:“娘娘,这针上喂的药足够您安心睡上三天,期间老奴会教那些奴才好生伺候您,待皇上归了天,大殿下即了位,再送您风风光光去下面服侍皇上,岂不美哉?”沾衣气得满脸通红,但浑身受制,根本动弹不得,又叫不出声,只好任凭乔仲正将她放到床上,拉过被子捂得严严实实,乔仲正又放下床帐,布置得仿佛沾衣正在床上歇息一般,然后背着手冷笑着离去。
回到万昭宫正厅,乔仲正煞有介事宣布道:“娘娘自觉身体不适,各位除非获传,均不必进房伺候。”众内侍见是乔公公亲口所言,哪里敢有质疑?纷纷口称遵命。出了万昭宫,乔仲正对那两个手下吩咐道:“你二人自现在起到明日未时,须在这里寸步不离地看守,不许任何人活着进万昭宫,也不许让万昭宫内任何一人活着离开!”
齐庭轩静静矗立在夜色中,此时更是笼罩了几分阴沉,冯伯义轻轻攀在檐下,从窗缝窥视屋内,焦急地等待小全子离开皇上的病榻,哪怕只有片刻,也足够他让皇上服下解药,这解药虽说不能将毒尽驱,至少可缓解病痛,使之病情不至恶化。可等了足足半个多时辰,小全子依旧没有离开之意,冯伯义无奈之下,从怀中摸出枚石子握在掌心,心道:“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举,你不离开,我就救不了你主子,只有得罪了!”正欲隔窗发去,忽然室内走进一人,小全子见了那人,慌忙下拜:“见过乔公公!”
乔仲正袖着手笑道:“免了免了——皇上龙体怎样?”
小全子神情忧郁道:“回公公,明日就是皇上册封东宫的大日子,可皇上从今早一直昏迷到现在,奴婢刚才去寻了众太医来,他们少时就到。”
“你果然忠心不二!”乔仲正大笑道,突然闪电般出手,扼住小全子的咽喉,小全子顿时一脸惊骇,却又发不出一丝声音。乔仲正将嘴巴凑近小全子的耳朵,轻笑道:“若明日皇上在满朝文武面前未及宣诏就驾崩的话,你认为谁该即位?”说完两指微微用力,只听一阵骨头碎裂的声音,小全子张大嘴巴,头向一侧歪去,手足抽搐一阵,不多时便一动不动。乔仲正从容将小全子的尸体移到皇上的床下,起身之时仔细凑到皇上脸前查看半晌,见皇上脸色发绀,呼吸甚微,便满意地点了点头,袖起双手,若无其事地离开齐庭轩。
冯伯义在窗外见乔仲正冷不防杀死小全子,已是愤怒异常,好在乔仲正并未继续对皇上下手,否则他必扑进屋内与其拼个你死我活。这时听得院里悉悉簌簌的脚步声,冯伯义从檐下悄悄探身观看,只见乔仲正的几个手下在这齐庭轩的院内前后巡视,当下在心里冷笑一声,将手中石子飞出,打断三丈开外一棵松树的边杈,那几人果然吆喝着向松树包抄过去。趁这当口,冯伯义敏捷从窗户钻进了屋,几步便奔到皇上跟前,掰开他的牙关将瓶内解药灌了进去,待确信皇上完全服下后,略略观望四周,飞身从另一边窗户跃了出去。
慎王府内,祐骋翻来覆去良久难眠,邵敏自然也睡不着,她虽不知父亲与祐骋一直在商议什么,但心里清楚这次立嗣的结果,必关乎夫君乃至整个慎王府的存亡。不过她也早已做好打算,无论结果如何,生也好,死也罢,她都跟定祐骋了,这么一想,心里自然安定了不少,甚至还有几分愉悦。
已至三更,祐骋呼吸渐渐平匀,似已睡着,邵敏轻轻披衣下床,走到院内,望着黑沉沉的夜空,冷风有一阵没一阵吹在她身上。她微微打着冷战,不禁将外衣拉得更紧了些,这时风里送来一阵若有若无的歌声:“十年修渡,百年修住,千年许返轮回处。意何如?情难书。心言万牍终无属,长痛已平待日暮。生,独自去!死,独自去!”歌声苍凉沙哑,音调虽无太大起伏,但个中无比的凄清如海浪一般绵绵不休向她直压过来,邵敏凝神听毕,不知不觉竟泪流满面。
“敏敏,你哭了?”祐骋不知何时悄悄站到她身旁,见邵敏梨花带雨的模样,不禁心疼起来,将她拥在怀里,“外面冷,敏敏,我们进去罢。”
邵敏站着不动,猛然搂紧祐骋的脖子,抽泣道:“我好怕,我怕你会丢下我一人在这世上……骋哥,无论怎样,我们都不要分开好么?”
祐骋从未见邵敏这般动情过,见她眼眸里溢满痴爱柔情,鼻子不禁一酸,也紧紧搂住她道:“好!敏敏,我答应你,今生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分开,我们都不会分开!”
就在这时,突然听得嗖的一声,一道寒光飞过,打在他们身后的廊柱上,吓了他们一跳。祐骋转身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根袖箭带着一个锦囊钉在那里,箭尾还微微颤动,他忙将它拔下,打开锦囊,从里面掏出一幅布帛,上面的字迹苍劲潦草,写道:“夜半打扰,望勿见怪,魏言之兵马确已近京城,拟明日午时柢京,京东十里外天门谷为必经之路,地势险要,老夫已请朱将军于彼处略做文章,以滞其行。……”祐骋看到这里感觉心头被什么物事撞了一下,那天门谷不是别处,正是当初他被沾衣救起的地方。
邵敏见祐骋盯着布帛怔怔发呆,便轻声问道:“殿下,这上面写的……可是有了变故?”
祐骋这才从出神中回转,忙道:“不……没什么。”他略带歉疚地望了邵敏一眼,继续看下去,只见布帛后面写道:“乔贼手下,何人何处,老夫已探明大半……”往后若干行密密的小字,皆是在各个宫内侍奉的一些太监的名字,近二十人,其中有些祐骋曾听眼线禀报,确是乔仲正的手下不假,但不及这布帛上面列出得全面详细,让他心中一阵兴奋。再往后看去,只见布帛最后写道:“……悉心布设如是,然明日一战,绝不可以轻心掉之,惟慎之再慎,方有望全胜。若老夫有幸不辱所托,助殿下荣即帝位,便欲出世离尘,从此不涉江湖,专心归隐,此言暂先示之,免生突兀。……”
这布帛毫无疑问是冯伯义给他的,可这末尾几句,分明就是诀别之意,莫非明日以后,他便从此再也见不到这位冯前辈了么?祐骋想到这里,心底涌起一阵强烈的怅然,这冯老伯虽喜怒无常,但睿智机敏,善察人意,与他认识以来的这许多天里,自己对他从敬畏到钦佩再到完全信任,不知不觉已将他当作一位忘年知己,心里委实一万个舍不得。但他也明白,自己再恋恋不舍,终究不能强求,这冯伯义惯看世事,定是不屑留在朝中任职,放他去做闲云野鹤,随他的性子度过余生,不能不说是件好事,但自己失却了这样一名高才,也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邵敏见祐骋神色忽而欢喜,忽而忧愁,再后来又变得凝重,便好奇问道:“这布帛是谁给您送来的?”
祐骋将布帛小心放进锦囊,揣入怀中,似没听到邵敏问话一般,沉思片刻,郑重对邵敏道:“敏敏,明日将会发生一件大事,你务必要按我说的去做——午时过半之时,若你还未得到我的消息的话……”
话未说完,邵敏便伸出玉手掩住了他的嘴,轻声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你这么快就忘记刚才对我许诺的话了么?”
祐骋怔了一怔,不知该如何做答,只好将邵敏再次揽进怀里。邵敏靠在祐骋的胸前,倾听着他强有力的心跳,低声喃喃道:“生,陪你去!死,陪你去!”
次日,十一月廿五,乃皇上册封太子之日,群臣之前早已接到圣旨,各自心情复杂。他们都知皇上的脾性,为免太子恃位而怠,皇上登基不多久便立下“非将崩不立东宫”的规矩,是以众皇子中祐珉和祐骋虽早成年,却始终仍以皇子的身份出入宫廷。如今皇上病中突然要立太子,可见自知时日无多,那么这太子到底为谁?众臣纷纷揣测起来。有人认为理所当然是大皇子祐珉,有人则认为三皇子祐骋更有可能,众说纷纭,不一而足,于是文武百官各自怀着自己的担心,老早就聚在齐庭轩外,静等午时那一刻。众皇子则更是忐忑不安,各自跟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在齐庭轩外徘徊,让众臣诧异的是,午时将到,却始终不见大皇子和三皇子的踪影。
午时刚到,乔仲正便从齐庭轩内走出请众人进去,众人慌忙进入,在皇上的床前黑压压跪了一片:“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立于一旁的乔仲正暗暗冷笑,兀自在心里盘算,皇上既已行将就木,这帮蠢人还尚且不知,过会他这个总领太监只须装模做样查看皇上一阵,故做惊慌喊出“皇上驾崩”四字即可。那帮臣子自然惊惶失措,此时皇上若真死了便罢了,若没死,自己稍动指头,便也可假戏真作,如此一来,便可瞒过宫中所有太医,届时珉儿再率禁卫军赶到……
“朕……怕是不可能万岁啦!”床上的皇上想是被群臣的呼声惊醒,便缓缓睁开眼睛,微弱笑道,“张丞相,王丞相,邵尚书,你们三人可在?”
“臣在!”左、右丞相和邵蓁齐齐应道。
“准备纸墨,朕口述立嗣之意,由张丞相笔录。”众人不禁愕然,皇上微微一笑,道:“朕虽病危,却不愿事先写好遗诏,免得有人质疑之或者篡改之,且如今病重此处,亦不能于正殿立嗣,此举虽于礼不符,却乃朕遗愿,诸位须谅解才是。”众人原本就不敢有异议,听皇上这么一说,纷纷附和,乔仲正在皇上苏醒的那一刻起便被惊得呆在当地,听到这会脸色愈加铁青,但不得不做出从容自若的模样。
皇上喘了几口气,一字一句道:“朕在位廿年,虽未有赫功,也鲜有昭过,人祸皆平,天灾可赈,铭记祖宗圣训,奉慈孝之心,行仁德之举,此为人君之本也。”说到这里,皇上停下来,众人都屏住了呼吸,一时间屋内鸦雀无声,静得连心跳的声音都听得出。
只见皇上急喘几下,吐字更为清晰道:“朕膝下皇子有七,三子祐骋,品端性平,智勇齐备,奉礼尊圣,可为帝君之选……”还未说完,皇上口中突然喷出一道暗红的血,身体摇摇晃晃,在场所有人不禁惊呼起来,乔仲正抢上前去欲扶,皇上从枕上勉力撑起半个身子,摆手示意他退下,喘气咬牙继续道:“……朕,立三子祐骋,为储君!”邵蓁三人将遗诏录毕,皇上又嘱咐道:“代朕……宣……宣……”未说完便瘫倒在床上,人事不省。
众人见皇上晕厥,登时乱成了一锅粥,这时齐庭轩外也乱哄哄一片,有人高声叫道:“禁卫军护驾擒贼!任何人不得出齐庭轩半步,否则格杀勿论!”正是祐珉的声音,乔仲正听了精神大振,纵身上前欲抢张丞相手中的遗诏。
突然从床后窜出一人将他拦下,两人打了个照面,那人嘿嘿笑道:“乔老贼,莫高兴得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