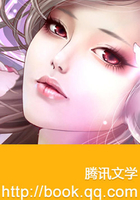转眼之间,战争已经持续了半月时间,半月里,南风朝内的政权已经渐渐稳固,南风皇帝南宫冕自遇刺之后便再也未露过面,只派二皇子南仲彦与定国王南笑睽共同主持朝中大局。虽然此事在朝廷之上受到众臣的多番质疑,但在二皇子与定国王以及丞相魏忠的高压手段下,那些质疑之声渐渐变小,最终销匿在朝堂之上。
如今,南风皇帝南宫冕的政权已被完全架空,所有的实权落在了二皇子南仲彦、定国王南笑睽以及六皇子南永阳的身上,而皇上只是一个虚有其名的摆设而已。
景阳宫里,一个面色浮肿,衣衫凌乱的中年男子颓然的坐在大殿的地面上,背靠着一张软榻,左手执着一方小巧精致的银质酒壶,右手拿着一只黄金铸造的酒杯,他就那样坐在地上,自斟自饮,不理世外之事,不管何年光阴,形容凄凉而颓废。
“皇上……”一个面大体肥的太监微微颤颤的走到那名迅速老去的帝王身边,带着几分心酸的出声喊道。
中年男子抬起头,看到那个熟悉的肥胖身子,咧嘴一笑,笑声犹若秋后的落叶般,带着萧索的味道,“胡同,你来了,来,陪朕喝酒。”
“皇上,老奴扶您去床上休息吧。”昔日南宫冕身旁的贴身太监一脸悲戚与不忍的走到那满身颓废气息的中年男子身边,从男子手中拿过银质酒壶与黄金酒杯,扶着男子朝大殿内侧宽大无比的龙床走去。
在刚要触到龙床时,之前还萧然无力的南宫冕突然暴起,一把推开胡同那肥硕的身体,一双醉意朦胧的双眼大睁,一条条血丝在那双迷醉的眼中清晰可见,他趴在床边,瞪大着眼,眼光不断的在大床上搜索着什么,他衣袍凌乱的爬上床,在床上一寸一寸的触摸,犹若瞎子摸象般,摸的那般认真,那般细致。
在他从床头摸至床尾,再从床尾摸至床头后,他暴怒了,回过头,狠狠的看向一旁的太监,“你说,远尘呢?你们把远尘带到哪去了?”
面对着面容凶狠,眼中泛着危险红爆的皇上,胡同碰的一下跪在地上,浑身颤抖着哭道:“皇上,您醒醒吧,奴才求求您了,远尘公子已经不在了,已经不在了。”
南宫冕从床上突然跳起,以迅雷之势奔到胡同面前,一手拉着胡同的衣襟,凶声吼道:“你胡说,你胡说,我明明就看到他躺在床上,就躺在那个位置,就是那里。”说着南宫冕放开了胡同的衣襟,转过身,遥指着之前远尘所躺过的地方,一脸的疯狂。
“皇上,您醒醒吧,奴才求求您了,南风就要大乱了,您快点好起来吧。”胡同跪在地上,头不断的磕碰着地,试图想要让这个沉醉于自我世界里的君王醒来,醒来主持大局。
南宫冕步伐虚浮的走近那张大床,高床软被,明黄色的锦帐,细滑柔软的丝绸被单,他的手轻轻的触上远尘所躺过的地方。突然,如想起什么般,他的眼中迸射出一股凌厉和慌乱的神情,他徒然转首,看到那个跪在地上不断磕头的太监,双眼迸发出仇恨的目光,“云妃,你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是你,是你杀了尘,是你杀了尘,是你,全是你……”南宫冕突然一步跳到胡同身边,双手死死的卡住胡同粗壮的脖子,死死的卡住,不留一丝余地。
看着那张在自己手中不断变白变靑的脸颊,那双布满仇恨的眼中带着几许快意与残忍,感觉到手中之人挣扎的力量越来越小,感觉到手下的身体越来越冰,他开始大笑起来,笑声畅快而疯癫。
他站起身,看着那个软绵到在地上已经没有丝毫气息的胡同,猖獗大笑,笑声传出景阳宫,传到很远很远之外。
远尘,我已经帮你报了仇了,我杀死了她,杀死了那个贱人,那个曾经辱骂你的贱人,那个将匕首刺进你胸前的贱人。远尘,我来陪你了,来陪你了,你且等等我……
南风冕帝十九年六月十八,南风第十代君主南宫冕驾崩,在位十九年,享年四十五岁。南风帝驾崩之后,举国哀悼,各国前来恭贺南风皇帝寿诞的使者在南风京城停驻大半月后,之前的寿诞变成葬礼,各国使节也终于趁此机会可以出得大使馆的门,重见天日。
此时,西南片区的战争还在依旧持续,这场内战已经打了大半月了,南永阳所带的军队与南俢禹的军队持久对峙,却始终不分上下,大半月下来,双方损失各半。南永阳兵多粮丰,又是正义之师,在全国人民正义的呼声之下,士气大振,一直以雄纠纠气昂昂之态冲锋对阵。
而南俢禹也是南风难得一见的将才,三十万西南军在他多年的带领下,骁勇善战,所向披靡,也正因此,在面对南永阳所带来的四十万正义之师,他的这支军队才能保持着该有的军人风范,没有害怕,没有退缩,勇敢的应战,战场上的厮杀更没有半分怯怕,他们跟着他们的将军,一步一步的坚守在邺城,对峙着那些要对他们赶尽杀绝的国民。
战争就那样一直持续,直到南宫冕驾崩的消息传到这片气氛紧张的战地片区。全国上下都知道南宫冕是被南俢禹派人前去刺杀,如今南宫冕驾崩,顺其自然的,各种讨伐之声全都朝南俢禹湮去。
南永阳手下大军在听闻这个消息之后,年轻的战士们愤怒了,通红着双眼,望着对面阵营里的年轻皇子,犹若望着仇人般,那是一种年轻的热血在沸腾,那是一种执着的信念在催动,对面的战营里,站着的是弑父杀君的逆子贼臣。
在南宫冕驾崩的第二天,两军再次对垒,南永阳白甲白袍,满目悲戚与激愤,坐下白色战马不断轻踏着马蹄,马鼻不断的喷出热气。在他身后的是三十万的士兵,黑甲幽冷而森严,每人头顶绑着白色孝巾,每一个年轻的战士脸上都带着悲愤,三十万大军气势如虹,声势震天,那些悲愤转换成了战争的力量,这支军队在面对着对面弑君叛乱的军队,没有丝毫畏惧,有的只是焚天的怒火,一把足以燎原整个世界的怒火。
朝阳缓缓升起,一轮巨大绯红的圆球在从遥远的地平线方向露出了整张脸蛋,那泛着金色的光芒一寸一寸的洒向对峙的两军,在他们身上染上了一片金红。
号角响起,嘹亮的号角声在整个旷野上响起,厮杀就此开始!那些盛着怒气的战士们挥舞手中的大刀长剑直捣向对面只剩二十万的贼子军团,顿时,厮杀声,喊叫声,马嘶声,怒吼声,在这片染着金红朝阳的大地上响彻,蜿蜒的血河在这片旷野上形成,脚下的青草早已被大军践踏得不成样子,飞扬的尘土被浸染上了鲜血的颜色,一点一点的如雨水般沉落在地,然后黏在那些高帮军靴上……
残尸断骸铺满了这片平缓的西里破,尸体若小山一般的堆积而起,那些被血与汗所覆盖的一张张年轻脸庞上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与狠戾,一双双年轻明亮的眼早已蒙上了鲜艳的血红。
南永阳坐在高高的战马之上,望着对面那个一身黑甲的阴冷男子,眼神几度复杂。看着周围一波波前赴后继而上的士兵们,他的眼中划过几丝不忍,这个战场本可以不存在的,但如今却因为他们几人的私欲让此地尸积如山,血流成河,这是他们的罪过。但既然选择了,便没有任何退缩的理由。
明亮的双眼几丝凌厉闪过,手中的长枪一转,策动战马,朝前方厮杀而去,手中的长枪不断的刺入那些国人的体内,虽不忍,但却毫无选择,手起手落之间,一条条生命在他手中流逝,鲜血染红了他白色的战袍,一道道的血腥味不断的在他鼻尖游荡,带着灼热气息的鲜血从那些年轻的士兵体内飞溅在他脸上,在微微的动容之后,他还是选择了继续持枪而继。
在南永阳所带领的三十万大军喷天的怒火以及超越生死的大不畏精神下,南俢禹麾下的那些士兵渐渐的心生胆怯了,他们在怀疑,在徘徊,在犹豫,他们此仗是与他们曾经的国家作对,他们这些小士兵,不知道那个备受他们尊敬的将军是否做过弑君之事。之前,他们一心一意的相信着他们的将军,可是,如今,南风皇帝驾崩的消息将那些隐埋在他们心底的丝丝怀疑勾欠出来,在对面军队散发着的势不可挡的气势下渐渐加强,终于,他们带着怀疑的目光看向了那个高高在上的指挥者。
感觉到身旁士兵的退缩,南俢禹愤怒的视线死死的定向对面那个白甲白袍的男子,他紧捏着手中的长剑,剑柄上繁复的花纹在他手上嘞出了一条条的印痕,但他却若毫无知觉般,双手依旧捏的死紧,指骨不断的泛着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