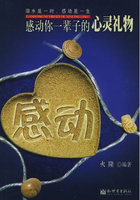我拉下曲洛的手,双臂圈住他脖颈,窝进他怀里。
“曲洛,我活着是不是个笑话。”
“不是。”
“那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我死。”笑死
“想杀你的人必须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听着像是哄人开心的爱语,神情也是一如既往的浅笑安然,只是他金曲洛早在心中起誓千百遍,字字肺腑,句句真心。他在这世上一日,便不会让她死。
“那你去把端木渊那厮给剁了。”我蹬鼻子上脸。
“啊?”
“把端木渊剁了。”
曲洛为难地看我一眼,凤眼轻挑:“吃完再剁行不。”
干笑两声,我就知道。推开曲洛,我赤足下榻,晃悠到阎王身边,研究他手上的冰晶银线,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有个结点。
“你看上端木渊了。”
“他很对我的胃口。”曲洛柔柔地看着自己的手指,笑比西子湖水柔媚。
“那你恐怕要多花些心思了,他很难吃。”
“我知道。”又不是用来吃
找到了,我寻到节点,轻轻一撮,原本紧紧缠绕着阎王手臂和扶手的银线猛地松散,随后规矩地落入我手中。阎王至始至终看着我的动作,可是我感觉他比较在乎耳朵里听见的对话。我转到阎王另一边,继续。
“债还完了?”我漫不经心地挑一眼阎王。
“阎王已死。”
“以后有什么打算。”手指一撮,收回另一套冰晶银线。
阎王活动着有些僵硬地手腕,低眉浅笑,这话又是什么意思,他上了一次当,可不会再上第二次。然而,阎王压根忘了,某人狡诈得根本是不按牌理出牌。
“阎王,我问你个问题,答对了,你就留下,答错了,你就去死。”
阎王抬眸看我,算是应下。
“他美还是我美?”
阎王顺着女子的视线看向软榻上的男子,脑中只有八个字,‘对了留下,错了去死’。
曲洛眼一眯,头一瞥,划一道八百里洞庭的浩渺,直接红牌罚我下场。
“他美。”
我斜看着阎王嘴角的笑,觉得这男人天生就是卖笑的,于是我很不给面子地把鬼域之王的下半生给定位了,给姐姐卖笑去。
“恭喜你,答对了。”
我勾起唇角,摘下发间的西域莲插在阎王发间。
入夜,百盏碧波琉璃灯燃起,将整个暮园笼罩在一层青纱中,如梦似幻。流水淙淙,莲色依依,俯看池中锦鲤都是无一例外的银白。半月皎皎,一袭白裘铺地,八盘糕点香味馥郁,一壶菩提血盛在白玉杯中,颜色醉人,白玉杯果然最配菩提血。
飞天不太正常,一个人坐屋顶上发呆。我知道她气我,气我连她都骗,还骗了三年不止。我知道她怨,怨自己几乎时刻跟在我身边,却还让我遭了那么多罪。我过半个时辰出去看她一眼,怕她想不开跳楼。
玉娘持着算盘噼里啪啦的算账,扶风坐一边思念她姐,曲洛去渊王府和端木渊谈合同,阎王很好学地研究我给他的《小倌之待客》,我懒散地趴在白裘地毯上,端一杯菩提血,想着两天以后怎么去死。
猛灌一口菩提血,我哀号:“我还是码不直。”
月娘瞪我一眼,扶风不解地眨眼,阎王素质一流地看着我笑。我本着就近原则一把揪住阎王的衣襟,走的是二爷的撒泼路线。
“我为什么要救他,我脑袋进水了卖自己的命去救他。我栽的树凭什么给别人乘凉,我种的花凭什么给别人摧了,我辛辛苦苦救活的男人凭什么和别的女人上床,我搭错了哪根神经怎么就非要去救他,五年前我就是被他那张脸骗了,长得好看有什么用,不是勾搭女人就是勾搭男人,他以为自己还是处啊,是个人都稀罕他,看了他就要往他身上扑,闲着无聊就要爱他爱得死去活来,掏心挖肺,至死方休,忙得发癫也要疼他疼得语无伦次,肝肠寸断,表里不一。他以为四海之内皆他妈啊,是个人就得惯着他。”
月娘傻了,扶风呆了,阎王斟了杯菩提血递给我,笑得如沐春风,可惜他那张脸和我一样不上不下,说难听点就是大众。我愤慨地仰头灌下整杯酒,也不管那杯子的价值直接潇洒地一扬手,一声脆响,一间半月阁碎了。
“众里寻他千百度,木然回首,那人却在别人床上做。他当他是转世如来普度众生那,都博爱到上他好兄弟的亲妹妹了,亏那姓莫的还笑的出来。我就是三十岁荷尔蒙失调,五年前被骗了一次还TM不知死活的往里跳,一次卖血二次卖命,再来一次,是不是要我卖魂啊!天下楼就是一大型欺诈团伙,姓落的就是一靠美色搞传销的,和着伙的骗财骗色,欺负的就是我们这种纯洁幼稚的富家小姐。”
月娘嘴角抽搐地不知道东南西北,扶风躲柱子后面,没见过白主子发飙地露半张脸瞅着。飞天从屋檐上倒挂下来,看了一眼,识趣地翻回去避难。
阎王好脾气地任我捏。
“说得很对,继续。”书里说的,顾客说什么都是对的。
我噌地站起来,一条腿架着栏杆,对着夜空狼嚎:“我装什么贞节烈妇,都没人给我立牌坊。制色种的那人就该去死,世道不好谁都知道,收了人家的钱你还以次充好,偷工减料,诅咒你十八辈子都做太监,不男不女永远站中间。是姐姐我歹命还是你端木泽命煞,偏偏姐姐喝的那口是盗版,怎么都着了道,就姐姐我放着一男人不去啃。我整一脑残,慕容傲那小王八蛋都就范了,我就该死趴着那座金山,至少还能捞个神兵山庄庄主夫人当当,然后败光他全部家产,让端木泽去哭吧……”
阎王难得不笑了,虽然她说得很快,但是至少有一点他听得清楚。这女人中了色种不假,可是似乎并未与男人交合,而且还活着,活生生地站他面前。
我低眉的瞬间扫过阎王那张若有所思的脸,一个气不顺地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想把他揪起来,无奈力量悬殊,我很牛顿定律地被他带趴下了,小脸很倒霉地撞上他胸膛。硬的,我的鼻子,MD我还不如趴地上。
姿势很暧昧,无奈气压太低。
一双白爪卡上阎王的脖子,使了劲地往里掐。月娘默哀地望着阎王,很爱莫能助地给了一个眼神‘小阎,来年姐姐一定给你多烧点黄纸,你就安心地去吧’。扶风全身一哆嗦,她想回天下楼了,她眼瞎了,跟错主子了。飞天看一眼局势,丢一对白眼过来,反正死不了。
我深吸一口气,掐着阎王地脖子卯足了劲地摇:“你怎么不笑了,没看见书上写着,客人怎么玩你都要陪笑吗!别说我现在掐你,就是我现在凌迟你,你也得给我亮着白牙笑。我已经够倒霉了,身边的男人TMD不是狼人就是娘人,你让我怎么吃,啊?我也希望自己无辜啊,至少还有权利哭那么两声,可我现在活着就没办法无辜。”
我踩着点地松手,阎王两眼一翻倒地上抽抽去了,我怀疑这小子有病,一身功夫都不知道还手,真当我民啊,就算我是民,我也是一乱民。
我整整衣裳,理理头发,趴回地上,姿势还是原来的姿势,手里握着的依旧是一杯菩提血。月娘手里的算盘开始运转,扶风蹭回了原来的位置,只有躺在地上喘气的阎王和几步外的一滩白玉碎片证实着刚刚某人大脑脱轨。
有人比我还会踩点地出现,身姿如柳款款而来,一袭淡紫衣衫,其上暗绣云烟缭绕,明绣仙宫琼宇,瑶池蟠桃,长长地拖尾勾勒的是天上人间,深蓝钻石如繁星嵌在其中。绫丝连接起百只玫瑰色玛瑙雕琢的蝴蝶,点缀在他青丝之中,自脑后拖至脚下。美人一笑,满池西域莲都成虚幻。
月娘两眼放光,扶风是绝对的臣服和崇拜,阎王,还是笑。我瞄眼曲洛,冷哼一声。
“谁惹我们家小白生气了。”
我抿一口菩提血,酝酿着下半场。
曲洛踩上白裘,优雅地曲身,双臂撑在我身体两边,将我压在他身下,我配合地转身仰躺在白裘上,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曲洛轻笑,眼底凛冽一闪而逝。
“白。”
离得最近的阎王将两人的表情看在眼里,不自觉地往外移了移,这两人瞬间将身边所有事物隔离,眼神交汇着只有他们二人才懂的信息,曲洛依旧完美如神,可他分明觉得这男人在生气。
“继续闹。”曲洛眉眼轻挑,撑在我身侧的一只手抬起探上我的命脉。
我挑回去,爪子恨不得撕扯那张脸,无奈理智告诉我,那张脸等于一张无上限性用卡。我退而求其次地去揪曲洛的耳朵,邪恶地想要转他七百二十度。
“这就是一笔赔本的买卖,我人生最大的败笔。我干嘛给他们机会,我就应该留天下楼白吃白住,白天在他们面前做人,晚上在他们床前装鬼,不把他们弄得精神分裂我就白活了两世。那俩死男人就是这么报恩的,一个在我面前搂着别的女人,一个一巴掌恨不得把我拍死,就TM一出杯具,特大号杯具。火起来,我把吴家所有产业卖了换成银锭子埋了他天下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