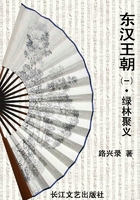“立功名兮,慰平生。”
罄冉耳听众人相和,剑势越发狂走,顿时便是飞沙漫天,慷慨豪情尽诉剑尖。
无人注意到,此刻燕奚痕和苏亮正站在众人之后也在默默望着这一幕。
燕奚痕目光炯炯望着被围在中央舞剑的罄冉,只觉那飒爽英姿便令空中明月都失了光彩。这个叫易青的男子,英挺俊秀,呼啸沙场,傲骨铮铮,敢在战场上抢他飞流,敢在他的面前发泄怒气,他欣赏赞许,却也不曾多加关注。
然而此刻,这个俊逸少年却生生如一阵风,吹入了他的心间。让他清晰地在心头刻印上了他的面容,他的姿态。那般强烈的震慑了他的心神。
燕奚痕愣愣望着那飞扬的面容,只觉男子的眉秀丽婉约,如远山青画;他的眸澄净剔透,似风中流云;舞动间身姿绰约,挥袂如仙。
昂扬的歌声,慑人的风采,在心中风起云涌,这般男子,当是男儿丈夫。可他为何,为何会觉得他如一朵怒放的玉兰花,高洁皎美,如一株秋霜白莲,淡雅出尘?
这身姿分明是坚韧卓拔,可他为何偏偏觉得舒卷中隐显媚丽?
眼见罄冉收剑而笑,燕奚痕的眼睛有一瞬间的慌乱,他能清晰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体内似有什么东西要破茧而出,多年来冷静无波的心湖,仿佛春风乍起,吹破层层涟漪。
“唱的好!唱的好!”
片刻静寂,场中爆发出如火的掌声。
苏亮亦跟着拍手大喝,燕奚痕却神色大变,复又面容一僵,猛然转身,脚步匆匆便往回走。
苏亮一愣,忙快步赶上:“王爷,您去哪儿?”
他追了几步眼见燕奚痕面容不对,也不做声搭理他,便不敢紧跟。脚步一顿,燕奚痕高大的身影已是消失在了营帐间。
苏亮思忖半响。如今刚打了胜仗,也没有什么军情。后续事情都吩咐下去了,连下一步的部署王爷刚才也都已经安排妥当。方才王爷不是还好好的,这到底是怎么了?
他茫然扭头,眼见一群人正围着易青笑闹,不免挑眉。难道王爷是嫉妒了?嫉妒易青抢了他的风头?不会吧……
燕奚痕大步回到主帐,只觉心头剧跳,面前不停晃动着那个从容舒展的身姿。
他大步走向长案倒了一杯水,咕咚咚的几口灌下。只觉天地沉沉浮浮,日月兜兜转转,而他的心起起伏伏,似有什么自其中炸开。
他甩甩头想将那个生动的面容自脑中扣除,可那张飞扬的面容却固执地不肯走掉,而且越发清晰了起来。
他只觉一阵慌乱,烦躁地在帐中来回踱了两步,复又站定,接着掠过挂在铜架上的长剑便大步挥开帐帘冲了出去。
翻身上马,飞流嘶鸣一声,便带着他如一道旋风飞驰出了军营,他驾马狂奔,不停挥鞭,身躯腾起在马鞍上,晚风自耳边掠过,脑中嗡然作响。
奔出十余里,只觉狂风吹得他眼睛生疼,他才勒马停了下来,眼见弦月移过半空,他翻身下马,目光渐渐平复了往日的幽深不测。
脑中恢复清明,他忖思道:绝对不会,自己绝对不会对男人动心!
在鹊歌城他分明便是见过那张面容的,在酒楼上便是那清冽如冰雪的目光和他对视毫不示弱。那张面容他记得清清楚楚,便是易青!
先前在战场上看到这易青他便怀疑了,怀疑“他”其实是个“她”,自己定是潜意识中已经将易青认定成了女子,才会这般……
对!自己怎么可能是断臂之人!
那么既然易青让自己这般失控,就该去证实!对!去证实!
证实那飞扬俊逸的人儿其实果真是个女子!
燕奚痕目光渐渐灼热,隐透坚定,他只觉自己此刻心中甜蜜中带着苦涩,欣喜中又带着焦虑!
他是个意志坚定的人,亦是个时刻保持清醒的人。从来都明白自己要什么,从来都是目标明确,勇往无畏。
这二十多年来,很少有过令他迷惑之事。尤其是这些年,领兵在外,一个错误的决断有可能断送的便是上万人的性命,所以他无时无刻不是冷静而自持的,也必须心坚如铁。
然而这次,他竟生出前所未有的茫然和无措,心头更是犹如有一匹惊马在四处乱撞。这样不行,他必须去弄清楚。
他今年已是二十有四,不是懵懂不知世事的小子,他自是知道心乱所谓何事。
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平生第一次动心,竟是在这样猝不及防的时刻,平生第一次心乱,竟是连对方的性别都没有弄明白。
燕奚痕唇有苦笑,本以为今生不会如小伙一般喜忧不禁,本以为已是过了血气方刚的年纪,却不想这一切只是来得晚了,只是尚未碰到令自己砰然而动的人儿而已。
他知道现在自己面临两个事实,一个是残酷的,也许会令他无法接受。而一个却是甜蜜的,会让他敞怀高歌。
这些年征战在外,皇兄不是没有为他赐婚的念头,相反已经逼婚多次。而他却都每每推据,一是自己常年在外,不想耽误人家姑娘的大好韶华。
而另一个他一直不好意思向皇兄启口的便是,他,燕奚痕,也在期许爱情。
他不愿娶一个陌生的女子为妻。他的妻子,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和他站在一起,他不要那些京城娇弱如花的闺秀,他的女人需得有霜花般的傲骨。
因为他是走在刀尖上的人,他的女人需得经受得住风霜,需得有不弱于自己的坚韧,那样才能令他心折,才能让他甘愿奉上自己的一颗滚烫之心。那样才能和他相互扶持,慰他征战怆苦。
而这些“她”都有啊!
既然心中怀疑,他便定要去证实,虽是心中惧怕,多年的坚毅也不容许他退缩。
燕奚痕猛然转身,翻身上马,目光灼灼,毅然望向前方,一声清喝,飞流如一道白浪劈破暗夜向军营方向驰骋而去。
而此刻的罄冉正和步兵营的兄弟们切磋着枪法,哪里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是怎样的试探。
翌日清晨,天晴,冬末的风已是带了稍许暖意,吹在脸上已不再那般刺面。
罄冉和往日一般天未亮便跟着步兵营的士兵们操练武艺,许是昨夜喝的酒过多过猛,她只觉头隐隐作痛。操兵之后正欲回寝帐拿水囊,却见苏亮带着一队燕云卫神情肃穆向这边走来。
罄冉眼见步兵营的兄弟们忙肃穆而待,撇撇嘴,心中颇有几分不以为然。
燕云卫乃是燕奚痕的近身亲卫,素来只听从其一人命令,身阶高于各营营长,也就是说随便一个燕云卫士兵都能指使一营之长。可罄冉总觉这些燕云卫太过自傲自大,目中无人。
她撇了眼苏亮,眼见他向这边走来,不觉一愣,顿住了正欲转身的脚步。
“易青以下犯上,于战时抢夺主帅战马,且不服上司命令,私自行事,军纪不明。王爷有令,绑其与中军营地,杖军棍四十,即刻执行。”苏亮肃目瞪向罄冉,说罢便冲身后燕云卫轻轻挥手。
罄冉一愣,还未待反应,已被燕云卫反剪双手,押着向中军营地走去。
身后步兵营的士兵们见罄冉被押走,顿时便个个面有不愤。但他们均知翼王治军甚严,只得暂且压下心中不满,纷纷商讨着要到中军大帐为罄冉说情。
罄冉被押着只觉一阵气闷,她大喝一声:“松手,我自己会走。”
挣脱两下,押着她的两个士兵竟将双手收的更紧。
罄冉正欲御气挣脱,却是苏亮笑着道:“放手吧,多有得罪。我等也是听令行事,易青兄弟可别介意啊。”
罄冉只觉他笑得有些奇怪,兀自蹙了下眉头便向中军大帐走去。她在帐前空地站定,见那里已经摆好了廷杖所用长凳,不免面容微沉。这四十军棍下去,且不说伤处上药是个麻烦,单是此刻便非得打得军衣破裂不可。那还了得?所以她说什么也不能让自己挨打!
燕奚痕负手而出,目光清冷站在营帐前上下打量着罄冉。见她面容沉冷,眉宇间显有愤怒,他心中有笑,面上却是一本正经,轻咳一声,冷声道。
“易青,你可知错?”
罄冉冷哼一声,挑眉瞪向燕奚痕,怒极反笑,道:“我不知错,我先前不知那是王爷的马,何来以下犯上之说?”
“哦?那现在呢?面有不平,不服管教,见到本王既不行礼,又语出狂悖,算不算是以下犯上?”燕奚痕大步走至罄冉身前,目光熠熠盯着她。
罄冉心下气恼,抬头看他,这才惊觉此人长身玉立,竟比自己高出许多。被他这么近距离冷静地审视着,罄冉只觉自己都能看到他瞳孔中那张愤怒的面容。
那双熠熠黑眸深处更似搅动着什么不知名的情绪,要将她吞噬而入。一股压力传来,罄冉心一惊,忙低头单膝利落行了个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