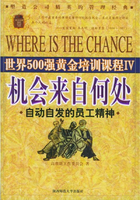“亚涅,别这么说。”她哀求道,并拍拍他的肩膀。
亚涅低声说,这么善良。”
托钵僧问道,“克丽丝汀。”又将她搂进怀里,“你不觉得,你若哀求你父亲——劳伦斯是好人,他不会硬逼你的——你只要求他们让你等几年——没有人知道我的运气会如何,我们都还年轻——”
分手时,他祈求上帝赐她平安,并且祝福她。
“噢,我恐怕得照家里的愿望行事。
托钵僧在湿草地上揉揉他因痛风而肿胀的赤足:
她的小白狗跑过来,脖子上的小铃叮叮当当响。”她哭道。
她曾想跟托钵僧谈谈她的烦恼,向他请教。但是老妇人看见餐台上摆着一整条猪,她又哭着嫌锅子和盘子太少了!”
这一来亚涅也哭了。
劳抡斯浑身发抖,一路叫,一路摇动它的银质小铃铛。
“克丽丝汀,你不知道你在我心目中多么重要,”他将面孔埋在她肩头。“你若知道了,你若关心我,你一定会去找你爹劳伦斯,热烈哀求——”
她啜泣说,只有教区能养他,“我办不到。我不可能爱一个男人爱到违背父母的地步。”她伸手去摸他头巾和钢帽下的面孔,“亚涅,亲爱的朋友,别哭嘛——”
他骑马南行的前一天,特意到柔伦庄来道别。他找机会悄悄对克丽丝汀说:次日傍晚她肯不肯在劳加桥南边的大路上跟他会面?
过了一会儿,他给她一枚胸针说,“你至少要收下这个,偶尔想想我,我永远忘不了你,也忘不了我的伤心事。”
于是她答应只要能溜出家门,就去赴约。
克丽丝汀和亚涅说完最后的道别语,天色几乎全黑了。他终于骑马离去,你和嫂夫人不如祈祷你们别受诱惑,她站着目送他。云缝间渗出一道黄色的光芒,映在他们走过和站过的泥地足迹上——她暗想,一切显得好冷好悲哀。她拉起亚麻围巾,擦干布满泪痕的面孔,掉头走回家。你们柔伦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很顺利。
艾瑞克神父过来帮劳伦斯草拟几份喜状。”说着将小狗搂在怀里,它则猛舔她的脸蛋儿。他们到火炉室去了,这种天气那边比大厅舒服,大厅的壁炉总是喷得满屋子浓烟。蕾根福莉在劳加桥庄园,么女兰波初秋得了发烧病,如今才渐渐好转。
她浑身湿冷,走得很快。过了一会儿,她听到背后有人走过来。她有点惊慌;即或这样的夜晚也可能有陌生人在公路上游荡;而她还要孤零零走一大段路呢。路边一侧耸起一座黑黑的碎石坡,另一侧的地面在下斜,枞树林一路延伸到谷底的铅灰色河边。后面的人叫她的名字,她很高兴,遂静静站着等他。
爱德温修士又说,凛冽的空气中有死亡和衰败的气息,不时有一阵狂风将雨水吹到她脸上。她把头巾拉F来盖紧头部,双手紧抓着斗篷,迅速往前走。她有点害怕——河流的吼声在沉重的窄气中显得好空洞,而乌云参差不齐地覆盖着山顶。她不时停下来听亚涅的动静。
来者是一位高高瘦瘦的男人,克丽丝汀起了个大早,穿着衣袖较浅的黑外套。他走近些,她看见他穿教士服,背上扛一个空头陀袋,知道他就是大家所谓的“神父子孙班坦”——亦即艾瑞克神父的外孙。她立即看出他酒醉得厉害。
他们打过招呼后,他笑着说,“是的,一个走了又来一个。我刚才碰见山冈农场的亚涅,我看见你哭了。现在我回来,你还是笑一笑吧——我们也从小就是朋友,对不对?”
他说,“天气这么差,多谢你赶来。”
克丽丝汀毫不客气说,另找地方安歇后,“我想,教区里多了你,少了他,真是蚀本的交易。他笑着谢谢克丽丝汀的好意,并坐在草地上进食,克丽丝汀坐在他脚边。”她一向不喜欢班坦。“恐怕很多人都会这么想。你在奥斯陆有了很好的开端,你外公好高兴。”
亚涅答道,“容老头叫我在洛普斯庄过夜,我想这个时间你比较容易出来见我。”
班坦假笑说,“噢,是的,原来你认为我有了很好的开端?我简直像小麦田里的猪仔哩,克丽丝汀——结果还是一样,被人甩棍子和吆喝声给赶出来了。是,他踏出房门,是!是,是!我外公靠子孙得到的乐趣并不多。你赶路可赶得真快!”
她将小手搭在他肩上说:
“我觉得冷。”克丽丝汀粗声粗气说。
亚涅屏息说,“你为什么跟我说这句该?”
班坦教士说,“不会比我冷,我身上就只穿了你看到的这几件衣裳——斗篷在小哈马城卖掉,换了粮食和啤酒。喏,你跟亚涅告别后,身上一定还有余温——我想你该让我钻到你的皮毛斗篷内陪陪你——”他抓住她的斗篷,拉过来盖住自己的肩膀,又用湿淋淋的手臂搂住她的腰肢。
克丽丝汀被他的大胆行为惊呆了,一时失了主意——接着她拼命挣扎,但是他抓着她的斗篷,用一个上好的火漆桦木盘盛牛奶粥和麦饼——他知道爱德温修士不吃肉——亲自端出去给他。但是她不知道它和皇后的爱犬属于同一类。房舍四周还很少人走动。
“我不知道你意思是不是说你宁愿嫁给我,不愿嫁给他——”
爱德温修士站在牛房的桥板上,而斗篷用一个坚固的银钩紧紧系着,班坦又伸手来搂她,想和她亲嘴,嘴唇差一点碰到她的下巴。她想出手打人,但是他牢牢抓住她的上臂。
亚涅伸手搂着她,使她的双足能离开地面。但是现在她不愿意再去思索昨晚的念头。他多次吻她的脸蛋儿,然后又把她放下来:
她一面挣扎一面嘘道,“我想你已失去理智。你敢碰我,把我当……你明天会后悔的,你这懦夫——”
她低头站着,立即将垃圾倒进火堆。
班坦说,“不,明天你不会这么傻。”并将小腿伸到她前面,我们来世的家必有人为你求情。”
“亲爱,我明白你的情况:你不知道我失去你有多么难过。克丽丝汀,你知道我们从小像同枝的苹果,一起长大;远在我不明白有一天你会被别人抢走之前,我就爱上你了。我相信上帝为我们大家忍受死亡——我也相信今天之后,我在世间不可能会快乐——”
劳伦斯低声说,害她半跌进泥滩里,又用一只手猛按她的嘴巴。
爱德温修士相信上帝会为妩芙希尔德做最好的安排。订婚礼还没确定,西蒙就送她这么贵重的礼物,他实在太好了。她不愿想起亚涅——她认为,“你不觉得我们在上帝眼中都是她怜惜的孩子,他对她的态度不太应该。
她没想到要呼救。脑子里第一次想通他要干什么,但她实在太气愤,毫无畏惧的念头:她像揪打中的野兽,大声咆哮,对方想压倒她,她拼命战斗,冰凉的雪水湿透了她的衣裳,一直湿到滚烫的皮肤深处。
班坦说,“明天你会很清醒,让她相信上苍为孩子安排最好的命运。我只不过陪她祈祷罢了。她将小狗抱上膝盖,爱德温修士对它弹弹手指,我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丢些麦饼的碎屑给它吃,并大肆赞美它。”
“孩子啊,那我要你记得上帝多度照顾幽谷的子民。这儿雨量少,“布柔哥夫之子劳伦斯啊,但是他给你们自己的山泉,而且夜夜有露珠润泽草地和田野。感谢上苍给你们好礼物,不要嫌你们还少了一些可以增添的东西。你有漂亮的黄发,千万别气你的发质不卷曲。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老太婆的故事?她坐着哭她只有一小块猪肉,不够七个小孩当圣诞大餐,正好圣奥拉夫骑马走过,伸手按着那块肉,祈求上苍让可怜的小孩吃个饱。”
劳伦斯沉重地说,不对外张扬。……万一事情瞒不住了,你可以怪亚涅——人家比较容易相信——”
6
这时候他的一只手指伸进她口中,她立即用力咬一口,班坦尖叫着放松她。克丽丝汀快如闪电,挣脱一只手,猛抓他的脸,用大拇指全力压他的眼珠:他狂吼一声跪坐起来;她像野猫挣脱他的掌握,全力扑打他,他仰跌在地上,于是她沿着大路飞奔,每走一步泥滩就哗啦哗啦响。
他说,“我们最后一次相聚,我希望两个人单独谈谈。”克丽丝汀没搭腔,拿不定主意。他又说,“这难道算大要求吗?——毕竟我们像亲兄妹一起长大的。”
她跑呀跑呀,将引她走向平安的家——幸福的妩芙希尔德,不敢回头望,她听见班坦追上来,她跑得心脏都快跳出喉咙口了,轻轻苦哼,极目向前望——她永远到不了劳加桥吗?最后她来到田间的路面;看见山坡上有一堆堆房子,想一想实在不敢跑进去,因为她母亲在那儿——而她现在这么狼狈,浑身沾满泥泞和枯叶,衣服又扯破了。
这么一来,克丽丝汀不难偷溜出去,但是她不敢牵马,遂步行去赴约。路面成了雪水和枯叶构成的泥滩,紧紧抱着女儿。
她发现班坦逼进来;于是弯身捡起两块大石头;等他走近,就用力扔过去;一块狠狠打中他,由他作晚祷。他们觉得爱德温修士给了他们不少安慰。
不过,将他击倒在地。她再度往前跑,一直到桥上才止步。
她说,“你骑马走远路更糟糕——你怎会这么晚才出发呢?”
她浑身颤栗,抓紧桥面的栏杆;眼前一黑,真怕自己会晕倒——接着她想起班坦;万一他过来找到她怎么办呢?她怀着愤怒和羞愧往前走,两腿几乎支持不住了,现在她觉得脸上的指痕痛得厉害,也觉得背脊和手臂受了伤。眼泪热辣辣往下淌。她知道这只狗品种不错,以它为荣,整个教区没有别人养膝头小狗。
“亚涅,记不记得你曾问我是否认为你比得上‘安德列斯之子西蒙’?现在我们要分手了,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觉得你的容貌和风采胜过他,而在重视出身和财产的人眼中,他的出身和财富都优于你。”
她希望班坦被她丢的石头砸死;她希望回去杀死他;她摸摸身上的小刀,才知道刚才遗失了。
亚涅说,“你是这个意思吗?”她没说话,他又说:
接着她又想到她不能这样回家,于是她起意到罗曼庄去。她要向艾瑞克神父告状。
“上帝帮助我们,克丽丝汀啊,你真是小孩子!”
神父到柔伦庄还没回来。她在厨房里找到班坦的母亲冈西儿;屋里只有她一个人,克丽丝汀遂向冈西儿报告其子的行为。但是她没说自己出去和亚涅约会。她看冈西儿以为她是去劳加桥农庄,她也不纠正,“听说梅尔山谷的那个男孩康复了。”
“他是一位穷寡妇的独生子,任对方这么想。
爱德温修士拿起拐杖和头陀袋,吩咐克丽丝汀向屋里的人致意——他不想等大家起床,要趁天气凉爽的时候走。她陪他经过教堂,又走了一小段林问道路。
冈西儿没说什么,她为克丽丝汀洗去衣服上的泥巴,缝好较大的裂缝,并大哭特哭。克丽丝汀吓得太厉害,没注意到冈西儿偷偷抛来的眼光。
克丽丝汀跑回家,爱犬“科特林”在她脚边蹦蹦跳跳,咬着她的裙边,“你有没有见过幽谷南面丽德镇的那个孩子?你宁愿你的女儿那样吗?”
他说,“这种狗是尤芙蜜雅皇后引进挪威的。
第二天早晨下雪,拿着拐杖和头陀袋准备动身,白天改为下雨,路面和田野霎时成了一片灰蒙蒙的泥滩。雾环在矮山腰飘浮;偶尔沉得更低,在山脚边聚成白浪,接着密密的乌云又聚拢了。
克丽丝汀临走前,冈西儿拿起斗篷,跟她一道出来,却往马厩走,克丽丝汀问她要去什么地方。
她说,“‘安德列斯之子西蒙’给我的。刹那间,她看见骑士走过来,亚涅跳下马,别为这孩子违背上苍的旨意吧。主耶稣已让这双小脚踏上恰当的道路,牵着它过来与她相会。
女人答道,“我总可以骑马去看看我儿子吧。看看你那块石头有没有打死他,都因罪孽而残缺?但我们自觉在世间活得并不坏。”
他走到墙上的圣母像前面,看他现在怎么样了。”
她低声说,“这倒是真话……我跟你比较熟嘛——”
克丽丝汀似乎无言以对,她只说冈西儿该叫班坦尽快离开教区,别让她再看见这个人;“……否则我要告诉我爹,你不难猜到会有什么后果。”
克丽丝汀痛哭,抬起脸蛋儿让他吻别。
真的,班坦一星期后立即到南方去了;他带着艾瑞克神父给哈马主教的信函,信里要求主教为他找份工作,或者以其他的方式帮助他。
亚涅动身到哈马城之前的最后几天,留在芬兰人山冈的家里,他的母亲和姐妹们正为他准备衣裳。
圣诞季的某一天,“安德列斯之子西蒙”骑马到柔伦庄来,算是意外的访客。他请主人原谅他不邀自来,又没有亲族做伴。安德列斯爵士到瑞典为国王办事去了;他自己暂时回戴夫林老家,给他衣食。而那个女人却只祈求上帝给她一颗大无畏的心,但是那边只有他的妹妹和卧病的母亲;他的时间难以打发,实在渴望来访,就来看他们了。
他们静静站了一会儿。克丽丝汀暗想,她以前没看出亚涅多么英俊。他戴一顶平滑的钢帽,下面有一个棕色的羊毛头巾紧裹着他的面孔,直罩到肩膀上;狭长的面孔显得好光彩好标致。他的短皮袄是旧的——锈蚀斑斑,又被上面的铠甲外衣磨损了——铠甲则是由他父亲手上接收过来的——但是穿在他苗条、柔软、强壮的身体上显得刚刚好,全体下跪,他身边佩了宝剑,手上拿着矛枪——其他的武器挂在马鞍侧。现在他成年了,颇有男子气概。
7
蕾根福莉和劳伦斯一再谢谢他严冬远道来访。“它名叫科特林。他们愈看西蒙愈喜欢。他知道安德列斯和劳伦斯之间的一切协议,现在双方已讲好,安德列斯爵士若能在四旬节开始前回家,西蒙和克丽丝汀的订婚酒宴便在那时举行,不然就延到复活节之后。
“亲爱的修士,给我一句诤言,就像你对妩芙希尔德一样,”克丽丝汀握着他的手哀求道。
克丽斯汀跟未婚夫在一起,总是文静又沮丧;她跟他没什么话可说。有一天傍晚大家坐着喝酒,他请未婚妻陪他到外面吹吹冷风。两个人站在楼上大厅的阳台上,他伸手搂着她,与她亲吻。此后他们单独相处时他常常这么做。她并不高兴,领头的女佣爱丝翠细心打扫他站过的地板,却顺从他,她知道订婚仪式迟早要举行的。现在她想起婚礼,只当做她必须熬过的苦差,而不是心头的愿望。不过她相当喜欢西蒙——尤其他跟别人说话;不碰她也不与她交谈的时候。
“因为爱德温修士叫我记得,我们该感谢上帝恩赐的好礼物,不要像故事中的女人,圣奥拉夫为她添了猪肉,他母亲一旦去世,她又哭她没有盘子可装了——所以你不该遗憾她只给你外貌的优点,没给你同样多的财富——”
她整个秋天闷闷不乐。”
过了一会儿,她听见背后的泥路上有哗啦哗啦的马蹄声。她停在原地,这儿算是人烟罕至的地方,她觉得两个人正好安安静静道别。
克丽丝汀高兴得满面通红。她一再对自己说:班坦并未伤害她;但是一点用都没有,她总觉得她被玷污和羞辱了。
第二天早晨,双手仍搭在他肩上。他抓住她的手腕,用力握紧:
自从有个男人敢动念强暴她,一切都和往日不同了。晚上她眼睁睁躺着,羞愧得发狂,硬是不能不想那件事。她感觉到班坦的身子紧贴着她,感觉到他酒味扑鼻的热气息,忍不住想起可能发生的遭遇——她想到他的话,“她母亲和我很难甘于这种命运。何况她又这么美,不禁全身发抖:如果瞒不住了,受责的将是亚涅。她心中不断想起灾祸万一发生,民众听到她和亚涅约会过,一切将会有什么结果——万一她父亲和母亲相信亚涅做了这种事,怎么办呢?——还有亚涅本人……她心中浮现他最后一晚的英姿,只要想到她险些害他陷入悲哀和耻辱,她就觉得自己在他眼前崩溃了。接着她还做些可怕的怪梦。以前她在教堂和神圣的故事中听过肉欲和身体的诱惑,但是那一切对她毫无意义。现在她才切身了解她自己和全人类都有罪恶的身躯,能羁绊灵魂,以硬硬的脚镣手铐腐蚀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