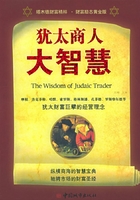挺着大肚子的二妈咂出第一口酒,这已成为规矩:土司家每年的苏里玛酒都由二妈亲手酿制,第一口酒当然也要由她来咂。金黄的酒液从弯弯的山竹管里流出,接下来的第一杯酒敬到神龛上,兰波念出土司家每一代祖先的名字,请他们回家团圆共度佳节;第二杯酒献给锅庄神,说了许多辞旧迎新的祝辞,为土司一家祈福祷告;第三杯酒端给爷爷,爷爷喝了一口缓缓咽下,品尝良久,然后干了下去,当即拿出一对早已准备好的银镯子递给奶奶,奶奶做主把镯子赏给了二妈,父亲代为谢过。大家正在看着二妈受赏的时候,卦祖老爷爷正悄悄地往自己的酒壶里灌酒,贼兮兮笑眯眯的样子煞是可爱。每年三十的这坛酒,精选了当年收成的青稞、稻子、大麦、荞麦、小麦、稗子、玉米等十几种粮食,分别在不同的时候用大锅煮熟、烘干,直到底层冒出锅巴的煳味儿,才用簸箕盛出冷却,上山采摘各种野花和药材制成酒曲,均匀地混合在煮熟的粮食里,装入篾制的箩筐发酵。每种粮食的发酵期不一样,所以烘煮的顺序和时间也不一样,这是一个劳神费力的过程。待各种粮食散发出自己不同程度的酒香时,才将它们混合装入坛内,用黄色的黏土和着牛屎做成密闭的坛盖储存在干燥阴凉的地方。年三十这天祭祀完毕,将开启后剩余的酒液咂到酒壶里,再把凉白开灌入原来的酒坛,大年初一大家就可以喝到口味稍淡却风味正佳的苏里玛酒了。第一咂酒酒香浓郁,酒精度高,容易醉人;第二咂酒就温和了许多,老少咸宜,爽味可口,这是摩梭人待客过节的必备良品。卦祖老爷爷每年都会到土司府里馋这第一咂酒,而且总是乐此不疲,一大清早就帮着大家干这干那,只为开坛的时候可以蹭上一口美酒,因为这样珍贵的佳酿,不是每一个摩梭家庭都有得起的,土司家也都只酿一坛。现在卦祖老爷爷如愿以偿,便悄无声息地抱着酒壶溜了出去。兰波达巴主持完仪式,爷爷赏了他们二两银子、两圈猪膘、两条腊肉、两瓶白酒、两袋粮食和一些糖果,算是打发给他们过年的礼物。
鞭炮声响起,厨娘们开始来回上菜。正房里的两桌坐着土司的家眷和家臣,厨房里的两桌围着厨娘和家丁,轮流值班的卫队都回自己家吃饭。大妈主持我们这桌,大哥和二哥都在爷爷那桌,奶奶一个人自成一席,我便成了我们这桌唯一的男子汉。大妈依旧用她惯有的作风,使得饭桌上热闹非凡。爷爷说过年不必讲究那么多礼节,更何况在座的都是亲人,大家不必拘束。坐在我们这桌的都是女眷,大家小声说话,可笑起来的时候,却仍然引得爷爷那桌频频转头探望。虽然很快乐,我却更羡慕大哥和二哥,他们像男子汉一样坐在爷爷那边,举止优雅,言谈潇洒,着实令人向往。我很快吃完饭,从扎嬷怀里挣脱,跑到爷爷怀里,他将我抱起。
“阿普的小乖孙吃饱了吗?”爷爷笑着问道。
我摸了摸肚子,确认似的点点头。摩梭人有这样的说法,年夜饭要过了三碗才能泡汤,否则来年出门的时候会被雨淋。吃饭的时候也必须吃饱,因为家神会在晚上降临,抚摸我们每一个人的肚子,看他有没有吃饱。如果没有吃饱,家神就会想:“全家人都吃饱了,为什么你没有吃饱呢?”家神就会生气,来年便没有好运。陈师爷看见我摸着自己胀鼓鼓的肚子,满脸通红地问我:“味道如何啊?小阿龙佐!”他用手逗逗我的脸蛋儿,我回答说:“如火,如火!”大家轰然起笑,爷爷更是高兴,师爷赞道:“小少爷聪明伶俐,卓尔不凡,是个可塑的人才。”爷爷说:“师爷过奖了,这孩子只是与众不同,惹人喜爱而已。”这时,父亲在一旁对我说:“下去吧,不要打扰阿普吃饭。”说着就要让扎嬷抱走我。爷爷的脸色有些难看,可是扎嬷已经过来。我嚷嚷道:“我要给阿普端酒嘛,我要给阿普端酒!”爷爷听了,脸上的笑容再度盛开。扎嬷一只手抱着我,一只手托着碗底,我抓着碗壁把酒碗送到爷爷跟前,爷爷伸过手拿住酒碗,扎嬷便放开托着碗底的手抱住我,我倾着身子让爷爷把碗里的酒喝完。师爷赞道:“好!好!孺子可教也!”自己也端着酒碗喝了一杯。
刘教头给大哥使了个眼色,哥哥便从座上站起,举着酒碗对爷爷说:“阿普,孙儿祝您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师爷听了大哥的话,觉得不对,他是个书呆子,觉得这样的话应该在寿宴上说,而不是团年饭上,便纠正道:“今昔是春节,何来贺寿之理啊?”
爷爷一听,觉得有理,便将端起的酒碗放了下去。大哥一着急脸就红了,他的老师刘教头笑道:“师爷怕是喝多了,脑袋怎生这么固执?贺寿是汉族人家的规矩,我们摩梭人从不过生日,贺贺寿敬敬孝心又何妨?”
师爷听了点点头,觉得有道理,端着酒碗摇着脑袋说:“那就祝老爷岁岁相增得益寿,锦上添花步步高!”
爷爷端起酒来,刘教头又笑了:“师爷喝多了,明明是大少爷尽孝在前,你尽忠在后,怎么不等老爷把尽孝的酒喝完了你再尽忠?”这两句话顶得师爷受不住气,脸色一下子铁青。坐在一旁的父亲起来调解道:“两位老师何必争执?为子者尽孝,为臣者尽忠,大家共同来敬阿大一杯,岂不更好?”听了父亲的提议,所有人就都站了起来一同向爷爷敬酒。
土司家的四大摩梭头人伍、汪、马、刘每年都在土司府里吃团年饭,今年也不例外。刘氏头人掌管着山价住牧洼里,平日与汉族多有交际,消息最为灵通,是土司家的千里眼顺风耳;伍氏头人掌管着瓜别以北、以西的大部分地区,是头人里土地最宽实力最强的,每年上贡的东西也最多;汪氏头人掌管着瓜别以南的全部地区,以畜牧和山货贸易闻名九所,经常往来于各所土司之间;马氏头人掌管着最少数的百姓和最小量的土地,却拥有瓜别最富有的人家和最肥沃的土地,光是瓜别大街上的地租就足以令其余的头人眼馋。
大家酒足饭饱之后,刘氏头人对老土司说:“老爷,这年头外面可不清净啊,汉人刚闹完‘长毛’现在又闹起‘革命’来了。”说到“长毛”,刘教头极不乐意地瞧了一眼刘氏头人,这两个字似乎让他很不高兴。
爷爷说:“管他革不革的,你只要守住洼里就行。”
刘氏头人唯唯诺诺地点点头,但又不安地补充道:“眼下也有一些汉人不安分,所以我想……”
爷爷打断他的谈话,说道:“不用你想,你好好守住就行。你的汉人最多,与外界的交流也最广,那些不该你管的事,不该你想的事,你就不要去过问,不要去想,自有朝廷为你分忧。”爷爷的目光突然转移到他的儿子身上,父亲便接过话茬:“土司的职责就是世守自己的土地,不要有非分之想。”听完土司父子的话,刘氏头人点点头,不再说话了。
汪氏头人说自己想去看看女儿,他的女儿就是土司家的二太太,下午他就要回去,他说:“孩子的母亲想她的女儿了。”爷爷说:“去吧,你也快抱外孙了,初五去给亲家拜年。”爷爷说完话,又看看他的儿子。父亲便说:“会的,我带着斯达来,她现在行动不方便,就不用过去了。”斯达是二哥的摩梭名。汪氏头人给老土司敬了酒磕了头这才出去,二哥和父亲起身送他。
“最近,”伍氏头说,“从冕宁营过来的倮倮越来越多,是不是该……阻止一下?”
刘教头说:“你的一个营已经训练得差不多了,可以随时征调。”
伍氏头人看看老土司,老土司没有说话,大家就都安静下来。但是,师爷却表态了:“如此蛮夷皆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人,老爷何不安抚之,给予一定的土地,划个范围,圈养起来,无再滋事,上贡纳粮便可,谁不想有个安稳的家园好好过日子。”
大家一起看着老土司,老土司还不说话,大家又都安静下来,这时他的儿子送完岳父回来,爷爷便说:“把你们刚才的话重复一遍,重复给土司听听。”父亲一听,觉得话中有话,赶紧跪在地上,说道:“阿大还在,瓜别就没有第二个土司,儿子一切听从阿大的调遣。”
爷爷起身,所有人就都站了起来。爷爷扶起跪在地上的儿子,让他坐下。父亲不敢,坐下去又站了起来。爷爷再压他的肩膀,示意大伙儿一起坐下。大伙儿坐下了,爷爷才说:“看来,你们把我当成我的父亲了。没错,我父亲在位五十年,使瓜别成为九所之冠,众所瞩目。他的所作所为成为大家争相效仿的对象,谈到瓜别的人无不说到他老人家的丰功伟绩、辉煌故事。可是时代不一样了,过去的就让他过去,谁也阻挡不住历史的洪流。他老人家同治三年辞官退隐,我是嫡长子,继承土司之职,两年后他就仙逝了。那时我还什么都不懂,凡事皆过问于他,总以为他会长命百岁,永远在我的身边,可是……”爷爷讲到伤心之处,停了一下,喝口酒,又继续说道,“可是不可能,等我真正管事了,才知道担子不好担。所有的人都看着你,盯着你,你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哪怕一句无关紧要的话都会成为你跟老土司对比的对象,真是步步惊心,如履薄冰,好在大家同心协力,才有了我们今天这点成就。我不敢拿自己跟他老人家对比,这么多年我只算是守住了他的家业。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朝廷的江山风雨飘摇,所有人都自顾不暇,动乱不安的时代已经来临。好在土司家十几代人打下的基业还算稳固,只要我们能守住瓜别,不妄自尊大,坚守好自己的土地,安安分分为人臣子,这里就永远还是摩梭人的天下。”
爷爷说完,刘教头马上接道:“可是老爷,现在匪患四起,倮倮到处烧杀抢掠,为所欲为,百姓妻离子散,苦不堪言,真是惨不忍睹,老爷身为一方之主,又岂能坐视不管?”
伍氏头人等不及了,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你们地处腹地,不知道我那里的境况,自道光末年司匹国富允许倮倮入境,之后老爷又大量招收彝佃,瓜别的彝族人就渐渐多了起来,他们主要聚居的地方全在我的辖地上。今天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明天又是你打他,他打我,每天每夜的冤家打不完,一两句话不对头就有可能引起一场冤家械斗,一路上烧杀淫掠,所过之处鸡犬不宁,四境了无人迹,奴役的奴役,变卖的变卖,就连还未成熟的庄稼也都被一一践踏,实在是魔鬼所为令人发指。”
爷爷并不言语,看看自己的儿子,父亲便说:“一切听从阿大做主。”爷爷说:“你现在是土司,大家都想听听你的意见。”大家望着土司,都想听他说些什么;可土司也望着大家,就这样僵持着。时间过了很久,伍氏头人突然给爷爷跪下:“只要老爷把您的骑兵营借给我,配合我的步兵,不等正月吃元宵我就能将所有倮倮全部驱逐出境,大不了这个年我不过了。”
这时,沉默了好半天的师爷起来说道:“夫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我认为……”
刘教头在座位上站了起来打断道:“师爷还是省省心吧,读书人的那些所谓之乎者也的大道理对付这些倮倮可是对症不对药,唯一的办法就是下猛剂,多喂点‘刀口药’,他们就肯老实了。”
师爷的脸色气得铁青,他颤颤巍巍地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大兵之后,必有灾年。一旦用武,瓜别罕来之安定必将毁于一旦,切不可轻举妄动。”
刘教头还想力争,却被爷爷打断道:“你呢?”大家这才发现,坐在最远处的马氏头人一直没有说话,老土司想听听他的意见。
马氏头人笑着喝了口酒,说:“我随便,怎么都行!有土地我就种粮食,有草场我就牧牛羊,有河流我就抓鱼吃,实在不行我就烤着黄太阳睡个大懒觉!”
伍氏头人听了,最气不过,数落道:“那么人家欺负到你头上呢?”
马氏头人便说:“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打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打!”
伍氏头人又说:“人家把你干掉了呢?”
马氏头人说:“那就掐着他的喉咙,把他噎死。”
马氏头人这番话把大伙儿逗乐了,一场严肃的论辩悄然熄火,又都喝起酒来。大哥一直没有机会说话,老早就想出去,趁着大家不注意,更想往外溜。他的心思被爷爷看得一清二楚,就在他的屁股将要离座时,爷爷望着他问道:“你呢?”
“我……”
大哥不说话,埋头坐了下去,他哪里懂得粮食、土地、鱼和太阳。他只知道刘教头说冲出去,他就带领大伙儿号叫着一窝蜂冲出去;刘教头说冲下来,他就带领大伙儿呐喊着疯狂地冲下来;刘教头教给他各种冲锋的队形,他便完完整整地去实施刘教头的战术,这就是我的大哥和土司家的骑兵队每天都要重复多遍的事情。可尽管如此大家还是乐此不疲,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各种不同的地方,以各样不同的方式,兴致勃勃地冲了又冲,冲了又冲。现在老土司问他对于自己将来要管理的这片土地的看法时,他很茫然。父亲让他跟着刘教头他便跟着刘教头,刘教头叫他冲向哪里他就带领着大家冲向哪里,除此而外的事情他几乎没有想过。
父亲见大哥不说话保持沉默,便对爷爷说:“孩子还小,哪里懂得这些?”又对大哥挥挥手,示意他出去。大哥如释重负,马上恢复生气,很快地溜走了。
爷爷的脸上布满阴云,刘教头过来敬酒:“镇藩还是很争气的,跟同龄的孩子相比已经是出类拔萃,九所里无人能及,老爷……”
“不用说了,我懂你的意思,我并没有要苛责他。”爷爷打断刘教头的话,可他心里还是不畅快,“对你,我是很放心的,既然你也认为他是个好苗子,以后多花点心思,好好教导他、培养他,让他成为有用之才。现在的世道是越来越乱了,我们必须做好各种准备,我代表土司家族谢谢你们祖孙二人。”爷爷端起酒碗回敬刘教头,父亲也站了起来,说道:“多谢了!”
饭已吃得差不多,头人们便各自回家了。老土司打发了他们丰厚的礼品,他们带着自己的随从高高兴兴地赶着跑马上路。你肯定会问,他们的随从怎么没在土司府里团年,这是因为他们全都散到百姓家中去了。摩梭人有这样的规矩,逢年过节,不管来到家里的人认不认识,只要进了门槛,就是自己家尊贵的客人,会受到热情的款待,还会以此为荣。渐渐地,许多人家在长期相处的过程中结成了亲家。他们才不稀罕上土司家团年呢,要是喝醉了酒摔坏了碗,那是谁都得罪不起的。竟至于后来形成了一个规矩,只要是自己的头人要去土司家过年,便个个都找借口开溜,不是脑袋疼,就是肚子痛,反正每一回都换一个不同的地方,找一个不同的理由跑到邻近的百姓家去。当然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使他们更愿意和百姓相处,和百姓交朋友,快乐时可以与共,幸福时可以比肩,苦难时可以相扶,贫困时可以相依,却不像土司家高高在上,无论如何都攀附不起。儿女亲家是他们之间最为常见的关系,除此之外他们还有经济上的往来。每年夏天,矮山气候湿热,牲畜容易生病,矮山的牧民便把牛羊赶到高山交给高山的住户代为牧养,新产的牛羊两家平分;冬天的高山干燥寒冷,牛羊受饥挨冻,高山牧民便把牲口赶到矮山交给矮山的住户代为照看,新增的牛羊同样是两家平分。高山上盛产洋芋、苦荞和圆根萝卜,矮山适宜种水稻、玉米和蔬果。高山以畜牧牲口为主,矮山以粮食生产为主,他们经常驮着酥油、山货、药材下来换取粮食、盐巴和茶叶,大家彼此交换生活之所需,建立起一个复杂的关系网,只为了能够更好地生存下去。
头人们一走,刘教头就回家了,他的家里还有一个比他年轻的老婆和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陈师爷却不想回去,家里除了他自己就剩他自己,孤家寡人一个,他每年都在土司府里和大家一起守岁。不过最近几年,他经常去“通衢之家”酒楼,和那里的汉人一起过年。本来以前陈刘二人很是要好,同住在土司府里,几乎形影不离;后来由于生活差异,政见不合,最终分道扬镳,近乎形同陌路。可是说起这两个汉人的来历却都颇有渊源,那得从我曾祖父的往事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