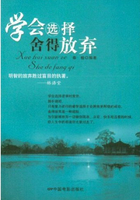“啊!”罗友杰吓得抱头蹲下,就连管家也吓得钻到了桌子底下,生怕这枪走火。半天没听见枪响,只听见“咔咔”的声音,他抬头一看,朱筱凤扣着扳机,可怎么也扣不下来,罗友杰起身,弹了弹身上的灰尘。“我劝你还是放下枪,这女人拿枪,可就不好看了……”
这一刺激,朱筱凤死命地拿食指板着扳机,可这枪就像和她作对似的,一点作用都没有,看着罗友杰的丑恶嘴脸,朱筱凤的脑海中忽然闪过当年蔡松坡教她使枪的景象,在罗友杰猖狂的笑声中,她牙一咬,一把捏住枪托,闭上眼睛,顺着模糊的记忆,扣下扳机……
“砰”的一声!枪声响起了,脖子上的刺痛,让罗友杰吓得瞠目结舌,这女人真开枪了?摸了摸刺痛的脖子,手上竟然是血。
“你你你……”没料到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竟敢开枪,罗友杰顿时被吓得魂飞天外,脸刷地一下就白了,腿也跟着软了下来,一只手扶着受伤的脖子,一只手胡乱地挥舞着,语气也不若刚刚那么嚣张,上牙打着下牙,结结巴巴地看着朱筱凤。“放放放……下……枪,否则……”
“砰”的又是一声枪响。“你这个狗汉奸。”随着朱筱凤疯狂的喊叫声,她像是发了狂似的,猛朝罗友杰继续开枪,可惜没打准,罗友杰顿时像个过街老鼠似的,四处逃窜。
枪膛里的子弹用尽了,她也用尽了最后一丝勇气,眼前一黑,昏倒在地,没有了知觉……
等她醒来,已经在一个破旧的茅草屋里,她想挣扎着起身,躺在椅子上打盹的耿副官也惊醒了。
“嫂子,你受了风寒,别急着起来。”
清醒的朱筱凤想起了自己为什么昏倒,她一把抓住耿副官的衣服就问:“玉魁呢?在哪儿,带我去见他。”
耿副官见状,眼睛也红了,强忍着悲痛。“嫂子,你已经昏迷了两天,大哥的尸首……我没能找到。”
“我要去找他。”朱筱凤一听,掀开被子就要起身。
“嫂子,你别固执了。”耿副官一把按住她。“我好不容易通过关系,几乎把钱都花光了,才从大牢里把你冒险救出来,你这一去,要是你有三长两短,你让我死后怎么有脸去见大哥。”两天前,朱筱凤拿着枪去逼罗友杰放人,可惜的是,王玉魁竟然不堪忍受折磨,在大牢里撞墙自尽了。朱筱凤得知丈夫惨死的消息,发了疯似的开枪,硬是打中了罗友杰,可惜没把他打死,罗友杰恼羞成怒,将昏厥的朱筱凤关进大牢,他捏着手上仅剩的银票,通过以前军营里的关系,才把在牢里发着高烧的朱筱凤带了回来。
被耿副官一吼,朱筱凤头脑清醒了大半,渐渐地,她不吵了,双手捂住脸嘤嘤哭泣,先是低声哭泣,到最后变成了嚎啕大哭。
等她哭够了,耿副官递给她一张车票。“大嫂,我是偷偷把你救出来的,现在这奉天城如临大敌,到处追捕你,你拿着这张南下的票,还有这些东西。”耿副官知道她珍惜那个盒子,走的时候没忘记给她拿,盒子里有几张银票和一些首饰。“你放心,你走了,我继续去找大哥的尸首。”
“我不走……”
“大嫂,大哥如果活着,也不希望你为了他出事。”
“那你老婆和孩子呢?”
耿副官笑了笑安慰道:“你放心,她们早就回了娘家,你一走,我就无后顾之忧了。”
可惜,天不遂人愿,天色刚刚擦黑,宪兵就追到了这里,情急之下,耿副官将朱筱凤从后门送出,她来不及细想,抱着包袱就拼命朝丛林中跑去,跑着跑着,她听到了远处的枪声,她知道耿副官为了救她被杀害了……可她来不及伤心,只能拼命往前跑,才不能辜负耿副官救他的心意。
整个奉天城贴满了捉拿朱筱凤的通缉令,朱筱凤只有乔装打扮,出城的时候,朱筱凤用头巾遮住了脸,可发现守在城门口的士兵不仅要一个个对照通缉令,还要搜查包袱里的东西。一路上还能听到人们的议论纷纷。
“哎,听说了吗?”
“怎么?”
“咱们奉天城出了一个抗日救国的女英雄。”
“谁呀?”
“王师长的四夫人。”有人压低了声音。“一个妇人拿枪大闹罗府,指着罗友杰大骂汉奸、走狗……”
“别乱说话。”一个女声打断了这些人的议论。
她抬眼看着不远处挂在城门墙壁上的通缉画像,那通缉令上的画像还不一定能认出她,可包里的照片和信件,如果被发现,一旦被士兵破坏了,她可真就一无所有了,她紧紧地护住放在口袋里的东西,脑海中思索着怎么躲过搜查,忽然,路边一堆黑乎乎的东西吸引住了她……
随着临近搜查,前边的几个人开始不安分起来。
“咦?什么味儿?”
“是不是那两箩筐腌肉坏了?”挑着箩筐的男人放下,掀起布闻了闻。“不可能,你闻闻。”
“不是这味儿。”女人摇了摇头。
经这么一说,后面排队的几人也捂住了鼻子。其中一个站在朱筱凤身后,约莫四十多岁的妇女找到了臭味的源头。“大妹子,你这身上怎么那么臭啊?”
朱筱凤一听,急忙把头巾严严实实又遮住,只露出两个眼睛,惊恐地说:“大姐,我……我得了传染病,被婆家赶了出来,想……想……”
“什么?”那妇人一听,急忙推开了。
朱筱凤抚着额头,呜呜地哭了起来。“就是没钱医治,我家丈夫被我传染之后得病死了,我也不知道上哪儿……”
她话还没说完,四周的人全吓得作鸟兽散。
前面搜查的士兵一听,眼看朱筱凤就要走过来接受搜查,立即捂着鼻子,另一只手指着她吼道:“你别过来了。”
“长官,您不搜查……”
“滚滚滚……”士兵满脸嫌恶地摆着手让她滚,于是,朱筱凤片刻不敢停留,也就顺利离开了奉天城。
深夜,乔装打扮后的她踏上了开往南下的火车,火车没开多久,宪兵就上车搜查了,宪兵拿着一张通缉犯的画像,到处搜人,虽然她把自己裹得犹如一个村妇,可还是有个宪兵认出了她,情急之下,她将放在桌上的水壶砸向宪兵,转身就跑……
后面是宪兵鬼叫的声音,跑着跑着,她来到了车厢的尽头,轰隆隆……轰隆隆,耳边是火车的奔跑声,双手紧紧捏着车厢两侧的门框,眼看宪兵就要从另一节车厢追赶过来,她一只手下意识地护住怀揣在怀里的盒子,眼睛一闭,纵声跳下火车,待宪兵追赶过来,已不见了她的踪影。
一片广阔的草原上,一个头发凌乱,步履蹒跚的女人在这夜深露重,寒风乱窜的山头,孤独地走着,原本乌黑的秀发此时平添了几许花白,山头上的杂草,发出呜呜的低鸣,似乎在为她悲鸣,在为她惋惜……她爱的两个男人,她都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她凄楚地笑了起来,那凄凉的笑声,回荡在四周,又被风吹散……单薄的身体似乎再也支撑不住,眼前一黑,她想,如果她就这样死了,或许心就不会那么痛了……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光阴从她的指尖迅速划过,还来不及感受生活带给她的磨砺,蓦然回首,头上已是银白的霜雪,岁月的痕迹爬满了原本光洁的脸庞,这个五十岁的女人坐在一个约莫十一二岁的小女孩身旁,督促着小女孩伏在书桌上练毛笔字,虽然是冬天,可她穿着一件蓝色的碎花旗袍,旗袍的一侧别着一块小手帕。
一个十七八岁,身穿蓝色运动服的男孩从房里拿着皮球走出来,丢了句话就走了出去。“妈,我去打球。”
女人没有抬头,只是仔细地检查小女孩的作业。
“洗非,洗非。”身材高大,五十多岁的李振海推门走了进来,手里拎着一个公事包。见他口中的洗非正在给小女儿辅导练字。语气有些激动。“你知道谁来沈阳演出吗?”
将小女孩写好的字放到一边,被叫做洗非的女人问:“谁呀?”
“梅兰芳!”
梅兰芳三个字让张洗非的手顿了一下。“什么时候?”她用略带平静的口气问道。
她想,她这一辈子值了,满清后裔,却在年轻时落入风尘,成了蔡锷将军的红颜知己,在她人生最辉煌灿烂的时候,梅兰芳为她唱过戏;做了别人的姨太太;拿枪打过人;躲避过追杀;跳过火车……
要问她是怎么跟李振海在一起的,她已经无从回忆,只知道跳下火车后的那几年,她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蔡松坡的死,让她失去了爱上别人的勇气,王玉魁的死却让她知道什么叫悲痛欲绝……那几年,她什么都干过,在服装厂做过女工,帮别人洗过衣服,烧过锅炉,当过保姆……可这些生活上的劳累都无法磨灭她内心的伤痕,一道道,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殆尽,反而愈加清晰。
早年丧妻的李振海和她一样是一个老戏迷,常常在周二的时候和她约着去大西门附近的金城电影院看戏、听评书,一来二去,两人娴熟起来,李振海总是大妹子、大妹子地叫个不停,常常也对她照顾有加,初识的时候,她知道李振海难得碰到一个戏曲知音,对她十分欣赏。其实,李振海是喜欢她身上那股安静的气息。
“大后天。”李振海殷勤地从包里掏出两张票。“我好不容易才弄到的。后天我们一起去吧。”李振海知道张洗非喜欢听戏,所以家里一有闲钱,就拿出来为她买票,让她去听戏,这一次梅兰芳到沈阳巡回演出,票价十分昂贵,他可是借钱买的票。
李振海欣赏张洗非的才华,更喜欢她身上迷一般的不凡的气质,他总觉得这种气质高贵的女人,不应该沦落在这种困苦的生活里。
后来,李振海带着小女儿去听戏,小女儿李桂兰没听懂,张洗非耐心地为她讲解,于是李振海就有了照顾她的念头。记得她第一天搬进来的时候,将一个盒子放在了梳妆台上,那是一个老旧的盒子,那盒子有些年代了,但是从盒身上镶嵌的绿色翡翠,可以看出价值不菲,盒子里有一封信和一张照片,她总是喜欢默默地抚摸着照片,仿佛在怀念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