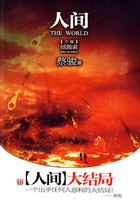赖二熊对小凤说,也不怎么贵的,去了就知道的。
当初认识小凤,小凤给他的感觉是,很淳朴,很实在。那些奇异而美好的感觉,一直深藏在心。当年(不到一年啊),小凤从微薄的收入中掏钱请他吃饭,那是何等珍贵的记忆?现在,他要好好款待小凤,这顿饭要山珍海味,要超级豪华的服务。他要小凤见识从未目睹过的奢靡世界。
王军军是个聪明人,多少瞧出了一些蹊跷来。当然,他是以自己的方式观察,和赖二熊的本意是有些出入的。饭局途中,他借口报社有急事先行离开。要是吃完饭才找借口走掉,留给他们的机会就少了很多。
可是没有人想到,正是他无意中留给他们的机会,最后毁了赖二熊的一切。
王军军走后,赖二熊有些不适应,小凤却开始轻松起来。赖二熊看到小凤开心,便也高兴起来,就尝试鼓励她喝酒。起初小凤坚拒饮酒,后来抵不住劝,同意喝一点点的啤酒。赖二熊不想她醉,只要肯喝一点,他就高兴了。他说她喝一口,他就喝一杯。她说那样不平等。他喝一杯,她也要喝一杯。按照如此约定,他们居然开始了两个人的竞赛。人一开心,话题就多了。小凤小脸变红了,赖二熊怕她醉,连说,别喝了,别喝了。
小凤摇头说,莫(没)关系,莫(没)关系。
渐渐的,她说话失控,家乡话时常冷不丁冒出来,逗得赖二熊哈哈大笑起来。她明朗健康的脸庞,因为酒精的作用,真是愈加光彩夺目。
那天晚上,赖二熊不知道是怎样度过的,只记得半夜嘭嘭嘭急促的敲门声吓醒了他。那是长到二十七岁第一次听到如此恐怖的夜半敲门声。他懵懵懂懂爬起来,急急忙忙去开门。伸到眼前来的,是一张愤怒得变形的脸。啊,那是阿燕?痛苦使得她还算好看的小脸全都扭曲了。那一刻,他实在是愚蠢的,他问她为什么半夜来找他。他冒冒失失地说,发生了什么事?让她如此恐怖?
以他对阿燕的了解,遇见她此刻的表情是少有的。低头看自己,他更加吃惊:哎,他居然赤身裸体站着。他一向不裸睡的,今晚居然没穿衣裳睡觉?
他走向床铺去取衣物,蓦然看见宽大的双人床上,赤裸地蜷曲着一个女娃子。那年轻的女娃子躯体白皙,娇柔,结实。天呐,他头晕了……这,这是怎么回事?
那女娃子当然是活的。她嘴角微微动,胸脯随着呼吸起伏战抖……唉!那个倒霉的晚上,阿燕说了些什么,他全然忘记。只记得她歇斯底里的号叫,眼睛发着凶光,满脸的泪水。他的脑袋一直昏昏沉沉。是的,他完全迷惑了。她为什么生气?她为什么要那么生气?
简直是恶狠狠的,她一扬手给了他一个响亮的巴掌,然后怦然踢门而去。他怔怔站着,擦去嘴里溢出来的鲜血,复又倒下去睡。事实上,那个晚上他一直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早晨醒来听见小凤抱住被子大叫。
叫什么叫?他也吓了一跳。他想起昨夜……她怎么会在这里?他迟疑的头脑,弄不清楚这样简单的问题。
血、血。她继续叫道。
什么血?赖二熊也看见床上一摊凝固的血迹。啊,我做了什么?他看见小凤身体紧张僵硬,表情懵然无知,神情无不惊恐。她怯怯地努力掩住身体说,哎,我的衣裳呢,我的衣裳呢?
衣裳?啊,她为什么在我的床上?他一下子不知道如何是好。
我的天,昨晚好像发生什么事了?昨晚,好像阿燕来过这里了?
他突然恐惧地感到,刚刚构筑好的世界,正在成片地坍塌——
10
他尝试着给阿燕打电话。他要解释清楚。是的,并没有发生什么,一切都是偶然的。在这些偶然里,没有一个是他有意的。
然而,阿燕却始终不肯接电话。做股票投资的女人是决绝的,她们什么风险都曾遭遇,什么风险都敢承担。这样的人,宁愿认赔出局,也不愿苟且偷生。常常是电话铃声响过,再打过去她的电话就已决然关机。看来,阿燕是铁了心了,她不肯再理睬他。而他呢,由失望、愤怒,渐渐变成忧愁、悲伤和幻灭。
他不能失去阿燕。是的,他不能失去她。他要找到阿燕解释清楚。他相信,曾经有过的美好的世界是会回来的。过去一直没有机会去阿燕家。有一次,阿燕告诉他说她的亲妈早已去世,现在家里是后妈当道。他还以为是这个原因她才一直没有领他回家。现在,他开始有些明白阿燕为何一直不带他回家,原因其实不止一个。自始至终,阿燕对他都怀有挥之不去的疑虑。她宁愿将身体交付于他,却不肯将家庭介绍于他。最近许多天,他在公司楼下守候,到阿燕回家的路上等待,最后直接到阿燕专用的大户室去寻找,均无所获。公司里负责阿燕业务的同事告诉他,阿燕最近休假,不来大户室了。
这些骤然的变化,对他是沉重的打击。某日,他突然想起他与阿燕相识的牵线人——“我是你姐姐”。哎,怎么忘了她?
他找出电话。和阿燕一样,“姐姐”的电话,响了很久也无人接听。
忽一日,总算打通了她的电话。电话那头声音听着很熟悉,猛然间还以为是阿燕呢。
有事吗?“姐姐”问。
他迟疑地说,记得我吗?
“姐姐”说,你?当然记得。你是不是做了对不起阿燕的事?她开门见山地说。
赖二熊低头说,是我错了……阿燕不肯听电话。
“姐姐”沉默了一会儿,说,有些错是不能犯的。你该明白这道理。
赖二熊说,我知道。
“姐姐”说,阿燕说她不可能再跟你继续下去了。你太伤她的心了。你知道吗?你们之间,本来是没有可能的,可是,她愿意给你机会。你想一想看,一个人有一次机会已经很不容易,而她曾给过你不止一次机会。特别是在你身无分文的时候,她也没有嫌弃过你的。
赖二熊说,这些,我都知道的……她的确是很好,她真的很好。
你们男人啊,让我说什么好?要我说,你真要明白这些,就该好好珍惜的。不是现在,而是从一开始。她这样说。
是的,我知道已经晚了。他沮丧地说。
以后,你不要给她打电话了。她说。
赖二熊心想,不要打电话给她?她好绝情啊。可是,对此,他仍心有不甘。他还想努力挽回点什么。
“姐姐”说,你该明白的,一切都已结束。阿燕跟我说,你们男人没有一个愿意真心对待别人。她好累,也好厌倦,她不想再见到你了。
赖二熊忽然赌气说,不!我一定要见到她。
“姐姐”说,你见到她又有什么用处?她不是一个轻易改变主意的人。
赖二熊执拗地说,我也不会改变的。
“姐姐”生气了,说,你不会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吧?
赖二熊本想说他是很爱很爱阿燕的。可是尝试了一下,才发觉这样的话,他说不出口。是的,他不明白他是不是真的爱她,他只是凭直觉知道,他不能失去她。失去她,就意味着已有的一切又将全部悉数失去。这样想,一阵伤感袭上心头。
他忽然问,我可以见一见你么?
“姐姐”听了,轻轻一笑说,我老了,不值得你这样的年轻人来见。
赖二熊喃喃说,就是想见见你……
“姐姐”说,还想我再帮你介绍女友?
赖二熊说,不敢。
“姐姐”那边,又沉默了片刻。真是出乎意料,她居然答应了他的要求。赖二熊很迷茫、难过。那女人将见面的地点定在深圳图书馆广场。赖二熊听了,心中不免一动,这“姐姐”看来很喜欢图书馆啊,她喜欢阅读吗?要知道,上次见阿燕,她也是定在这地方的。
前些日子阿燕托人来将小宝马开走了,现在赖二熊重又成了步行一族。在瑟瑟暮色中,他寂寞地漫无目标地在广场附近徘徊着,忐忑不安地等待“姐姐”的到来。
南方的秋天仍然溽热。远处,像油画一般堆满云朵的沉静的莲花山,在苍莽中依然郁郁葱葱。
电话响起。他去看那号码,正是“我是你姐姐”打来的。
你听着!慢慢朝后看。“姐姐”说。
电话贴在耳旁,赖二熊身子没敢动,心里却高兴得不行。他喜欢这样有意思的人。天呐,简直就像西方电影中既有品位又浪漫的女人。随便一个见面,都能够尽显机智与品味。
他依言慢慢转动身体,立时就呆住了:眼前这人,不是阿燕却是谁?秋天来了,她仿佛更加瘦小了。憔悴的脸,也仿佛更加苍白了。脚下的皮鞋,却不经意地沾着些乡村的泥土,在晚风中头发有点乱。
是你?!他激动起来,兴奋、冲动、新的希望……
别动!就站在那里。阿燕说,制止了他。
赖二熊并不打算听她的,仍旧想要走过去。
Stop!阿燕喊道,你要不站住,我就走了。
赖二熊只好停住。现在,他与阿燕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仿佛银河两岸的两颗星星,却不是牛郎与织女,而是两颗完全陌生的星星。
阿燕你……他欲言又止。
阿燕皱眉说,别喊我阿燕!我曾经告诉过你的,我叫雁雁,是大雁的雁。不知为什么,你一定要叫我阿燕。
大雁的雁?很纳闷啊,他不是一直喊她阿燕的吗?现在,她却来计较这称呼。
阿燕说,过去纵容你,没去纠正你,将错就错这么久。单单就是这件事也表明,从一开始,我们之间就是一场误会。
误会?
雁雁说,燕子跟大雁,分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鸟儿。这点常识你也没有吗?
我晓得的。他说。
雁雁说,你一点也不在意我。
不是的,我在意你。他说。
雁雁说,你知道不,女人最重视男人什么?
他笨拙地回答说,在不在意你?
雁雁生气地说,你就只会鹦鹉学舌么?告诉你,女人最在意的是男人爱不爱她,而你根本不爱我。
赖二熊沮丧地说,情况不是这样的。
雁雁说,那情况是怎样的?
赖二熊说,你知道的,你知道我爱你。
雁雁很失落地说,现在说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想问你,是不是男人骨子里,都喜欢追逐女色?
赖二熊瞠目结舌,没想到她会如此赤裸裸地追问自己。追逐女色?真要说起来,在这个世界上,男人的天性又何止是追逐女色?追逐金钱,追逐物质,追逐人世的珍奇……男人的天性,简直可以说就是猎人的天性,他想要追逐的东西多着呢。
雁雁恨恨地说,我讨厌自私放纵、不负责任的男人。
无论雁雁怎样想,无论她愿不愿意重归于好,单就赖二熊来说,他在心里仍对阿燕抱着一线期望。不!不是一点点,而是非常热切的期望。他知道自己不能没有她,所以,这些天他一直很痛苦。他的痛苦建立在他的后悔上面,他的后悔又带给他更多的痛苦。现在,他发现自己总是后悔,一个人为什么总是要后悔呢?他的性格或者他的人生,一定有些方面严重的先天不足……唉!难道是自己过于急于求成了么?
他知道的,他知道,自己倘若当初能够一直哄住阿燕,然后,跟阿燕结婚,生子……那么此后,即使出点轨怕也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唉!都说广东女人对男人纵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他很倒霉的,他遇见的第一个广东女人,便是如此凌厉决然,不可侵犯。
在他胡思乱想的当儿,雁雁冷冷地说,还记得你在晚报上看到的消息吗?38岁的年轻富翁不明不白死了,警察也没能破那个无头案……你们津津乐道的那件事情……你还记得么?
那个有钱人?他想起那个下身被人割掉的倒霉透了的男人。哎,他不安地说,你为何提起他来?
雁雁盯着他,平静地说,这个男人,他曾经是我的丈夫。
赖二熊吓了一跳。老天!谋害亲夫?他的后脊梁背不由得阵阵发冷。啊,她会不会有朝一日也派人来谋害自己?这么一想,他感觉自己的腿在不由自主地战抖。
他瞧见雁雁乌黑的头发里,斜斜的插着一枝新鲜的小菊花,不由看得呆呆的。
雁雁见他看自己,便伸手将头边怒放的小菊花摘下来,拿在手里把玩着。这瘦小的女子幽幽地说,你知道么,今天我去关外的墓地,看望了他。
看他?他喃喃说,腿仍在抖。
人虽然死了……怎么说,也曾经是我的男人。她说。
赖二熊心里涌出一种无法言喻的感受。他不能明白,眼前这个女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雁雁打算离去。他胆怯地问,你要走了?
雁雁回答说,别再打电话给我了,知道吗?
他说,好吧。
现在,他想起了那个名字叫做“我是你姐姐”的人,正是那女人再一次安排了阿燕来见自己。起初他还是很感激她的,可是现在,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不经意间已洞悉了人生的若干恐惧与残酷。现在,他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那女人了。
赖二熊喃喃地说,我没有想到会见到你。
雁雁停住脚说,什么意思?
赖二熊说,我是想见到你。只是……那位“姐姐”怎么没来?
雁雁一双冷冷的眼睛,直直地看着他,这使他有点慌乱。过去,他没有发现她的眼睛居然如此锐利,生冷。她的皮肤有点灰,有点暗,反衬出眼神更沉。现在,他发现自己好害怕她。
雁雁说,你真想见她?
赖二熊点了点头。
雁雁沉默了片刻,说,告诉你吧,我就是“我是你姐姐”。
老天!赖二熊不由得心中暗暗叫了一声。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是她呢?她与那“姐姐”,实在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啊。那怎么可能呢?
他迟疑地说,不会的不会的,她怎么会是你?
他很想说,她比你更成熟,更有母性。可是,话没有说出来。现在他感觉她的成熟,早已超过了那“姐姐”。是的,她是过于成熟了。
雁雁沉思着说,按道理她不会是我的,这个我也知道。可是,我一直想,一直想让她成为既像姐姐又像母亲的人……关心我,体贴我,呵护我……让我不要再受到伤害。雁雁说罢,深深地叹了口气。
伤害?他忽然想起她其实是个孤儿,是只有父亲没有母亲的孤儿。
雁雁出神地说,是的,伤害!明白么,你网络上遇见的那个“姐姐”,正是另一个我,是另一个渴望温暖的我。
另一个你?
思寻良久,雁雁终于说,希望我们,永远不要相遇了。
赖二熊怔怔地站着。此刻他有一点糊涂,又有一点清醒。他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再见。雁雁幽幽地说。然后转了身。
一个世界,就这样离他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