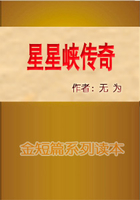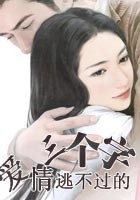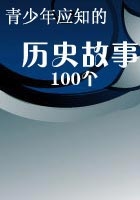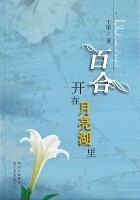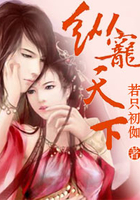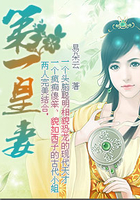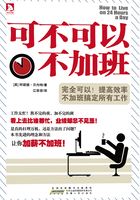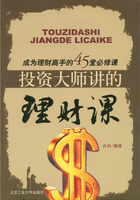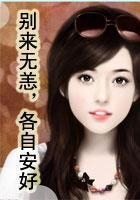四
鲁迅先生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这是多么富有哲理的一句话啊。长生在走向陌生世界的时候,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自己是在“走”一条“路”,他的每一步每一个脚印,仿佛都对这个世界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有一种创造性的神圣感。
他在家乡的时候也常常到村后的龙王山上玩耍,但那是他所熟悉的山,哪怕没有别的人,哪怕是漆黑的夜里,他闭着眼睛都能找到下山的路。而现在,他必须学会用一种冒险家的勇气去探索一座新的山,摸清它的秉性与脾气,试着与它打交道,因为他已经将自己命运的一部分与它紧紧关联在一起了。他常常走过一段路以后再回头看一看,看到的总是很陌生的景象,然而他已经走过来了——所以,陌生是不可怕的,陌生是可以征服的。
冬天的山像老人。树木大多掉干了叶子,像除去一切修饰的人一样,表情肃穆得惊人。许多蔓生植物牵了丝丝缕缕的线,沿着泥地裸露的表面与狭小的石缝缓慢地爬行,也许它们真的是爬得太慢了,不等到达终点,就落尽了绿叶,只剩下枯枯的蔓藤,像老人手上枯皮下的青筋。长生走在苍老的山上,踏着它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每走一段就在显眼的地方作上记号,以防万一走不出山,还可以走走回头路。
太阳升起来,山上开始变得暖洋洋的,是个好天气。像有个大炉子在烘烤着草甸,山上弥漫着草类发酵的香甜味,那味道由底下向上面抒发,嗅着,都有一些飘飘然的感觉。长生饿了。从饿了这一点判断,已经快到正午了。
他从怀里掏出馒头。是早上从食堂拿的,炊事班手艺不好,做出的馒头又黄又硬,战友们常笑说这是“军用馒头”,军用的嘛,带点军黄色,有棱角的。长生的饿使“军用馒头”的一切缺点都被忽略,他的牙齿舌头与馒头碎屑充分地接触,嚼得很慢很慢,把又冷又干的食物吃出了温热与潮湿,还有淡淡的甜味,这是艺术,如果把这一类的艺术发挥到极致,也许人可以做成任何事情。
馒头还没吃完,他发现自己竟然已经在走下山的路了。原来这山不大!这倒是没想到的,他一心想的就是爷爷走的那座山,走也走不完,有着无数艰险挫折在前面埋伏着,哪会这样顺利呢?长生开始失望了,这座山不过如此,小白一定也就在不远处,一逮就着。
下到半山腰,已经可见山下的小村落了。稀稀拉拉的房屋东一个西一个,就像小孩子亲手造的玩具盒子,盒面上若隐若现地飘浮着一层淡蓝的炊烟,农家饭菜那朴实的香味裹挟在炊烟里漫天游荡。长生的鼻子循着那香味一翕一翕的,竟有些酸了。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离家已经很远很远。他怕是走不回去了。
正当午时,家家在做饭,村里人少,长生像走进一座凭空冒出来的空城里,极不自在地一边走一边东瞅西看。到了一棵大槐树下,有个小杂货铺子,倒有两三个闲汉赖在女掌柜的窗口前说着笑话,一见到他,全都把脸转过来,奇怪地打量他,却谁也不说话。那窗口里烫了卷发的女掌柜总有三十七八岁,很是有些见识一般,大大方方地冲长生喊:“当兵那个——你干啥?”她这样主动反倒让长生显得拘束了,他走近几步,隔着前面三个汉子硬生生的目光屏障对女掌柜答应道:“我找一个人。”
“找哪个?”
长生比划着说:“他……比我矮一点儿……穿和我一样的军装……”
女掌柜惊异地说:“穿军装的?……倒是有一个……”她把嘴抿紧,似乎触碰到了一个易爆物品般小心起来,紧张地问:“你找他干啥?”这一反问把长生也弄紧张了,他涨红了脸一时对答不上来,窗口前的几个闲汉却是来劲了,一个一脸木渣渣胡茬的猛地把嘴里咬的烟嘴夺下来,惊喜地大声说:“我就晓得要来找他!部队早晚要来找他!”他为自己预言的成功而激动不已,站起身来冲长生嚷嚷:“——就是前面那个拐角,门口有块大石头的那家!”其他人一听,都说:“是咧是咧,那家有一个!”脸上都露出兴奋的笑容来,有点等着看好戏的样子。长生谨慎地问道:“他……走了没有?”他们又异口同声说:“没咧没咧!就在屋里!”
大胡茬看来是个闲人中的热心人,他主动担负起为长生引路的任务,另外两个也不辞辛苦地跟了上来,明摆着就是看热闹了。乡村生活里一年到头难得有那么一两件刺激点的事,错过就很不划算了。长生被前呼后拥着,不知不觉额上沁出了汗。除了当兵走的那一天,他还没有做过众人瞩目的焦点人物,众星捧月,那月亮一定是经得起捧的,他突然对自己没有信心了。对于小白,他该是哪一种姿态?当了这么些人的面,也许该严厉些——为着这一层想法,他已提前板起了面孔。
在他们轻车熟路的带领下,那一户人家的门像是突然从天而降地立在前面。长生陡然感到一阵轻松与快慰,关于以后都不重要了,小白是他胜利的旗帜,是他奔波的终点路标,是他在这个地方唯一的亲人,如果没有别的人在场,他几乎想冲进去拥抱小白了。这时候,他身后另两个闲汉停住了步子,站在离着门有一丈来远的地方耐心地等待着,那架势是很能打持久战的模样,眼里净是期盼的欣喜。长生看出来,他们有好奇心却没有胆量。只有大胡茬倚仗着带路人的身份大摇大摆地上前拍门:啪啪啪!啪啪啪!一边喝喊:“军爷!军爷!找你的人来啦!”
那门怕有好些年月了,油漆掉得看不出颜色了,斑驳的木头上净是阡陌纵横的印迹,长生盯着门正看得仔细,冷不防门板哑着嗓子拉开了,立在门后的是一张和门板一样陈旧多痕的脸,散发着阴雨天气木头深处渗出来的腥腐味,神情阴沉地打量着门外的人。他是个老人,瘦而硬朗,头发显眼地花白了,对于整个生活却有着相当多的不肯原宥的理由,因而是愤懑的,不平的,老死不服输的样子。当他的眼光触及到长生这身军装时,眼睛忽然像原本奄奄一息的油灯,给谁一拨灯芯,亮了。他盯着长生,说:
“请进来吧。”
他超出农民身份的彬彬有礼的举止震住了长生——请——教导员也不会这么说!但是他“请”得很有限,很有针对性,所以在长生愣愣地跨进门槛时,门板就端端正正地在带路的大胡茬面前关上了,又是低哑地叫了一声。不过从那门板微微抖动的态势看,外面的人又不屈不挠地把眼睛紧贴到门缝上来了。
院子很小,但是围墙厚而敦实,密不透风,就有些壁垒森严的模样。老人请长生在院里的一张竹椅上坐下,自己另去搬了竹椅和方凳,方凳上很快放上了茶水和一碟自家炒的干货。这老人看样子是不善与人接触的,但他对待客的程序非常熟络,好像他是一直等着这个客人的。长生有些消受不起了,他的城府仅限于十九岁这个年龄的正常水平,所以迟钝地开了口:
“我……”
老人神情严肃地抢过话头说:“你先听我说行不行?”虽然是征询意见,却是不容否定的坚定口气。他面色黝黑,目光深不可测地看着长生道:“我也是当过兵的……”这才使长生注意到,他居然也穿着一件军装,旧式的,早已洗得发白了,领口、袖边都磨破了,有几处还小心地用颜色尽量相仿的绿线缝起来——再旧也是军装啊。他见长生开始盯着自己的军装,便欣慰地微笑了,又为自己能与他平起平坐感到由衷的得意。他说:
“我穿这身军装有三十年了。”
这只是个引子,但是像一声长长的叹气,有着太多欲诉还休的味道;他把“三十年”这样沉重的字眼说得轻飘飘的,裹挟在空气中一带而过。长生真的是太年轻了,他这个年纪是听不出弦外之音的,他一心想的还是小白、小白、小白……老人对他的心理有着相当稳妥的把握,所以不给他留下可以插嘴的空间。老人说:“我早你三十年当兵。刚当兵时村里像出了个大人物一样兴奋,大伙都不喊我乳名学名了,叫我军娃;后来,年纪大了,叫我军叔,现在么……”长生脑子里就浮现出刚才带路人拍着门板喊“军爷”的样子来。
三十年前,也有一个像长生这样的愣头小伙子,从这个山村里横跨大半个中国被接到部队去了。在同样憋闷而黑暗的军列军厢里,车外同样的灯光也一晃而逝地刮过他稚嫩的面容——他也没有很明确的目标,只是遥远而坚定地认为自己就是去保卫祖国,保卫毛主席。然而他的军旅生涯只有两个月——不是逃跑的,是祖国和毛主席不要他保卫了。那天他的指导员神色相当沉重地叫他去谈话,是个天色冻青的上午,他走过连部长长的走廊时,一步步走得很艰难,觉得天在往下塌似的,是个极其不祥的预感。到了连部会议室,才知道找他谈话的还不只是指导员,从教导员、营长到政委都来了。有封揭发信寄到部队,说他的成份有问题,他不是贫农是富农。部队调查的结果是,他家里不久前被揭露,在分土地时就有十块大银圆隐情不报。那十块银圆,按当地的生活水准,划个地主也是没人反对的。尽管他父母一再解释,是一位远房亲戚寄放在家里的,却没有人相信。
因为那十块大银圆,因为隐情不报,因为成分的质疑,在这个冻青的冬日上午,他的远大理想变成了巨大的重金属物件,沉沉地下坠,他能听到它落地后轰然而起的杂音与回声。两个月,他从家乡到部队,又从部队回原籍,像是谁开的一个不伤大雅的玩笑,又像是完成了一次免费旅游,然而不管怎样他也做不到一笑而过,他很清楚自己的命运发生了怎样不合情理的变故,他的人生也从此有了清晰具体的目标。
谁也没有想到他回乡后强硬的态度,他拒绝承认自己的富农成份,坚信组织上终有一天会调查清楚的。他不断地写信给上级部门反映情况;他每天都穿着部队带回来的军装,配好毛主席像章,并私下里把帽徽和红领章精心收藏好;他用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克己奉公,正直为人,认真阅读《人民日报》,三十年如一日;他每天出门劳动前都把待客的一套用具备好,调查情况的人来了随时可以用到;他相信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他的政委会热泪盈眶地迎接他回去,拉住他的手对他说:“你是一个好战士!”……村里人很早就知道,那个“军娃”已经“反映”了,迟早会解决问题重回部队的。但是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过去了,没有人来调查过,旁观者的信心是很容易崩溃的,他们看出重回部队只是他单方面的想法,渐渐的,看他的眼神就像是看个有病的人。他岁数大起来,就有人教小辈们喊他“军叔”、“军爷”,分明是嘲笑的口吻。由于担心部队不收结过婚的人,他迟迟不谈婚事,终于在三十九岁那年和一个大他八岁的寡妇结了婚,对方带来两个女儿,都不太亲近他,一到婚龄都赶紧嫁走了。直到他老伴去逝了,他根本就没有续弦的念头,人们便相信他会就这样等到死。
三十年的时间其实也很单纯,就在这样的等待中,每天都怀着一样的心情活下去。三十年,军装都换了好几种样式了,他还穿着那身过时的旧军装,把自己套在过去的时光牢笼中。他倒是很散漫地叙述着,不甚上心似的,品咂着已经泡开的浓茶,眯起眼睛回忆当年他的连长、指导员和班长,还掏出一张发黄的照片给长生看,上面是个壮实的年轻战士,眼睛睁得大大的,很憧憬未来的样子——很像老人的小儿子或者大孙子,当然长生知道那就是他本人。
长生有点明白了,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误会,这个误会的澄清会使双方都感觉到深深的失落。但他还是说了:
“但是……我不是……来调查你的人……”
“军爷”却十分宽容地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一站在我面前,我就知道了。”他叹了口气,接着说:“早就没人管几十年前的成分不成分了,我是瞅准了你这身军装,想和你说说话呢。”这样一来,长生倒没有话了。
走的时候,长生的一条腿都跨出门槛了,又回过头来,喃喃地安慰道:“说不定……”老人的头像风铃样来回摇晃,截断他的话头强硬地说:“没可能啦——”
“我的老政委——两年前,去了。”
五
这个下午长生有说不出的沉重与茫然。他所预期的人和事都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存在着,他还得去寻找。原以为是一座山的问题,看来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找一个人和找一条路,都是带有未知性的探险。在“军爷”悲壮的故事里踏上新的找寻之路,对长生而言又添上了一种莫可名状的复杂心情。
太阳淡下了许多颜色,看上去简直灰不溜秋惨不忍睹。他低着头走在凹凸不平的乡村小路上,每走一步,后面的世界就消失了一尺,他所经过的、刚刚熟悉起来的世界,一点点地消失了。留给他去走的,永远是最艰难与陌生的。小路很快到尽头了,前面一百多米的地方横着灰白的一条线,一辆辆奇形怪状的大客车、货车、三轮车在线上来来回回地穿梭疯跑,他知道,这条线是村外的公路。这条线成了他前一段行程的终点线,长生再是穷山沟里出来的孩子,也清楚地明白,有公路,那路就是走不完的。全国有多少地方啊,城市,乡村,它们就像一粒粒珠子,由公路这条线串连着,比蜘蛛网还繁密、细琐的公路线。
车鸣声越来越清晰地迎面扑来,长生感到脚下越来越酸软无力,走得都有些期期艾艾、磕磕碰碰了。在看到公路的那一刻,他终于悲哀地相信,小白去了更远的地方。长生原本计划今天之内就把小白找到带回去的——找个人嘛,多大回事?在家时他常把逃学的弟弟从各种旮旯缝里揪出来——他甚至想好了晚上参加体能训练前一定要把训练服的一颗扣子钉上。关键是,小白不是他弟弟,他的逃也不是逃学的逃,是永远不回来的那种逃。
一辆大客车从远处驰来,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减速,在长生根本没有回过神的时候稳稳当当地停在了他面前。车窗里横着晃出一个一头乱发的男人脑袋,他费劲地喊:
“当兵的——走不走?”
长生懵懵地问:“去哪里?”那男人又扯着嗓子快活地喊:“去城里!瞧大姑娘去!”车里一定有不少人笑了,本来笑得很淳朴,很老实,但是声音在车里受到了约束,听起来就有些瓮声瓮气的,像不怀好意。不过长生什么也没理会,他像第一次看见汽车一样惊恐地盯着这个铁皮庞然大物——他从来没想到坐车,坐车是件严重的事情,至少它有种距离上的不可估量的意味。他也从没想过到城里,城市在他头脑中只有入伍时在火车站转车时所看到的闹嚷嚷的景象——难道要到那个人山人海的地方去找小白吗?长生被这个想象吓住了。
不管怎么样,那个好说笑话的三十岁的卖车票的男人改写了长生这一阶段的人生。三分钟后长生已经坐在一个靠背稀脏却格外合体的位置上,把头扭向车窗外,那些田园风景贴着他的面颊一闪而逝,变化多快啊,每一秒钟都是不同的新世界。他的身体正在飞,飞向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豁出去了——他恶狠狠地闭上眼——豁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