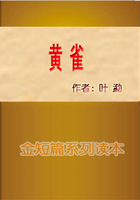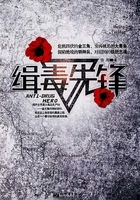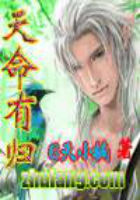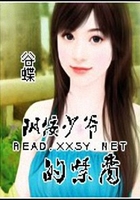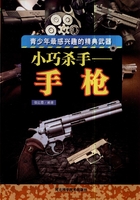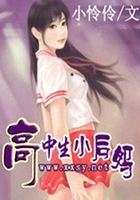1
到了连队,就直接称呼连长。这样才亲切,像是自家人了。叫张连长是不行的,见外。没人说过这个问题,但进了连队的门儿,就像被赋予了某种天赋,你会忽然明白这简单却微妙的规矩。
第二个问题是——必须判定连长是否具有幽默细胞。然而在最初的五分钟里谁也不可能轻易下结论,于是王远和肖遥——前来报到的两个实习学员——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一无所知者应有的沉默,或者说沉稳。
连长裹了一身塑料围腰走过来,塑料围腰上黏着黄棕色的糊糊,看上去,连长的上半身是个未完成的泥雕作品,还散发着新鲜的粪臭。“我跟通信员交代了,”他一边脱去脏得不成样子的围腰交给一个跟班似的兵,一边神情淡漠地说,“叫你们来了就到猪圈找我,怎么,找不到?我只好把那边的活儿停了来恭迎大驾!”
肖遥听到“来了就到猪圈找我”本想笑,但话里明显的讽刺口吻阻止了这种冲动。他撇了撇嘴,向王远表明,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负担谈话责任的。王远忍住不快,极尽礼貌地解释:刚刚才到,把行李放下了,又去做了一番洗漱……
连长嘴角牵扯出一丝嘲讽,显然是不认同这些解释的,一边走一边说,当年我去特种大队参加集训,坐了三天火车,报到时行李一放下,以为可以洗个脸喝口水,人家就说,去,参加第四分队,搞一组五公里!——老子第一次听说五公里越野还有按“组”来算的!一组是四个!四个五公里!每两个五公里中间休息十分钟,就这十分钟也不让人消停,要做一百个俯卧撑,或者手持重物做一百个蹲下起立……
王远、肖遥一声不吭地跟着他,在他碎碎叨叨的荣耀回顾中参观了连队大半景观——无非是毫无特色、堆满器具的仓库,上了岁数、苍白脸色的营房和被青苔小路环绕的日渐破败的食堂。两个年轻学员努力抑制着不断泛上来的阵阵困倦,王远闭着嘴,做了个超级长度的深呼吸,成功地替代了一个哈欠。就在这时——后来他告诉肖遥——就在这时,他确认了连长的幽默感。
正好三个人已走到修理连门岗,连长下巴一抬,在此发布了结束语:“以后,只要看见我的半身塑像,就知道是到我的地盘了!”
门岗旁边是一台伤筋动骨、垂头丧气的大型装备车,不知停放了多少时日,轮胎泄气以至浑身瘫软,车身害着皮肤病一般成片脱落绿漆,但那庞大的身形和结实构架隐隐透露着昔日的威严。
其实修理连早已名声在外,实习学员们来之前就知道的。
“那个修理连号称光头连,好端端的娃儿都要被带坏,简直去不得!”泄密者用严肃的姿态告诫王远,“出了名的烂泥潭!”
现在王远就陷在“出了名的烂泥潭”里的一张两铺位行军床上,是下铺。他和肖遥是地方大学毕业生,刚刚结束了初入军营的基础训练,按规定到基层连队实习。原以为基层都跟电视上演的一样,天天英姿飒爽地带兵演武,没想到给分到这么个小、远、散的单位来,倒霉透了。
作为实习排长,他们分别住在不同的班,和战士在一起。其他人都睡着了,鼾声渐起,黑暗的空间里慢慢浮现出各种音符,节拍不一,但多是降调。闭上眼,王远似乎也能看到睡着的兵们白亮亮的脑瓜,像一盏盏大瓦数的白炽灯,晃得眼疼。
光头是修理连的兵们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来来去去的都顶着“大灯泡”,没有哪个连敢像他们这样个性而张狂。上午来了不久,王远和肖遥便瞅准机会逮住通信员小何私下里打听全连光头的底细。小何面容清秀,像气质儒雅的少年僧人,用手摸着光滑的脑瓜,轻声说:“这都是连长的杰作。”
他们的张连长没有别的爱好,就喜欢给兵理发。天地良心,他真的是“理”而不是“剃”。但理发是个细致活儿——美发店里都是一水儿的温柔型小男生,而他那么粗咧咧的一个汉子,哪能为细如针尖的头发耐烦呢!他的所有理发过程都是一样的:在兵的左边脑门削削头发,短了,又比照着削右脑门,削完一看,右边又短了,赶紧又削左边……反反复复,要不了几次,两边头发就短得失去比赛资格了,可还搁不平,最后只好采用唯一的公平办法:剃光。
全连战士都陷入了瘟疫般的理发恐慌之中。为了躲避对头发的制裁,大家变着方儿地软抵抗:装病、出公差、请假外出,还有,拼命讨好通信员——他是为连长具体物色牺牲品的执行者——当面讨好,背后却又恶意地叫他“太监”。一到周末,连长摆好架势要为战士服务了,小伙子们就往光线暗的地方躲,已经被剃过头的兵故意制造气氛,满楼道乱蹿,边蹿边嚷:“河伯娶媳妇啦!”
当光头兵的数量一个一个地增加起来,修理连的名气也在翠鱼梁大山上悄然而起,大家都叫它“光头连”。极有责任感的政治处主任听说此事之后专程拜访了修理连,大家满怀期待这位大领导能够改变现状,不料主任只是折中地说:“剪短就行,不用剃光嘛!”张连长就在主任充满人性关怀的目光注视下,当场给一名战士削完了头发,主任克服着一切心理障碍久久凝视着这个艺术成品,觉得它一直在沉重考验自己的审美忍耐度,终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以完全投降的口吻说:
“还是剃光吧!”
修理连从此不再有翻身的机会。它几乎是被上级正式命名的“光头连”了。
想到这,王远忍不住笑了一声。只一声,接着便叹了口气。他侧过身,掀掉行军枕,命令自己数到五十必须睡着,可大脑无法完成任务,耳朵只听到硬邦邦的床板传递着心跳的声响,咚,咚,咚,硬邦邦的声响……
连长有句口头禅:我是个粗人。仿佛这就解释了他的一切言行。普通人因为害怕被批评,总是率先给自己定个低标准,拿这做块遮羞布,高高地支起来。支在明处。然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低标准了。
王远不能忍受的倒不是他的粗,而是他对自己的忽视。忽视已经是客气的说法了,凭他来来去去、吆三喝四时眼神的游动方向,连余光散神都没落在王远身上,简直是“无视”!无视一个主动申请来“烂泥潭”实习的胸怀宽广的青年,无视一个已经小有名气、前途无量的优秀学员,无视一个可能给连队带来无限生机的大学生!
但肖遥对此嗤之以鼻。“收起你那套吧,优等生,”他说,“到任何一个新单位都得从头开始,夹起尾巴吧!”他自己倒不用夹尾巴,刚来不久连长听说他是学校里的足球明星,很积极地把他拉到自己房间去,以商谈军机的架势和他讨论了半天“光头连足球队”的建设问题,很快制订出了一个近乎半专业的训练计划。
修理连的指导员碰巧受命到一所军事院校参加政工培训了,家里就连长在。没有指导员的连队就像没有女人的家,少了些温馨气息,线条也粗了些。对于两个学员的到来,连长只在晚点名时提了一下——提的这一下也毫无精彩,像个老农民脱下旧布鞋磕磕磕地在床沿敲几下,掉了点鞋灰而已。没有想象中最起码的欢迎辞,没有哪怕是象征性的掌声,王远有点郁闷——郁闷在于,他自认不是俗人,为什么也要计较这些俗气的形式主义的东西!他甚至有些后悔,或许应该去个更加正规、更加像连队的连队。
在一次足球训练间隙,肖遥给连长递了支烟,有意无意地提起了王远,暗示他在学校是拔尖的人物,大有作为。连长面无表情地深深吸了一口烟,看着长长的烟灰像黯败的尾巴缀在亮丽的烟屁股上,倏地颓然落下。他忽然冷笑一声:“尖子?什么算尖子?什么尖子我没见过?”
不过之后连长确实给王远派了些活儿,当一当公差勤务人员的监工,负责组织一些政治学习之类的,算是看在肖遥面子上对“尖子”的器重。
只是他没想到“尖子”的另一重含义——代表锐气与倔强的,充满硬度与力度的,可以予人疼痛的。
2
有关代号“丛林风暴”的联合军演的消息,经历了风声、传闻、秘而不宣到摆上桌面的正常渠道,已经相当确凿了。对于这次军事演习最夸张的说法来自一个老兵,他无视保密规定的存在而声称将有八个国家的将军来现场观摩。谣言很快被攻破,一条更为可靠的信息将其做了修正,事实上是——号称集团军“巴顿将军”的新任军长将坐镇指挥。
和以前的演习一样,在正式动员之前,装甲团就以积极姿态展开了一系列热身运动。周五上午就将有一次拉动。按规定,全体人员要在号声响起时开始进入状态并采取行动,包括立即结束手头工作、迅速按战备要求收拾携行装备、小单位集合、跑步到大操场,全团在大操场集合后登车,统一出发。
吃过早饭后王远回到房间,发现他手下的兵全都提前进入了战备状态,一个个都在收拾东西,把被褥拼命塞进背囊里,脏兮兮的脸盆把水一泼,倒扣在被褥上,再一股脑儿地揉进雨衣、解放鞋……背囊吃力地一口一口吃进形状不同、味道各异的难消化的物品,像笨拙的孕妇一般胖了起来,撑得一身滚圆。兵们都很熟练,互相帮衬着,递递毛巾拉拉袋子,是修理连在足球场以外少有的火热场面。还有个脑子灵活的兵,已经把王远的背囊打开,带着毫不避讳的讨好意图替他们的实习排长收拾着装备。
“干什么?”王远警惕地问。他站在屋子中间,像个红色的大叉,确定地制止与批判着。
八个士兵中的七个都在一刹那间定住了,剩下的一个是姓余的班长,他拿定实习排长犯了健忘症,放出一脸“这不明摆着嘛”的亲切表情,然而已经忍不住掺了些轻蔑的成分。余班长说:“待会儿要拉动啊!排长你忘了?”
“号还没响就开始行动了?这是哪条规定的?你把条令翻给我看看?”王远不知不觉学习集训队熊队长的样子皱起了眉头,努力制造出成熟男人的外观,以免被这帮兵油子笑话——虽然修理连的兵们爱沉默,但他们的想法全摆在脸上,一看就透。所以王远看出来,他还是被笑话了。屋里忽然有了放松的气氛,似乎凭空有张嘴要笑要笑的。排长的青涩、稚嫩、经验短缺陡然增添了兵们的虚荣与自信。难怪部队最讲资历,腿脚浅了连底下人都不服的;话说回来,这资历也不是白讲的,至少余班长参加的拉动比实习排长多个几何倍数,如果上战场,说不定王远被打成筛子时,余班长还能全身而退呢。
基于这个理由,余班长认为自己最无私的做法是帮助年轻的排长适应实际情况,他忍住惯有的、对无知者的笑,没有计较王远的唐突与认真,以过来人的老到口吻向他传授通行于基层社会的秘笈:“不单我们连,哪个连都是事先准备的,一响号就整队出发,哪有时间收拾背囊?我们连在山上,路远吃亏,去得比别人晚了还挨过批评。”
王远树起一只手掌,做出个潇洒的制止手势,没有说话。沉默片刻,他往屋外走去,到门口又回转身来,说:“别的连我管不了,咱们连得按着规定来。”余班长气得一口气上不来,急促呼吸几下才大声说:“这是连长布置的任务!”王远从门边一气冲回来,到他面前,一字一顿地说:
“是连长让我布置的!一级对一级,我对连长负责,你们只需服从我的命令!——那个谁,你把我背囊里的东西也腾出来!”
说完甩头他就走。一下子,明亮、干净的屋子忽然像积满灰尘吊子的鬼屋,站了一屋的人都跟影子似的了,没了声音,没了轻重,没了着落。半晌,被唤作“那个谁”的兵一脸愤然地挤到余班长身边说:“他算老几啊?懂个屁!我们去问连长!”余班长目光低了低,声音也低下去了,然而话里满是突出的生硬——“听他的,一级对一级,我们只管服从就是了,越级反映情况——这罪名我可背不起!”
兵们——哪怕仅仅当了一年的兵——享受到了“经验”所带来的好处,他们完全正确地预测到了事情的发展与结局,甚至幸灾乐祸地偷听了连长对实习排长王远的训斥。转播这个场面的人拥有特别发达的表述能力,惟妙惟肖地模仿着两个不同身份、不同声音的人如何艰难对话——
连长说:我他妈没见过你这号的呆子!班长都跟你说了,都要提前做准备的,人家一到号响就跑步出发了,我们连倒好,号响才收拾东西!再天远地远地跑去集合!没听见团长怎么骂我吗?他说我服了你们光头连,真是样样剃光头啊!他大爷的!我没有要你争个第一啥啥啥的,你也不要让我丢脸行不行?
实习排长说:我们是按正规要求做的,问心无愧!别的连赶到前面了,他们是做假,真打起仗来做得了假吗?如果不按实战要求来,别说一个拉动,就是联合军演又有什么意义!
连长说:你这大道理跟我说什么呀?跟团长说去!
排长说:我会让团长知道的!
连长说:你?你才吃了几天军粮?你他妈以为你是谁呀——
……
不是哪次听壁脚都有这样丰厚的收获,兵们为此津津乐道了好几天,哪怕一个星期过去了,都还有人在茶余饭后的调侃中引用其经典语录。肖遥批评过两个做得明显过分的二年兵,又在班里旁敲侧击地提醒大家必须对上级(哪怕是资历很浅的)具有应有的尊重,但他还是难以完全排除遗留在自己心底的、兵们眼神中顽固的讥讽。
“你疯了?”晚上在僻静处他扭住王远的胳膊,“别做得那么不成熟好不好!来之前我们不是定好原则的吗——入乡随俗,合理变通,外圆内方,不走极端!”
王远抽回胳膊,抱了臂,盯着方寸尽失的死党,哧地笑了。
一周。
肖遥的目光慢慢聚集到白炽灯下王远那根明晃晃的食指上。王远以神秘莫测的笑容配合着这戏剧性的手势。他再一次加强了语气,重复了一遍这个关键的时间数字。
一周。
“我们将用一周时间进行实验,做一个他们观念中的排长——不管是好还是不好,都是他们觉得‘应该’的。”说话者把脸庞微微地、骄傲地抬起来,知道这番话不是所有人能都听明白,哪怕是死党肖遥。没有关系,这个理论实践性强,一旦付诸行动,那帮战士每个人都会感到无比熟悉。
“要让他们知道,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不愿意做成那个样子。”
实习排长王远手下的兵们犯糊涂了,他们弄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为他的情绪一点没有受到拉动事件的影响,好像他不是挨了连长批评反倒是戴了大红花,一脸红艳艳的、流光溢彩的生动。
但一切又来得那么自然而然。周五晚上看完《新闻联播》后王远叫住了一直不肯跟他说话的余班长,以熟稔的潇洒动作甩给他一支烟:“叫两个娃儿到活动室,打‘双抠’,老子犯瘾了。”余班长和周围几个听到这话的兵都在第一秒钟没有反应,第二秒钟余班长略带疑惑地看着王远,嘴上却是习惯性地答应了。在这里,基层干部口语里都把兵叫“娃儿”——带着家长口吻的,充满家庭氛围的,有种别样的亲切。既然让他叫两个“娃儿”打牌,那么,他余班长也是必须参加的,否则四人一桌的“双抠”就凑不齐人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