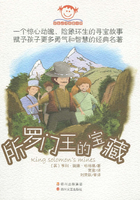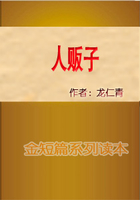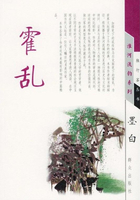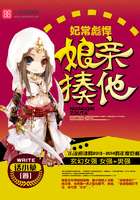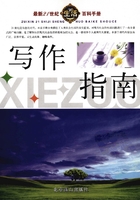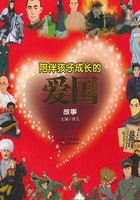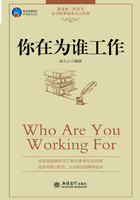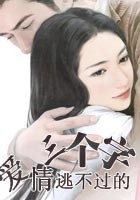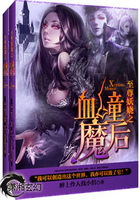二麻婆眼睛不大,但一笑起来,眼睛总是弯成一个弧度,好像把她眼里的人啊景啊都挤得变了形,有着别样的刺激。这样的眼睛水灵、招摇,风情万种,它注定会给一个女人带来俏丽的容貌与悲剧的人生。于是眼睛的主人从十几岁开始就麻烦不断,围绕着她的男孩与男人们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影子部队,虚虚实实、若隐若现地存在着,有种恶毒的说法是她十六岁那年就跟某家父子俩同时睡觉。坏名声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地降临,家里慌了,要把她弄去嫁人,但谁敢娶呢?哪怕长着滑嫩的脸蛋与弯弯的眼睛,流言蜚语像狗一样跟着你了,就一辈子都甩不掉。
她终于在二十六岁那年——在农村,这是很壮观的出嫁年纪——嫁给了杨家湾老说不上媳妇的屠永富。屠永富老娶不上老婆的原因在于他娘。永富他娘是寡妇,更是远近闻名的恶嘴婆,谁要踩了她一棵苗或拾了她树下的一枚果子,她一定会乐于将嗓音调高到广播站级别,用自己漫长人生里收藏的各种污秽词语去描绘对方。她的强悍形象很好地保护了自己与儿子,没人敢欺负这家孤儿寡母。村里人叫她“麻婆”,虽然她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粒雀斑,但憎恶使它们成为被放大的缺陷。新媳妇进门了,有关她的传闻也像嫁妆一样带了过来,令全村人亢奋——凶狠了一世的麻婆,最后讨到的儿媳妇不过是这样的角色,让人解恨啊!
大家根本不想知道新媳妇的名字,直接幸灾乐祸地叫她“二麻婆”——都是有污点的货。
水芹跟村里所有未婚女子一样,老早就得到过以二麻婆为负面典型的道德说教,这些教育不管是什么样的开头,结尾总是相同的:“不然,就跟二麻婆一样!”
跟二麻婆一样,名声坏了,只能找个有恶婆婆的人家。好像麻婆与二麻婆,是互为因果的——由于种了恶因,就只能得到恶果。一个女人是另一个女人的结果。多么奇怪的人生!
水芹就在那天,第一次走进了二麻婆的家。跨进大门的时候,老式的旧门板吱嘎一声,空气里的灰尘四下逃窜,水芹怔住了——扑面而来的竟然是一种熟稔的气氛,仿佛她上辈子就曾跨入过这道门,做过这家的主人。她坐在几乎暗无天日、仅靠屋顶上几块透明塑料瓦采光的堂屋里,吃着二麻婆递过来的一把苕干,喝着带点菜叶味的煮玉米水,很自然跟她聊起了家常,就好像她跟二麻婆是多年的相识一样。
“莫去河边了,”二麻婆吹了一下碗里的玉米水,忽然把眼皮搭拉下来,“那地方去多了,一心就想跳下去算了。”
水芹心里一沉,全身晃晃悠悠地麻起来。就好像在那一瞬间,她和二麻婆两位一体了。她们是紧紧相靠的硬币的两面。她们是血肉相通的连体人。她们是失散的孪生姐妹,终于相认。她们是同一种人。
没有哭。但水芹相信遥远的大山里,有自己的哭的回声。
促膝长谈的闺蜜画面是瞒不了人的。天晓得这两个相差十多岁的女人之间会有什么样的沟通话题,反正两人的交往在舆论监督下郑重开场。水芹往二麻婆家跑得勤了,一进那大院,她浅粉色的塑料凉鞋后面就跟上了二麻婆家的黑花狗,再后面跟上的是半村子的冷眉冷眼、半村子的闲言碎语。村里人虽然对水芹有看法,但界定很明显——她只是喜欢把自己收拾得花花朵朵的,说话带点洋里洋腔,笑起来飘着些浮浪,但这不能说明本质。而现在,花花朵朵要一头栽进粪坑,怕是连表面的光鲜也没有了,沤成了肥,跟屎没两样。
一个傍晚,水芹在家门口让半截砖头一绊,趔趄了一下,差点摔跤。等她站起身来,看到大姐水英立在院门口,两腿张着,两手叉腰,像个草书的“大”字。这个“大”字冷着脸,要是脸上那道剑眉横过来又提上去,活脱是个“天”字了。
还真把自己当天了!水芹在心里吐着唾沫:呸,呸!
天字号的水英挡着门,代表门里所有人问:“从哪里回来?”
水芹想说“学校”,但看水英的样子,答案是写在她脸上的。水芹恨恨地瞪了大姐一眼,用沉默抗拒着。她预备着水英要来一番长篇大论的训斥,但她真是小看大姐了——这个落榜的复读生,哪怕落一万次榜也落不了屠广福家长女的架子,她总有一天会飞出穷山沟,她已经为此做好了一切思想准备与理论武装。
“看看这道门,”水英说,“它是屠家的脸!这张脸不好看,但是不长麻子!”
水英的眼睛瞪得像庙里的金刚,也和金刚一样高高在上地立在门槛上,以凛然的架势俯视水芹。这是她历来的姿态,她用这种姿态占据着水芹对大姐的所有印象空间。水芹出奇安静地竖在下风口,抬起湿沉沉的眼皮扫了大姐一眼,那一秒钟产生了错觉——好像看到七岁的水英坐在摇篮边轻轻唱着山歌,慢悠悠的,拍子总是缓下一截,想唱到哪儿歇就在哪儿歇似的。这画面是水英告诉她的,也许只说了一次,却牢牢吸在水芹脑子里,想忘也忘不掉。水芹忽然突破年龄的界限,用三十岁女人的表情苦笑了一下!
“何苦呢屠水英,”三十岁的水芹痛楚地说,“真是何苦呢……”
结论:长大了。
这是水芹和二麻婆坐在光线混乱的灶屋里,经过一顿饭工夫的讨论后,得出的唯一结论。为加强效果,二麻婆还坚定地点了点头,她光滑的脸庞在灶火映照下霞光溢彩,嘴角挂上了一丝斜斜的嘲讽——这个表情总是斜斜地挂着,像颗美人痣一样成为她的标志。
七岁的水英会心疼一岁的水芹,因为是姊妹;十年后的水英却再也不会心疼妹妹了,因为水芹无可挽回地长大,女大十八变,变得俊俏,变得伶俐,变得众目所瞩——那她就再也不是妹妹,而是女人,是其他女人的竞争者。姐妹总是互为参照,她是水英的对立面了,她的俊俏像锋利的刀,无声地刺向老气横秋的水英,水英只有用克己、努力来抵抗——多么艰难的抵抗!她们变成了敌人,太正常不过了,天底下的女人与女人,不都是敌人?
水芹忽然冲二麻婆一笑,眼里有了波光,她柔柔地把头倚靠在二麻婆肩上。水芹只想无声地告诉她,天底下的女人都是敌人,唯独她们不是。她们是一样的人。她们漂亮。她们招惹男人。她们是其他女人的眼中钉肉中刺。钉子与钉子、刺与刺之间,也会是敌人吗?当然不会。
钉子和刺们都有近身的威胁,水芹的天敌是水英,二麻婆的天敌是麻婆。
如人们所料,麻婆与二麻婆的相处过程充满乡村情调的观赏性。屠永富长年在外面打工不回来,家里就剩着两个唱对台戏的女人。最初的一段,二麻婆肯定是要受受气的,新过门么,谁不攒点舆论分。通常的情况是:二麻婆做了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往往是喂了猪忘了关栅栏门啊、炒菜时油放多了不够节俭啊),麻婆就抖落出十二分精神,站到院坝里开始骂人。她骂的当然是二麻婆,但人家多么会用词啊,说骂的是“那个睡千人垫万床的”,说永富家要不是孤儿寡母哪会受人欺负,不受人欺负哪会轮上娶这种烂货进门,烂货进了门不低着头走道反倒还要给她吃咸得熏人的菜,存心想把她这老婆子用盐毒死,末了还要让“下头”的死鬼男人睁个眼看一看,她都过的什么日子……二麻婆嫁来之前就有人提醒她得“学会打滚”,因为她未来的婆婆一哭闹起来,可是随时随处都能一坐二躺、满地打滚的。
“跟个牲口似的!”二麻婆说起她,斜斜的嘲讽又挂上嘴角来。
但二麻婆没有掌握打滚的技巧就进了麻婆家的门,就像还没背课文就要参加考试、还没学会拼刺刀就被拉到战场上一样。她不需要背课本和拼刺刀,在男人堆里混出来的女人知道什么叫四两拨千斤。
二麻婆先尽着麻婆去闹,随她怎么说,反正二麻婆的坏名声又不是才起头的。大约一年半之后,一个利利索索的清晨,二麻婆做早饭时,以一个漂亮的手势,在干饭里浇上了昨晚吃剩下的半碗菜汤。在屠永富家众多的规矩里,关于早饭的一条是绝对不能是稀的,麻婆认为早上吃了稀的,一上午干活都会没力气。把干饭变成了汤泡饭,二麻婆简直翻了天了!
果然,麻婆走到饭桌前,第一眼瞟过饭碗,第二眼便狠狠瞪向二麻婆——后者正若无其事地站在桌边夹着咸菜——麻婆二话不说,把脚下的凳子一踢,径直走到院坝里,一屁股坐到地上,拢拢双腿,替它们找了个舒服角度,又深深地咽了一口口水——全部准备工作就绪,架势已拉开。
“头上三尺有青天啊——”每次开场都是这句,霎时便把舞台无限扩大了,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是活灵灵的一个麻婆,显得既是气势上的凛然正义,又是视觉上的孤立无援。
但三尺青天之下的麻婆,这一天注定是个失败者。她刚刚起了个头,调准了音,却蓦地抬头看到儿媳妇已经跟腿到了,高高地、挑衅般地立在她眼前。没等麻婆唱出第二句,二麻婆忽然俯下身子凑到麻婆耳边,轻轻说了句什么,不慌不忙的,那样子像是跟自己娘家母说着体己的话儿——麻婆的脸色就变了。
二麻婆说完,直起身,扭着腰肢风调雨顺地走进了屋里。留下麻婆在院坝里坐着,她仇恨的眼光像蛇一样尾随儿媳妇进了屋,却怎么也没办法咬她一口。麻婆哑了,枯坐良久,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第一次安安静静地撤退了。
麻婆就这样被治住了。以后有再大的事,她就算是和儿媳吵架、赌气甚至摔摔碗碟,却再也不敢到院坝里扯开嗓门邀请全村人来收听她的控诉了。
“是句什么灵验的话呢?倒也教教我来!”水芹一直追问着,二麻婆只是笑,她说这话只能说给麻婆听,传开了,就跟药品过了期似的,味儿都散了,哪还能治人呢。
三
“水芹回来了?”水英气乎乎的。
她一回来径直就朝屋里走,把旅行包掀下来重重往墙角一扔!妈赶快把两岁的兵娃放到地上,一面说“脏!脏!”一面抢着把旅行包拾起来,拍拍灰,小心放到堂屋中央的桌子上。印了英文字母的旅行包是水英上大学时给买的,家里最好的一个包。
“她回来了?”水英瞪着眼。
妈重新抱起兵娃,避重就轻地叹口气:“回了。”没有要解释的意思。不过又有什么好解释的呢?
看妈的反应,是打算装傻,把水芹当成最正常不过的出嫁后回娘家的女儿看待。彼此心知肚明,只要把面上糊里糊涂地应付过去就行了。
那是不公平的!水英心里说。一视同仁,对于恪守道德规范、维护家庭尊严的其他女儿来说,是一种侮辱,一种损害。
“她听说水芬今年要回来过年……”妈说了这句,忽然把话头打住,知道没说对话。她掩饰地抓起兵娃的小手亲了亲,仿佛那只小手可以替她遮挡一下难堪。
因为水芬,只是因为水芬!三姊妹里就数水芬最能团结人。她说话不多又能干活,爸妈喜欢她;她性情温和、不争不抢,姐妹关系自然也处得好。水芬初中没念完,有一年跟着屠丽娜家一个陌生的远房“孃孃”去打工,这一走就跟吹口气似的,生生没了消息——直到一年后才收到她写来的信,她被卖到河北一户农家,已经生了儿子。水芬回来过一次,大他十多岁的男人跟着——带着点防范的意思,怕她一回娘家就滞留不走了。其实,水芬的性子就是那样的,你把她往哪块地里种,她就会长出哪块地的苗。她和所有出嫁的女儿一样,回家是回家,但已经是出嫁的心态,走的时候一点没打磕巴——不过看得出来,夫家虽是出钱买的媳妇,待她还是不错的。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打着水芬回家的旗号,水芹回来过年,简直是又一把扎向水英心里的刀!这不光是明的驳她水英这个老大的面子,宣告她统治的失败,更是专挑屠家的弱处下手——水英上大学,她没有回来;妈生兵娃,她没有回来,有喜事她都不愿沾边,偏偏水芬是给拐走嫁人的,她就要回来!她成心要在屠家隐痛处出现!
“她回来不好好待着,又到哪条脏路上去踩烂泥了?”水英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平时性子是蛮温和的,但只要一提到水芹,她攒了八辈子的火爆脾气都给点着了。
“你看你,”妈妈说,“家里院墙旧了,我说等你爸回来要重新刷墙,她就说去供销社看看有没有刷墙的涂料。”
不知道什么时候,和水英水火不容的水芹已经在院门口站定了,她扶着的蓝色自行车像是一匹威风的战马,衬得她的表情也是战士般的严肃。她是做好了相当的心理准备,可是在她停了自行车、跨进屋来的第一个瞬间,她仍没有料到大姐的火力会那么强劲。
“水芬还没回来呢,”大学二年级的高材生屠水英无不讽刺地说,“陈志军回来了?”
水芹咬紧了嘴唇。
四
第一次见到陈志军,也是在二麻婆家。
十九岁的陈志军跟着他叔舅公九贵来麻婆家串门,老的捧着一罐土法酿的“青纱醉”,小的则拎着两条新鲜的黑头鱼,二麻婆迎出去时笑得晴空万里,边把他们让进屋边说:“妈又去东头打麻将三个钟了,也该回来了。”
坐在堂屋的水芹见来了客人,忙起身要走,二麻婆一把拉住她,说:“是镇上‘朝天门’的掌门人呢,你躲啥?”说成“躲”,水芹倒不好坚持了,不然坐实了她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女子。她只好抬头故作大方地说:“‘朝天门’谁不知道呀,我还去买过文具。”
“朝天门”是镇上最大的一家杂货铺,东西多,还新鲜,好多村里人都是在那里了解城里的时髦新动向的。
九贵笑眯眯地说:“是不是啊?你来的时候多半我不在铺子里,不然我肯定会记得你。”二麻婆水灵灵地睃他一眼,笑道:“个老色鬼!还不服老哇!”其实“朝天门”是陈志军父母开的,九贵算不上掌门人,他充其量是个打杂的,但他长期往各个村子跑腿送货,和女子姨婶们混得熟了,嘴上自然没遮没拦。
倒是陈志军不声不响,一直抿嘴笑着立在原地。他不是腼腆、认生,而是漫不经心,仿佛这些场面上的事情都见惯不惊了,不值得费神去应酬。他慵懒的眼神像没拧干的抹布,拖泥带水的,迟钝地抹过来抹过去,但还是在水芹身上定住了一下。抹开了,又回头定一下,水芹就有点飘了。
水芹问他:“你的鱼是自己捕的么?”
这就故意了。明明知道镇上离河道远,而陈志军又穿得一身齐崭,哪会是他亲自捕的呢,但不找个近便的话题就不好进一步交流,让人看出点用心来也无伤大雅。水芹的故意是带着娇嗔的。
果然陈志军开口了,他认真地吸吸鼻子说:“我哪会捕鱼?是我拿一个玩具跟人家换的——还是个新款的变形金刚呢!”
一屋的人撑不住都笑起来,笑声里要数水芹的声音最脆响,像灶膛里哔哔啵啵的烧柴声里总有啪啪炸开的小火星。
那不过是个普通的开头,一个用变形金刚换黑鱼的年轻人不可能得到水芹的特别注意。后来她在二麻婆家又见过九贵几次,陈志军倒来得很少。谁也不知道,危险的气息从那时起已经渐渐逼近了,水芹却什么也没有觉察——要怪她贪玩,都上初三了还不惦记功课,好多同学都在为考上高中而起早摸黑地看书、做题,水芹倒好,动不动把水英当个失败典型,觉得读完高中又怎么样,考不上大学还成个笑话。她照样常往二麻婆家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