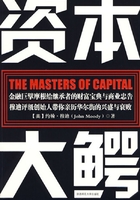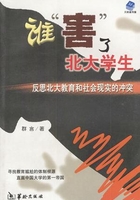灯亮了一夜,早晨妻子推醒编剧,说那灯光刺得她半宿睡不着……妻子还想说什么,却没有说下去。编剧爱妻子,执意要搬到仓房里写悲剧。妻子哼了一声,任凭编剧一个人搬去了。
从此仓房的灯光长久不熄。悲剧在发展。编剧同主人公产生了共鸣,写作进了疯狂状态。妻子说他经常不回去睡她好怕。编剧说,就要完成了。妻子本想唤编剧去睡,话含在嘴边,又咽回去了。
编剧把主人公悲剧的高潮放在结尾部分,可恰在这时思路断了。编剧想把结局写出悲壮美。
放下笔,编剧步出仓房,向家里走去。编剧刚要按门铃时突然想,现在是午夜,妻子一定睡了。不能吵醒她。编剧就掏出了钥匙。编剧轻手轻脚地走进卧室。妻子和另一个男人睡在一起!
妻子泪流满面,跪在编剧面前,那男人抖着身子站在旁边。
编剧却旁若无人地坐在写字台前,操起笔铺开稿纸,悲剧的结局就沿着笔尖倾泻下来。
编剧进人了创作的最佳状态:无。无我。无他。无她。
草坪上的石雕
平日里,肌在窗口看草坪上那个赤裸着粗壮臂膀的沉思者往往是白露打发白天的主要方式,这石间雕的玩意儿有时令白露产生小小的激动。
这天白露先把那男人买来的衣服搬出来统统试了一遍,企图通过穿衣镜发现自己的新形象,可白露没发现新奇的东西。于是白露放弃了那与堆各种各样的纺织品,而开始摆弄室内的摆设,不顺眼的过时的大半被花扔在地板上或扔出窗去。
白露将自己的放大像也扔到窗外去了。她最初并没有意识到扔的是谈什么,只是想扔点什么,那东西啪的一声摔响,她开始有点后悔。放大像摔在草坪中的石雕像一沉思者身上了。玻璃罩摔成碎片,图片在那结实的肩头吻了一下便飞落在甬路上。白露望着便有点激动。
恰恰这时有个穿牛仔服的高大男孩进人白露的视线。大男孩拾起了甬路上亮闪闪的图片。白露揉了揉眼睛。看得出大男孩被图片上美丽的家伙打动了,他用衣袖轻轻拭了拭图片。白露的脸便一阵火热,红了,如同那衣袖拂在自己脸上。大男孩收起图片向楼上张望,白露便缩回头。此后白露只顾在床上喘气。
第二天白露守在窗口看沉思者,却看见大男孩。白露有点怀疑自己守在窗口究竟是为了谁。白露这次狠狠地自己留在窗口,但是把视线转向远处一座大厦。她男人是那大厦的总经理。那男人玩别的女人去了,几天不露面。白露想重新寻找视觉对象。她还是选择了草坪上的沉思者。大男孩也在沉思,那体态同石雕像一样,白露想象了一下他赤裸时的样子,便一阵心慌。
白露无法明确刚才是否挥动了手臂,或许挥了或许没有,白露回忆着。大男孩明显注意到她的动作了,犹豫了几秒钟,然后挺了挺胸晃着宽大的双肩向她的别墅走来了。白露开始喘粗气。这时白露看见远处的大厦,并想象着那辆黑色轿车奔驰过来。要发生大地震了!楼下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白露大吃一惊,慌忙跑下楼去,拽过一张桌子把楼门顶死了。接着她感到门被人轻推了一下然后是没有声响,几秒钟后脚步声远去了。许久,白露打开楼门。门外台阶上躺着自己的相片。
那晚她男人来了,问:你今天怎么没激情?白露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白露说话时好像有个粗壮的沉思者在眼前一闪,身旁的男人便无比瘦小可怜了。
遭遇老鼠
他同她办完离婚手续就准备跟那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结婚了。她哭起来。同事劝她,莫哭。男人多半这样,生活苦时守着老婆,一发迹就另寻新欢。这种事多了。她还是哭。
天气也要大哭一场了。天气预报说要下几天,必须准备防洪呢。好一对狗男女,洪水冲跨你们的窝!她心情痛快了些。站在大坝上,心情不坏。那儿太危险!同来察看水情的人在远处提醒她。
她没在乎。她与别人不同。她感激这洪水呢。她心里诅咒着:再大久些,再猛些,冲跨他们的窝!突然,风吹来,她脚下一滑,滑到洪水中去了……她呛了口水,就晕过去了。她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汪水,加人到洪水中一道冲垮了他和那个年轻漂亮女人的窝:冰箱、彩电,还有崭新的结婚照。她感到快意。
懵懂中,她碰到了硬邦邦的东西。她迅速地提醒自己:抓住。抓住这棵生命之树!
她抓到了。在抓到树那瞬间她感到自己从洪水中分离出来。她不再是一汪水,而是水的对立物:水要把她冲向死神。她要摆脱水的挟持,爬出去。她死死抓住那件东西,并努力爬上去,这样肩和头都完全露出了水面。她能看见四周全是汪洋。她不敢看了,想闭上眼睛。这时她明白,自己正抓着一棵树。她想看看这棵树还能维持多久。老鼠!
一只老鼠也在死死抱住这棵树!老鼠是她平生最讨厌的动物。说不出为什么,就是讨厌,讨厌透了。那时他和她都住乡下。乡下少的是粮食,多的是老鼠。她常吓得拱进他怀里,从此他们共同对付老鼠……他们的恋情是从对付老鼠开始的。
树上的老鼠悲伤地望了望她,眼神里饱含绝望。按说她讨厌的老鼠能有今天她应该高兴,可是她没有。四周一片汪洋,她在这片汪洋中显得同样渺小无力。一棵生命之树把她们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她们同步体验着生存的危机,她们同步在死神怀抱中挣扎。茫茫洪水中与它在一起,她感到的是亲切。
喂!一定抓住,坚持到最后!
她听见人的声音。一艘汽艇向她开来了。她激动得差点松开那棵树。与救援的手向她伸来,抓住了她。这一瞬她又亲切地看见了那只同命相怜的老鼠。老鼠也正望着她,目光中透射出乞求。她慌乱中把手伸向那只老鼠。她们刚离开,那棵树就被洪水吞没了。
医院的病床上,她伸了一个懒腰,惊险的记忆渐渐远去。突然她感到手中攥着一个湿漉漉的东西,很不舒服。她松开手……啊?老鼠!
她浑身起了疙瘩,尖叫一声,那只水淋淋、脏兮兮的老鼠抖落在床上。老鼠也吃了一惊,然后得意的看了她一下,跳下床,出去了。护士听到她的惊叫,跑进来,问她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哪儿都不舒服!恶心的老鼠!她全身抖着,感到浑身发冷。嘻!那可是你从洪水中救上来的,要不是你执意带进医院……她茫然地说,是吗……
洪水消退后他和那个年轻漂亮女人重新操办婚事。那可是个很好的天儿。有一阵她又禁不住想起那只老鼠。忽然她觉得,我不就是那只被自己抖落在地上的老鼠吗!
想罢,她又有点不舒服。
玫瑰梦
画家本人的生命与他的艺术生命是同步的。当画家连续几天只能提着笔茫然面对画布的时候,画家意识到自己的艺术生命走到了尽头。这天,画家的笔抖落在画布上。画家的手苍老无力了。画家倒在床上,懵懂中画家似乎嗅到了缕缕的玫瑰幽香。可是画家明白这玫瑰对他来说将是遥遥无期的。现在陪伴他的只是一只虎皮鹦鹉。
在画家过去辉煌的艺术生涯中与玫瑰曾有着一段不可分割的缘分。花也正是这玫瑰使画家的艺术生命出现蓬勃绿意。
那是一个崇拜画家的女孩,在一个亮丽的早晨给画家寄来了第一朵谈玫瑰。这是当年画家孤独艺术生涯中收到的第一个认同。从此每周都有了一朵玫瑰从千里之外寄到画家手中。当画家懈怠下去懒于着墨时,当画家准备移情别恋于物化的世界时,都是一朵飘然而至的玫瑰唤起画家对绘画艺术的疯狂并使他又回归艺术。
为此,画家陆续创作出一系列上乘的画作,画家渐渐地为公众所认同……
可是乐观的情形终于发生了变化,他的崇拜者们对绘画艺术一天天淡漠下去。转眼一周过去了,画家没有收到千里之外寄来的玫瑰。虎皮鹦鵡也表现得焦虑万分。后来画家收到了女孩寄来的一个名片。原来女孩已因为不说也罢的原因变成了女人,并且做了某公司公关部的部长,每天处于机构的忙碌之中。由于疏于侍弄,她的那些玫瑰都凋谢了……
画家惊姥、悲伤、疯狂。无数朵玫瑰从画家的窗子中扬出去,飘落满地。然后画家呆坐在面市前。
这一天虎皮鹦鹉竟说话了。这是画家没料到的。以前画家以为这是没做过手术的那种不能说话的鹦鹉:为什么,为什么?鹦鹉问。因为玫瑰,玫瑰凋谢了。画家说。
画家说着从床上坐起来,走向鹦鵡。画家觉得这么多年委屈了它,现在应该还它自由了。外面的天空比这乏味的斗室宽广自在。奇怪的是虎皮鹦鶴并没有飞出窗子。它站在了挂钩上,抖了抖一身斑斓的虎皮,与望着画家。
第二天早上,微风从窗外徐来,一股玫瑰的幽香飘进来。画家睁开眼睛。原来窗台上躺着一枝玫瑰。阳光斜射进来,玫瑰放射出鲜艳的谈异彩。
画家从床上坐起来,苍老的生命中又注入一丝生机。连续两天画家的窗口都躺着一枝玫瑰。画家说不清这玫瑰的来历,但画家感到自己窒息的生命有了些许的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