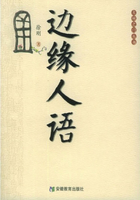1967.5.12
再次讨论进点如何办。“支左”从来没有人干过,加之七机部是搞科研尖端的,915、916又是全国闻名的两大派,最不好搞。根据中央关于军事管制的文件、周总理的指示以及听到的“支左”经验教训的介绍,经军管人员反复讨论,基本上统一了几条……
1967.5.19
见面会由军管会主持召开,干部和915、916两派群众共一万多人参加。在一个广场中间用石灰划出一米宽的界沟,东边915,西边916,两派人员互不过线,军管人员在界沟内监督。会由我主持,我讲话,首先宣读上面命令,我是三院军管会主任。接着讲话时,有一派的几个人上台,将我话筒夺走,接着又一群人将两旁高音喇叭拉走,中间挂的毛主席大像,也被拆走了,他们那派的队伍也带出了会场,他们派的头头也找不着了。但另一派不退场,整整齐齐坐着在唱歌。此时,我们一面派人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打电话请示,无人接。一面军管会开会研究,会开还是不开,经大家研究认为:会必须继续开。
1967.11.9
从部直跑到一院。一院军管会贺主任汇报大联合情况,915还有二十多人打得不敢回来,916的一些爱打的青年在奶牛场集训,还收点效。但六厂一处天天都有打人的人,也有被人打伤的。经常有小武斗。看来三院比一院离京城远一点,好得多。七机部知识分子多,真打也不见得能打出个结果。
1968.1.24
国防工办军管小组负责人陈××批评我们七机部,说七机部抓516,核心人物你一个未动,不理解。好像我与516有什么关系。他讲话我光听,不吭声。我有我的老经验,毛主席说过错杀人,二十年后还要昭雪。我未弄清谁是516,我是不会乱抓人的。近日又谣传什么七机部不抓516,七机部是516的窝子,516的核心在七机部。什么农村包围城市,什么中国人民党,什么东北人民党,什么××组织十二个常委有六个在七机部,两个人民党都有三个头头在七机部等等。乱七八糟。上面除周总理外没有人说一句好话。难办,难办。近日武斗又多起来,谣传不管它,自己军管人员不能不提高警惕。
1968.6.8
中午南苑915、916两派发生大武斗,有上万人。703所所长姚桐斌被915殴打致死。前去制止,又无法接近,也无法弄清情况。天气热,打得也火热,想忙于制止,又制止不了。
1968.6.12
召集915、916两派头头开会,张翼翔主任参加。研究制止南苑发生的6.8武斗和姚的尸体解剖问题。经耐心做工作,两派共同商定了六条:(1)疏散人员;(2)双方人员撤出武斗现场;(3)食堂开饭;(4)211医院拿出整改措施;(5)发工资;(6)双方交出武斗工具,集中起来由军管会处理。
军管会还规定了五条:(1)群众各回原单位。由军管组织学习:(2)721、731医院都要按十条执行;(3)伤员生命垂危,允许家属探望。双方扣的人交军管会,保证安全;(4)带头抄家、冲医院的人,要揪出来;(5)组成执行协议、制止武斗监督小组,各派三人,两派总部各一人。为制止武斗,总算达成了一个协议……
最后,公安局的法医解剖验尸完后作出初步结论:姚桐斌同志是钝器伤头致死。
——(《天涯》2000年第5期)
姚桐斌就是在制止两派武斗时被打死的。
搞尖端武器的科技人员打起来,似乎并不比使锄头、扁担的农民心慈手软。据说,有人朝他阴部猛踢一脚,又有两个家伙举起铁棍向他头部猛烈击去……
此时,中国到哪里去找一张可以安静读些书的桌子,一盏能够俯首橘黄色的光晕下专心科研的明灯?
此时,国人中还有多少人不在发烧谵妄,心里存有一片清风明月,还能独善其身?
由“文革”,我们可以发现,在许多老知识分子那里,他们对于国家和事业的全副身心的挚爱,具有亡命决绝的性质。这即是说,当他们确信国家已成了一辆疯狂的战车在向悬崖奔去,事业已被一头红眼的斗牛撞成满地碎片的瓷器店,他们学不会苟且,他们绝不会偷生,他们只能告别这个世界了!
……姚桐斌之死,对赵九章与其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莫如说是一个绝望的信号,一个微妙的暗示。
姚桐斌死后的几天时间里,他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吃不喝,不言不语,甚至整夜不睡。如果说在姚桐斌死之前,他对眼前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多少还抱有一种幻想,心中还默默燃烧着一盏希望的灯火,那么姚桐斌死后,他的这种幻想消失了,心中那盏本来就不明亮的灯火,也开始变得暗淡微弱了。
……每晚夜幕降临,他便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从未有过的恐惧感,直至深夜,他也无法入睡。一合上眼,街头巷尾、门前楼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便像雪花般飞来,每一张大字报上,他都仿佛看见写着两个血淋淋的大字:吃人!
1968年10月10日晚,赵九章独自一入伏在走廊里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份检查。
时针已指向两点。赵九章工工整整写完最后一份检查的最后一个字,起身走进属于自己的卧室,刷了牙,洗了脸,烫了脚,做完平常每晚睡觉前该做的一切,然后再翻身上床。接着,他轻轻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纸包,把平时一粒一粒攒下的几十粒安眠药全部倒进嘴里,这才静静地躺在了床上……
——(李鸣生《赵九章之死》2004年8月16日《文汇报》)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这是赵九章生前常爱吟诵的诗句。
仿佛这诗句成了谶语,他的命运真是“壮士不还”——遗体,不知在哪里火化;在深秋萧瑟的寒风中,他的骨灰也不知飘向了何方。
1978年,赵九章得以昭雪平反,恢复名誉。
八宝山革命公墓里,多出了一只罕见的没有尸骨的骨灰盒。
赵九章自杀后,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将军打电话向周恩来作了报告。放下电话,周恩来清癯且多有老人斑的脸上,缓缓地蒙上一层泪影,恍如一个沉暗的陶器上了一道釉光……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周总理当时表情非常悲痛。他显然有亡羊补牢的意思,派出专人去中国科学院进行追查与调查。
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已经达到二十人。
“文革”不但发轫于像北京、上海这样国内最现代化的城市,而且,它的一幕幕云诡波谲的高潮,也在这些城市上演。越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越是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密集的单位,对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响应,越是强烈;对其“路线斗争”的说辞,也越是顶真。
这不禁令人回想起欧洲早期的革命运动,激进派以清教徒形式出现的狂热而又系统的政治运动,特别盛行于“无主的自由人”中,这些“无主的自由人”,并不是下层群众,而多半是绅士和商人……
1967年至1968年里,在中国科学院和七机部及下属单位,革命的大潮如火如荼,它有一种“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气势,不说是一切,但肯定是将绝大多数人们裹挟了进来。
复杂的社会动因,复杂的心理动因。此外,上有高层策略的迤逦变幻,下有藏在扇扇重门后摇动的鹅毛扇子……这决不像大幕落下后将一切罪责推在“造反派”身上那么简单。
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的整个研制工作,大部分是在“文革”最动乱的年月里进行的。唯一庆幸的是,物是人非,沉舟侧畔,卫星的试制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1967年7月,正在忙于导弹设计、时任国防部五院导弹总体设计部副主任的孙家栋接到通知,为确保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不陷于停顿,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钱学森推荐孙家栋担任总体设计。
孙家栋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去七机部挑选干才。“915”、“916”两大派内斗之烈,结怨之深,让带兵打仗的杨国宇将军都头皮发炸。孙家栋却没有使这回挑选变成一部鸡飞狗跳的历险记。在全面了解和分析卫星研制情况的基础上,他在七机部上上下下跑了两个多月,详细考察了各部门有特长的技术骨干。他并不想一碗水端平,而是一切以搞卫星需要为标准,从中挑选出18人。他们个个是攻坚执锐的精兵,人人是埋头干活的好手,日后被赞誉为“航天十八勇士”。
有意思的是,在路线斗争上打得天地玄黄的两大派,对于孙家栋挑中的人选均无异议。
事后,钱学森对孙家栋有过一句评语:“看来,把孙家栋找来还是对的,他的确敢干事,会干事。”
1967年12月,孙家栋主持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工作会议,审定了总体方案和各系统方案,以及技术方案的重新论证工作。
鉴于法国已发射了人造卫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发射卫星的国家,邻国的日本也在紧锣密鼓加快准备;而以当时我国的国情、技术基础、工业水平与技术指标,按1965年的卫星设计方案,发射还需要很长时间;这种局面,促使我国第一颗卫星首先得是一颗政治卫星,即简化过去的方案,去掉卫星上的很多探测仪器,不追求高难技术,只要做到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就是成功。
用许多年后孙家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种简化,是把一辆汽车变成了平板车。
当年这种话,孙家栋是绝对不敢说的。怎么能将充分展示“文革”伟大成果、象征着毛泽东思想经天纬地、光芒万丈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说成是粗街陋巷上贩夫走卒谁都可以拉的“平板车”呢?
上得去,便是发射成功。抓得住,即是准确入轨。难就难在看得见、听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