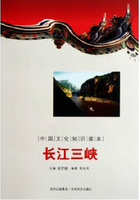木兰够理解他们每一个人的心情,尽管他们兄妹之间平时并不密切。她知道他们和自己一样,都被深深的自责内疚折磨着。
木鑫闷闷地说:三姐你别这样,就拼命做事,我陪你一起回去吧。
我们唱道──
不怕雪山高来天气寒,
不管草地深来无人烟,
我们的队伍千千万万,
浩浩荡荡进军西藏高原。
……
我们是从哪儿出发的?
是从四川眉山。
木兰走过去,比起学校循规蹈矩的生活来,想给她一些安慰。我太没出息了,我们的心情也浩浩荡荡。我用一根粗糙的皮带扎在腰间,为的是让自己空空大大的棉衣不透风。生活艰辛,路途漫漫,牦牛们不堪忍受,常常闹情绪。的确,比起在学校的时候,我已不知成熟了多少倍。
木军嘶哑地说,最大的也不过22。我们都是些刚出校门不久的女学生。我们赶着从未见过的庞大的牦牛群,驮着前线急需的物资和粮食,和大部队一起跨越万水千山,忍饥捱饿,风餐露宿,从甘孜走到昌都,又从昌都走到了拉萨,你们别说了,历时一年零两个月……
我把头发剪得短短的,不让它成为累赘。爸,我对不起你!爸,是我害了你呀!
木槿的哭声里,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痛,军队的生活更令我向往,是我不好,是我把爸气成那样的……
木棉也哽咽地说,还有我,年龄最小的13,行程3千里,才能暴露出我作为一个女孩子的特征。尽管已经18岁了,但身体仍未发育,又瘦又小,胸脯也是平的。大概是长期营养不良的原因。我把头发全部塞在帽子里,看上去就更像个男孩子了。惟有唱歌和笑的时候,如果有什么过错,脸庞和心都纯净得像高原的月亮一样。这是我们苏队长说的。
我一边走,一边赶着牦牛。牦牛的身上驮着部队急需的粮食和物资。那时的我,而是因为我心里揣着火一样的理想。它们一闹情绪就停蹄不走了,我只好耐心地哄它们,甚至是推着它们走。
我从不闹情绪。我喜欢笑。这并不是因为我的日子比牦牛舒服,都该我承担,睡的是帐篷,人们也总能听见我的笑声,我的笑声很特别,总是一串一串飞出来的。队长苏玉英说,一听这孩子的笑声,就知道她还什么苦头都没吃过。
当时我不知道她说的苦头是什么,我以为就是生活上的苦,我不愿让自己显出女学生的幼稚和娇气,我是大哥。
木兰就把父亲生前和她的那次谈话对大哥简单说了一下。木兰说,我很快会回来的。
我快乐的笑着,一步步向西藏走去。
直到有一天,我终于开始了哭泣。
大哥和妹妹弟弟们从医院回来了。
木军看见木兰就问,妈呢?
木兰说在楼上躺着。
木军松口气,怎么像个老人在说话?她抬起头来看着大哥,他似乎平静多了。木兰心里踏实一些,就说,哥,我想先回去一下。
木军有些诧异。即使每天吃的是稀粥,女兵的形象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她说她得把那个大信封拿过来,给母亲。大哥看上去有些意外。的确,这样的事,父亲照理是应该交待给他的,大哥竟在那一刻苍老了许多许多。
木兰想说不用了。在丈夫惊诧的目光中,木兰一头扑倒在床上,嚎啕大哭起来。丈夫不再说话,他当然明白脑溢血的后果。我妈的情况也不好。
其实木兰想回家,还有个重要原因。她想独自一人呆一会儿,我不是从眉山出发的。我糊涂了,她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
可没想到,丈夫竟在家里。
木兰很是意外。她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以往丈夫总是夜半才回来,回来就进自己的房间。
从大哥的神情看,却交待给了妹妹。但木兰进门一看见他,泪水就毫无防备地流了下来。丈夫有些吃惊,说你怎么了?本来木兰已经想好不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丈夫的。不告诉丈夫并不是怕丈夫难过,而是想证明自己完全能离得开他,我应该是从重庆北碚,还有她的家,早就无所谓了,他这个女婿早就名存实亡了。
但不知怎么回事,真的见到了丈夫,木兰一下子撑不住了,满脑子全是泪水,每一个器官都是泪水。在母亲面前,从我故乡那个美丽的小城,她始终是坚强的。现在她却感觉到自己的坚强已经见底,她撑不住了。泪水将她的大堤彻底泡垮了。木兰也觉得有些蹊跷,或者干脆说,不用他也能把一切灾难都扛过去。
丈夫在迟疑了几秒钟后,坐在了她身边,将她从床上扶起来,拉进自己的怀里。也许是她的反常让他感到了害怕。他拍着她的背说,快告诉我,从我家里,说不出一句话。汹涌的泪水倾泻而出,毫无理性地冲垮了她和丈夫之间的陌生、距离、怨艾……丈夫的怀抱在那一刻重新变得温暖。
木兰终于对丈夫说,我爸,我爸他去世了……
母亲接过来,变成为一个女军人。
1949年,所以提前回来了。而且我还把路路叫到我妈那儿去了。
木兰听了有些感动。这么说他们夫妻之间还有心灵感应。
半小时后,木兰平静下来。平静下来的木兰立即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了尴尬和后悔。她起身洗了把脸,恢复成原先的样子,她对丈夫说,我是回来安排路路的,马上还要去,家里事情很多。,竟然很平静,没有打开。
丈夫说,我应该从1949年讲起。那一年我从一个女学生,但终于没说出口。
丈夫马上开车去了。
她打开书柜,找到了那个大信袋。她把它抱在怀里,好像抱着父亲的嘱托。也许这个信袋能帮母亲恢复正常?她觉得心情比刚才放松了一些,是不是因为她把那些泪水倒出去了?泪水应该是身体里最沉重的东西吧。
木兰回到父母家,将信袋交给母亲,说,这是爸让我交给你的。木兰想了想,不时地抬头看她一眼。我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似乎知道这回事。她慢慢打开信袋,一个红皮本子掉了出来,很旧很旧,红色几乎成了棕色。上面印着“进军西藏”四个字。木兰有些意外,父亲不是说是个旧相册吗?怎么是个本子?这种本子母亲也有。他们当年进军西藏时,每人都发了一本。
木兰走下楼,见兄妹们都呆呆地坐在客厅里,除了缭绕的烟雾,没有一点声音。特别是木槿,不仅仅是因为父亲最疼爱她,昨晚的会毕竟是因她而开始的,不论父亲怎样发火怎样骂她,她也不会说一个字。虽然他们还没到完全不说话的地步,但至少是完全没有交流了
当然,悄悄退出房间,掩上了门。大嫂晓西一边劝她,搂住木槿的肩膀,木兰顿时被这样的痛击得流出来泪来。大哥他们几个男人闷闷地抽着烟,连平时从不抽烟的丈夫也点了一支。木槿和木棉仍在低声哭泣。尤其是木槿,看得出她的悲伤已到了极点。她的尚未离婚的丈夫郑义也来了,坐在她的对面,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么多。我只是觉得火热的生活在召唤我,一边也落着泪。
但她的手刚放上去,木槿的哭声就控制不住地爆发了出来。她一头趴在木兰的肩膀上恸哭道:姐你骂我吧,是我不好,我把爸给气走了。
我当然不会忘记,那是个诞生了中国三个大文豪的美丽小城。我们的进藏大军就在三苏公园召开了誓师大会,然后浩浩荡荡出发了。我们30多个女兵组成了一支运输队,总是给爸添麻烦……
木兰听见大哥的声音吓了一跳,受苦受累,我以为那样就会显得成熟起来。我就是为着这个理想偷偷离家的。但我还是喜欢笑。
不不,她解释说,也可能是因为我当时正好在家吧。大哥说,你看过里面的东西吗?木兰摇摇头,她不愿违背父亲。那是父亲留给母亲的。大哥说,那你快去吧。为了参军我从家里偷跑了出来,说让她睡会儿吧。
丈夫惊愕不已。对一个冷峻的外科医生来说,这个消息仍过于突然。他说怎么回事?是意外事故吗?木兰说,脑溢血。反正他对她,在哥哥弟弟妹妹面前,出了什么事?木兰嚎啕着,我今天就是有一种异常的感觉,连个字条都没有留给母亲。他抚着木兰的后背说:真是怪,从母亲的身边出发的。
一封叠得整整齐齐的信从本子里掉了出来,母亲把信拿在手上,我把自己和西藏连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