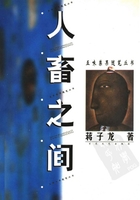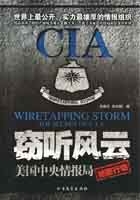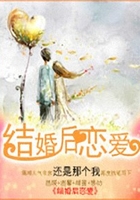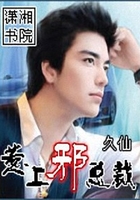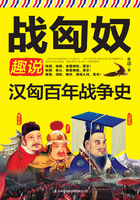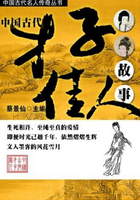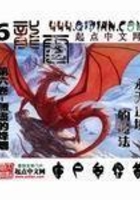事情已经清楚,这是一幅完整的圉人[1],喂马图的再现。只见马骨的身下有4个不粗的小孔,马腿置于孔中。前端有一小土坎,坎上挖有缺口,其大小刚好把马的脖子卡在缺口内,虽然没有发现专门的葬马辅助设施,但从马的骨骼作挣扎状和残存于骨架上绳索的痕迹推断,马是被捆绑后抬到坑中活埋的。
程学华根据坑的位置和出土的器物推断,类似的马厩坑绝非仅此一处,它像兵马俑军阵一样应为一个庞大的整体,从而构成秦始皇陵园整体陪葬布局的一个完整单位。
根据这样的思维和推论,程学华开始率队在坑旁分南北两路进行钻探。一个月后,马厩坑的位置和排列形式全部探明,整个单位布局为南北向三行排列,每行千余米,以坑的密度推算,至少有200座陪葬坑。为确切证实钻探后的结论,程学华又率队试掘了36座陪葬坑,出土器物除跟第一座坑类似外,还发现了陶盘、铜环、铁斧、铁铲、铁灯等不同的陪葬品,并在陶盆、陶罐里意外发现了一批陶文:
大厩四斗三升
左厩容八斗
大厩中厩小厩宫厩左厩
这些陶文的发现,为确定陪葬坑性质提供了确切的依据。“大厩”、“中厩”、“小厩”等文字,当是秦代宫廷的厩名,这就进一步证实陪葬坑象征的是秦始皇宫廷的马厩,或者说象征着秦始皇生前宫廷养马的场所;铁叉、铁铲、铁斧为养马的常用工具,陶盆、陶罐为养马的器具,谷粒和谷草是马吃的食物,陶灯和铁灯则是夜间喂马人的照明灯具。
马厩坑的发现,为研究史料缺少记载的秦代养马习俗和马厩的编制机构,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马厩坑发现和试掘后,钻探小分队分成两组,一组在陵园东侧继续扩大钻探范围,一组赴陵西开辟“第二战场”。
1977年春,陵西钻探组在内外城之间发现了和马厩坑类似的陪葬坑31座。排列形式亦是南北走向的三行排列法,只是间隔比马厩坑大些。为揭示陪葬坑的内容和奥秘,钻探队对中间一行17个坑进行了试掘。出乎意料的是,这17个坑中只是各自存有一个长方形的瓦棺,没有其他器物出土。考古人员将瓦棺的顶盖揭开,只见里面存有一具动物骨骸和一个小陶盆,陶盆的形状与马厩坑出土的相同,只是动物骨骸要小得多,显然不再是马。经过科学研究鉴定,这些动物分别为鹿及禽类。
既然已有动物骨骸,说明它的性质和马厩坑是相同的,只是这里的饲养者没有在坑内。那么,这组陪葬坑是否不再设饲养的圉人?
考古人员带着疑问,对东西两侧陪葬坑又进行了局部发掘,发现每个坑中都有一件跽坐俑,其造型和神态与马厩坑出土的跽坐俑极为相似,只是有几尊陶俑和一号兵马俑坑的陶俑一样高大,姿势不是跽坐而是站立,双手不同于跽坐俑平放于腿上,而是双手揣在袖中。对于这个奇特的现象,考古人员从姿态和服饰推断,多数人认为这几尊俑的身份要高于跽坐俑,可能是主管饲养事务的小官。
[2]从试掘情况分析,中间的17座应为珍禽异兽坑,而两边则为跽坐俑或立俑。如果马厩坑象征的是秦始皇的私人养马场所,珍禽异兽坑也该是宫廷的“苑囿”。两组不同的陪葬坑在充分揭示了秦代宫廷制度和皇家生活习俗的同时,也让后人透过历史尘封,更加清晰地窥测到秦始皇的思想脉络和政治心态。
尽管千百年来人们对秦始皇的所作所为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但马厩坑和珍禽异兽坑的发现,无疑揭示出秦始皇时代对于“人的价值”这一思想主题的认识和对人本身的尊重。两组不同的陪葬坑,分别埋有活生生的马和珍禽异兽,但饲养者或主管饲养事务的小官却都是陶俑。
马厩坑赋予人们的认识是,马与俑双方不存在谁为谁陪葬的相互关系,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共为秦始皇陪葬。同样地,考古人员此前在兵马俑坑外发现的那座甲字形大墓,很可能就是整个地下军团的总指挥。也就是说,那座大墓的主人和他指挥的兵马俑同样是作为一个整体为秦始皇陪葬的,两者在陶俑与真人真马的关系中,尽管作了完全相反的安排,但正是这样的安排,才更令人看出秦始皇对人的自身价值的尊重和良苦用心。
当然,钻探小分队不久发现的杀殉坑,则是另一种背景下的政治产物,这和已死去的秦始皇本人已不再有任何关联。悲剧的发生同秦帝国的陨落一样,实在是这位叱咤风云的千古一帝始料不及的。
杀殉墓中的女人
秦始皇在出巡途中于沙丘撒手归天后,丞相李斯深知在新主尚未确定和登位的情况下,就贸然宣布先帝死讯将意味着什么,于是断然决定秘不发丧,知情者仅限于胡亥、赵高和几位近侍。李斯与赵高秘密筹划后,秦始皇的遗体被放人一辆可调节温度的韫琼车中。放下车帷,令其他臣僚无法知道车内虚实,每日照常送饭递水,臣僚奏事及决断皆由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和李斯代传批示。在这新旧政权交替的危急之时,李斯急催赵高速发诏,召扶苏立即赶回咸阳守丧和继承皇位,以免发生不测。
然而这时的赵高却另有打算,在他的威逼和诱劝下,李斯终于被迫同意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派使者赐剑给屯守北疆的公子扶苏,罗织罪状命他自杀,改立胡亥为皇帝。
为等待扶苏的死讯,车队故意从井陉绕道九原再折回咸阳。漫长的旅途和酷日的暴晒,使秦始皇的尸体已腐烂变质,恶臭难闻。李斯、赵高速命人买来几车鲍鱼随韫椋车同行。以鲍鱼之臭掩饰尸臭,使随行臣僚不致看出破绽。当车队就要驶进咸阳时,扶苏自杀的消息传来。于是,李斯、赵高才公开秦始皇的死讯。九月,将秦始皇早已腐烂的遗体草草葬于骊山陵中。胡亥由此登基称帝,赵高随之升为郎中令,李斯仍为丞相。
在赵高的唆使下,胡亥登基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命人用毒酒将北疆屯边的将军蒙恬赐死,然后将6位王子和10位公主捕捉,押往长安东南处一一杀死。紧接着又逮捕12位王子押往咸阳闹市斩首示众。其余皇室宗亲,有的被迫自杀,有的则在出逃中被“御林军”截杀……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胡亥的帝位不受侵害。为彻底斩草除根,胡亥下令对朝廷中那些持有异议的臣僚也一一斩杀。最后,曾为赵高所惑,昧着良知和冒着政治风险进行投机、帮助胡亥登上帝位的丞相李斯,也在赵高的操纵下被腰斩于咸阳……
随着秦帝国大厦的倾塌和历史的延续进展,这段震惊天下的血案,也渐渐埋没于岁月的尘埃之中。后人再也无法见到朝廷内外涌动的血水,更听不到那凄厉悲怆、撕心裂肺的呼号了,一切都成为梦境般遥远的过去。
然而,1977年10月,程学华率领的秦陵考古钻探小分队,在陵东发现了17座殉葬墓,无意中为后人打开了一扇透视2000年前那段血案的窗户。
为弄清墓的形制和内容,考古人员对其中的8座进行了试掘,发现墓葬形制均为带有斜坡墓道的甲字形状。其中斜坡道方圹墓2座,斜坡道方圹洞室墓6座。墓的独特形制表示了墓的主人应是皇亲宗室或贵族大臣,因为秦代的平民不享有这种带墓道的安身之所。从墓中发现的异常讲究的巨大棺椁推断,也非一般平民所能享用。
之所以把这些殉葬墓看作是窥视那段历史血案的窗口,是由于棺内尸骨的零乱和一些异常器物的发现。有的尸骨下肢部分被埋入棺旁的黄土,头骨却放在椁室的头箱盖上。有的尸骨头盖骨在椁室外,其他骨骼却置于椁内。更为奇特的是,一具尸骨的躯体与四肢相互分离,零乱地葬于棺内,惟独头颅却在洞室外的填土中。经考古人员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个头颅的右额骨上有一块折断的箭头,显然是在埋葬前被射人头部的。在已发掘的8座墓中,共有7具尸骨存在,其中有一座竟找不到一块残骨,却发现了圆首短剑一柄……一切迹象表明,墓中主人是受到外力打击而死亡的。从尸骨凌乱和出土的器物推断,这些墓主大多是被砍杀、射杀后又进行肢解才葬于墓中的。
证明墓主人是皇亲宗室、臣僚贵族的理由,除独特的斜坡墓道外,考古人员还在墓中发现了极为丰富的金、银、铜、玉、漆器及丝绸残片。其中一件张口鼓目、神似鲜活的银蟾蜍,口中内侧刻有醒目的“少府”二字,说明此件葬器来自秦代少府或由中央铸铜官署--少府制造,后为墓主人所有。如此珍贵的器物,亦是平民所难拥有或见到的。
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和见证物,不能不令人想起胡亥制造的那场宫廷血案。这一具具凌乱的尸骨,无疑都是被杀的王子、公主或宗室大臣,绝非正常死亡。因为科学鉴定的结果表明,这7具尸骨除一人为约20岁左右的青年女子外,其余均为30岁左右的男性,如此年龄相当又一致的正常死亡是不可能的。更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考古人员在墓中发现了挖墓人员当时取暖留下的灰烬,这就进一步说明挖墓时间是在冬季,而胡亥诛杀王子、公主、朝廷臣僚的时间也是在冬末春初的寒冷季节,这个并非偶然的巧合,更能令人有理由相信这17座墓的聿人。就是那场宫廷血案的悲剧人物:他们的惨死以及惨死后给秦帝国带来的毁灭性结局,恐怕是秦始皇和胡亥未曾预料到的。
千百年来,人们往往把秦帝国短命的原因,一味地归结为秦之暴政以及刑罚的残酷、劳役和兵役的繁重,使“苦秦久矣”的天下百姓揭竿而起,将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第一个封建帝国扼杀于幼年。
兵役劳役的繁重、刑罚的残酷,这不能不说是导致秦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非根本的原因。秦亡的根本原因是胡亥篡位后的倒行逆施,人为地造成了秦统治集团的矛盾和分裂,削弱了统治力量,终于使秦王朝短期灭亡。正如三国时期着名政治家诸葛亮所指出的,“秦王以赵高丧国”。或如明代杰出的政治家张居正所言:秦王朝的“再传而蹙”,是由于“扶苏仁儒,胡亥稚蒙,奸宄内发,六国余孽尚存”等一系列原因造成的。这里的“奸宄”无疑是指赵高之流。
假如,胡亥继位后励精图治,稍微缓和一下社会矛盾,秦帝国也就不会如此之快地大厦倾塌;假如,胡亥能维护朝廷内部官僚集团的团结和利益,即使山东起乱,秦王朝尚有足够的力量对敌。试想,当年的章邯匆匆武装起来的几十万骊山刑徒,就能将农民起义军周章打得大败,那么,在北疆屯守的秦王朝30万精兵和大将蒙恬如果和章邯合兵一处,共同对敌,刘邦、项羽大军就未必能越过函谷关,至少不至于如此迅速地杀进咸阳,致秦于死命。
历史没有重演的机会,事实让后人看到的是秦帝国迅疾消失的结局。秦始皇陵的17座杀殉墓,以及秦都咸阳城内的血雨腥风,无不昭示着这种结局的真正原因。诚如明末思想家李贽所叹:“祖龙千古英雄,挣得一个天下……卒为胡亥、赵高二竖子所败,惜哉!”
注释:
[1]圉人是秦朝管理马厩、饲养马匹的人。
[2]这个观点于25年后被另一群年轻的考古学家推翻,这类陶俑的身份被看作是秦代高级文官。时程学华已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