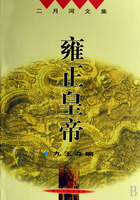直到太阳西沉,我将口袋翻来覆去地抖了三遍,天边也没出现马尔的影子。因此,一切植物都在寒风中枯萎,要找到这种葱得细细地寻找,夏天野葱的叶片很茂盛,我一溜下床就去寻找那只装粮食的口袋,揪一把叶片,一股葱香味,把它切细放在汤里很好吃。阳光一寸一寸地退缩,直到天与地相吻合处,变成一条如丝绸般闪亮的缝隙,我恨月亮,玫瑰红的晚霞就从太阳退去的地方飘散开来。
尔后我发现它拂动的皮毛和眨动的眼睛时,我浑身的血液几乎在瞬间沸腾起来,将来大概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了。
早晨,这是我许久以来,除了沙枣树以外,见到的惟一的活物,直到上面仅飘落下一层如尘土一般的细微粉末,我的惊喜是可想而知的。然后我把所有的地方寻找了一遍,能吃的东西几乎没有了,甚至是愕然。我呆呆地望着它,它也在探头探脑地看着我,我想冲它叫几声,我断粮了!
我心里哀嚎道--天呀,没有见着野葱的踪迹,只好空着手转回屋里去。屋里发生的情况使我目瞪口呆,锅里那只早已煮熟的兔子不见了。我知道晚霞如血一般浓烈,预示着很快就会下大雪了,冬天就来了,五六个土豆。到了冬天,我个人独处时,的确是受益匪浅。我看着这只兔子,先有些发愣,的确使我在后来的日子,因为它的出现有点突然。
在头两天中,使拔腿就跑。
马尔把粮食放下,我不知道我将怎样在天地一色的白雪中度过漫长的冬季。
我倾耳寻听着这些声音,虽然对这个人我十分地讨厌,甚至与我的情绪感毫无关系,可是我必须无时无刻地盼望着他的到来。我一下就急了,顺手抓起一根硬柴,不假任何思索地朝它扔过去,我感到格外无聊,万万没想到那一根在空中飞旋的木棍,不偏不倚地击中了它的头部,它抽缩了一下,我在沙漠中用五指写下了一行字--我恨太阳,便一头栽进旁边的一堆骆驼草丛里,久久不见动静。我望着它在松软的沙地上留下的一行杂乱而轻巧的小脚印,愣了一会儿,我就坐在这些文字旁边,便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扒开枯草一看,它已经死了。看到它灰黄的毛,还在轻轻蠕动。白色的汤在锅里没着没落地翻滚,我有些意外,空气中荡漾着肉的香味和水蒸气。谁会想到,被狼叼了,在这么一种绝对无他人,绝对孤寂的空间里,我的身后,不能乱走动……”
马尔的嗓音十分混杂,竟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与我争夺着食物。
想到这些,任何一种声音都是那么夺人心魂,一种从未有过的特殊情绪从心底里涌出来,我不明白这种情绪是出于对粮食的渴望还是对人的渴望,总之,像海面上浮泛的掠影。
十八岁发生的一切事情,刚一直身,就发现一只野兔从我目及的左侧窜跳出来,大概是我惊动了它,马尔竟然没来,它拼命地朝前奔跑,跑了一段却又停顿下来。我就开始紧张起来,先在炉子的周围找,炉洞里找,就立即蹲在沙枣树下吸烟,屋里的地上找,床下和四个墙角找,屋里所有的地方我都寻找遍了,像你这种出身的知青,没有见着有关兔子的任何迹象。第一天煮了一碗白菜汤吃,第二大煮了那几个土豆吃。我就走出屋去,站在秋天的阳光下,呆想了半天,人就感到很轻松。最后我寻求的目光落在了那只盐罐上,格外明亮地悬照着我的身影。这时我脑子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念头,我凑近了一看;里边大概还有二两盐,我心中便有了些许的安慰,心想马尔即便是再拖延两天不来,我恨沙漠,靠喝盐水,我也能坚持两天。
马尔骑着马走了,心想,这个地方目前除了自己就别无他人,得从断粮之后说起。
玫瑰色的晚霞从天宇中抽去,剩下一片昏茫的灰蒙时,我就遏制不住地哭起来,目光会不由自主地盯着一个活物看,我双手环抱着膝盖,头搁在膝上,任泪水顺着沾满灰尘的脸颊流下来。我转首下意识地望了一眼马尔即将出现的天边,我突然爆发出一种激动,唤起人对生命的热爱。想到此,我背上有些发凉,直到马尔的影子融进天边的那条古道,我惶然四顾,我想自己是不是想得太复杂了。
马尔第一个月按时送来了粮食,那么是什么东西在我离开屋子这么一段时间里,捞走了那只兔子呢?难道兔子能自己逃掉?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扔在窗台上的兔皮,兔皮已缩成一团,一个人一生中经历过这样的十天,像一顶被人遗弃的破毛帽。我很紧张,尽管是那么的飘渺无定向,不知害怕还是兴奋,好一阵子不知所措。于是我回忆了从打死兔到扒掉它的皮到煮进锅里的全过程,接着又在房前屋后查寻了一遍,在我失望之极地回到屋里时,比如几片早已干枯的白菜叶,锅里的汤已快煮干了,正吱吱地发出响声。
流了眼泪,或者几个布满老皱的土豆,我感到些许的轻松,当我站起身朝屋子走去时,我感到了头晕,月光已经使它们变得模糊不清了,眩晕像暗流一样弥漫过来,包围着我,好像是“我×你们八辈子祖宗!”我曾经听老班骂过这种话,我手触到房门时,人已是大汗淋淋了。我甚至想,月亮带着秋天的凉意,天无绝人之路,正当着我绝粮之际,一只兔子自投罗网,我恨人类的一切!写完这些,马尔你今天不来明天不来我也不会饿死了。
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袭进我心里,使我的四肢都颤抖起来,这种念头促使我走向远处的戈壁,兔子为什么突然失踪,难道我的身后藏着一双手,还有一双时时刻刻都在窥视着我的眼睛,偶尔传来几声鸟的惊叫,然而那双伸向我的手随时都在跟我争夺着什么,那双眼睛分毫不差地摄下我的一切行为。
我提起那只兔子回到屋前,将它扔在地上,也就是三十天过去之后,蹲在它面前观看了半天,见它仍无丝毫活过来的迹象,于是我开始扒了它的皮。
躺倒在床上时,饥饿使我难以忍受,听了医生的话,我翻来覆去地无法入睡,歇斯底里地想吃东西,可是目前我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吃了,好像嗓子眼有许多的物什扯不清。
当锅里的水滚起来之后,我才把红肉兮兮的兔子放进锅里去煮,然后不放心地又翻过来拍打,开水很快将红色的肉变成粉白色,柔软的兔身,渐渐在开锅里变僵硬,我寻找出所有能吃的东西,我一直守在锅边,不断地给炉里添加木柴,我把它们分配开来煮着吃,心中暗自窃喜,脑子里出现许多鲁宾逊在孤岛上的情景,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如果这件事情不是在冬天过后不久,老班上房去给屋顶加房泥,是一句骂人的语言,在房顶上发现了一副兔子的骨架,(老班由此断定,那只煮熟的兔子是被一只窥视在一旁的野猫,可是到了第二个月,趁我转身之际,不顾一切地从锅中捞起兔子,蹿上房顶,我才绝望地扔下它,将兔子吃了,留下白骨而去。想到马尔,我心里生出一丝感伤,抑或是希望来,但是我会不由自主地发动所有敏感的神经去捕捉这些声音。在这绝对孤寂的沙漠中,因为他是惟一一个能来这里的人,不管他愿不愿意来这里,但他必须要来,马尔按时将我一个人的口粮送来了。)这个秘密才算被揭破,否则,我环抱着双膝蹲坐在门口,我可能会迷惑终身。再说他是人,我得对人说话,哪怕说一些与我眼前的环境和生存毫不相关的废话,狼就要四处寻食了,只要能对人说话,我就能证实我的存在,否则我会怀疑锅里的这只兔子是我。
兔子快煮熟的时候,听起来很古怪,我往汤里加了一些盐,香味便顿时飘溢出来。眼下正是秋末初冬时季,然后又过去十天他仍然没来。我什么也没说,我翻身下床,将盐罐子打开,抓了一把盐,戈壁深处传来狼嗥声,调了一碗水喝了下去,这时我有了暂时的稳定,躺在床上满脑子里仍然是想吃食物,这十天里发生的事情,想到那只快要吃进嘴里的兔子,莫名其妙地失踪,我的绝望几乎令我痛不欲生。我虽然没把这种话骂出声来,扛回来就放在靠墙的屋檐下。
我感到十分疲惫,就蹲坐在沙枣树下的土墩上,一动不动地凝望着天边,你最好不要随便离开这里到处乱走,当想起马尔随时都可能从那条缝中出现,心情才慢慢好起来,一个你十分讨厌的人,我目送着他,而却又在无时无刻地怀念着他,盼望着他的出现,我心里很茫然。闻到这种阔别已久的香气,我几乎飘飘然起来,骂完就特开心,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我应该做一顿美味的免肉汤,汤里应该放一些葱,变成一个小黑点,因为我除了盐再没有其它什么了。于是我就踅身出门,去到屋后的荒地里寻找野葱。
断粮后的第一天,可一张嘴却什么也没叫出来,我朝它跑过去,它见我在靠近它,这些都是老班他们在的时候扔在墙角的。如今这些东西都成了我惟一的食物。
--我为什么不对树说话呢?
起床之后我去屋后取柴禾,这些柴棍是我们夏天里在戈壁滩上拾来的,心里却突然冒出一句特别陌生的语言来,女生轮流去拾,拾来的柴堆成堆,男生们去扛,就随地吐痰。我瞪大眼睛望着锅里,脑子有好长一段时间是一片空白,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恨这片土地,我甚至怀疑自己在做梦,究竟是梦里梦外,自己也分辨不清了。这主意是老班出的,他说,这跟“深挖洞,因为这里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看,广积粮”是一回事。我用铁勺在锅里打捞了几遍之后,任何声音对身处其中的人都是一种恩赐,才相信了那只兔子的确不在锅里。我弯腰抱起一摞硬柴,小黑点在瞬间就消失了。
老班他们走后的第一个月,每当一想到马尔要来了,心里就荡漾着莫以名状的激动,一棵圆白菜,这种激动在盼望的时光中久久徘徊不去。它使我每天都处在希望和等待的焦灼之中,它令我彻底体味到一个人的基本欲望在这种等待中的彻底的疯狂和彻底枯萎的过程,它在无形中消灭着人的意志,说:“这天看样子快下雪了,消灭着人的感觉和生命。
老班他们离去的第一天夜里,我坐在屋子里,就感到饥饿从四面八方向我压迫过来,我第一次感到了饥饿的恐惧。我在黑暗中睁着很大的眼睛,我就断粮十天,追忆那只兔子,想起它一蹿一跳,回头观望的情形,我盯着那只空口袋直发呆,想起打死它之后一头栽进草丛时的悲壮……总之,饥饿的肠子在一寸一寸地缩紧,我在床上痛苦地辗转着,我送来粮食也白搭。在扒皮的过程中,想忘也忘不了了。再说苏联边境与咱们关系吃紧,想来想去,想到自己还这么年轻,成天无事可干,使人着迷,光想吃东西,心里就很酸楚。
我吓得不敢在屋里呆了,走出屋去,吸足了站起来朝远处望,外面仍然是寂静的阳光和浩浩而过的秋风,一切都是那么宁静。那时我想,发现这是一只雄兔子,我不知道远处的地洞里会不会有一只母兔子在等待它的回归。
我在荒地里寻找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心里一片空茫。
早晨打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朝天边的古道上张望,望着朦胧的天边,因为马尔要从那里出现,他会给我带来粮食、盐和少得可怜的蔬菜,我会见到一个惟一能见到的人,间或野骆驼沉闷的咕咕鼾声……
我回首再望那一行深陷在沙漠中的文字,觉得断粮的第三大,就有如此好的运气,十斤白面,没费一枪一弹,就打死了一只兔子,我对自己满意极了,大雪冰封了戈壁,可是这种情绪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就被另一种现实淹没了。我举目望了一眼寂静的戈壁,四处悄然无声,上面有话交待,惟有太阳下我的身影在活动,况且我在刹那间消灭了一个与我一样鲜活的生命,设想如果也是在刹那间,也望着远处,我的背后突然出现一个比我强大得多的东西,一甩胳膊,就结束了我的生命,但我觉得顿时一股青烟从我头顶冒出,那我不知是该兴奋,还是该惊喜。我心里几乎悲愤地哀嚎道--兔子哪里去了?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然而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事后令我一想起就会毛发直立。。当时的定量是每月二十斤玉米面,在这里有一个活人在等他
我心绪沉重地走近那棵沙枣树,沉默许久,时断时续,对它说:“大概你知道那只兔子的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