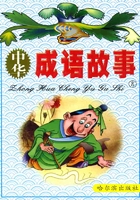雪后的那天上午,聂书记带着秘书,驱车百余里,去邻县的一家医院看望吕国清。
那夜坠楼摔伤,吕国清被送进县医院抢救。待伤势稍平缓,吕国清也神志清醒后,他坚决要求立即转院治疗,不在本县,也不去市里任何医院。他的这个要求很容易理解,官场上的人,脸面重于伤势啊。小县城里的人谁不认识他?又谁没听说这桩风流丑事?市里的同僚们也不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磕头碰脸的,对人说什么呢?自己脸上挂不住,让别人都跟着尴尬。聂书记派车把他秘密送到邻县的县医院,那家医院的院长是聂书记过去的老同学,他只说伤者摊了车祸,是自己的一个亲戚,务请多给些关照。又吩咐司机和秘书守严嘴巴,吕书记需要用车用人,只管来就是,不需再请示惊动其他人。县里的干部们也预测吕国清伤好后,不好再回县里工作,上级必另有安排,便故作不知,也不问,只是在私下里嘀咕嘀咕而已。
吕国清因此得些清静,身边陪护的只有夫人。起初夫人也哭闹着不去,说嫌丢不起那份人。聂书记又做她的工作,说了许多言不由衷和推心置腹的话:“日子还是要往下过。国清同志伤好了,大不了换个地方,而且还得与原级别相对应,这点小节之误,是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党对一个干部安排使用的。不要看一时一事,而要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组织上要这么衡量使用干部,家属也应这么看待问题。国清一时糊涂,做下错事,这要批评,他也真心实意有了痛悔的表示。我们总要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吧?
不能因犯下一点错事,就一棒子把人打死嘛。一个家庭,破坏掉容易,再重新组建就难了。家家都有本难唱的经,大局为重,长远为重吧。你一时气愤,这我理解,但还能永远不再理他吗?一日夫妻百日恩,还想再走进另一家门吗?即便有这么个可能,你能保证那个男人一定会比国清强多少吗?男人嘛,寻花问柳是通病,常见病多发病,既有社会的原因,可能也有生理上的因素,地球上的所有雄性,差不多都犯这种毛病,据科学研究,连鸳鸯那种鸟,都不能免俗呢。国清有了这一次,也许就有了免疫功能,那就变坏事为好事了嘛。再说孩子,因为家庭的破裂,孩子一时心灰意冷,就可能误了她一辈子的前程。国清眼下最需要的,除了治疗,就是亲人的原谅与安慰。谁是他最亲的人?就是你和孩子嘛。我说这番话,可不是打官腔,也不是依着民俗古训,宁拆十座庙,不拆一对婚。我全是真心话,就是我亲姐妹摊上这种事,我也要这么劝,这么说。这你信吧?”
吕夫人顺坡下驴。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家里又有孩子在念书备考,还能闹到哪里去?又能闹出什么结果呢?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丢人的事闹开了,也就不觉见不得人。在背后,吕国清又痛哭流涕,跟她说了许多其实只和夫人天长地久,和姓谷的只是逢场做戏,并保证和那狐狸精划清界线永不来往的话,尊贵的夫人只好让自己娇嫩的脸皮像入冬后的畜兽之绒,一日日地浓厚起来,一脸愠怒地还是跟着来陪护了。吕夫人甚至心里还生出些悔意,如果那天在谷姗家门外,顺了聂书记的意思及时躲离开那个是非之地,又何苦惹出吕国清伤身丢人又丢美差、自己也跟着抬不起头的这番后果呢?这个酸果子既是自己又吼又骂讨来的,吃不下就只有强咽了。这般一想,才知确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聂书记确是高人一筹啊!
聂书记的再次专程探视,让吕国清心生感动,也暗存惊疑。转院之后,聂书记曾来过一趟,说了些宽慰的话,又把院长请来,当面再请关照,离去时说,正逢年底,县里工作忙,又暂缺你这员战将,可能就要更忙,我就不常来看你了,有事多打电话吧。吕国清说,你忙你忙,再牵扯你精力,就更让我没脸见人啦。
按说,聂书记于公于私,这几步棋,走得都已十分到位,无可挑剔。他不顾雪后路滑,又一次亲自来,一定还有探望之外更重要的事要说吧?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呢?莫不是市里为了消除影响,已经做出重新安排他工作的决定?那总得等他伤好出院吧,能这么快吗?
果然,聂书记问了些治疗情况,又说了些闲话,便望望吕夫人和秘书,说:
“我和吕书记谈些工作上的事,你们去休息,就不要陪着了。”
吕夫人和秘书会意,退出,门掩死。吕国清的心紧上来。
聂书记淡淡一笑,问:“是不是在猜我要跟你说什么?”
吕国清故作镇静地说:“您说吧,我有心理准备。”又把床头柜上的烟拿起来,“哟,坐了这半天,也没说请您抽棵烟。”
聂书记又笑:“怎么,刚分手这几天,连我不吸烟都忘了?还是心里发毛吧?”
吕国清便尴尬地赔着笑:“那是那是……心虚,心虚。”
聂书记敛起脸上的笑容,说:“好,那就言归正传。我跟你说两件事。第一件,市公安局最近破获一个诈骗集团。据犯罪嫌疑人交代,几个月前,也就是孟昭德神秘失踪的那几天,他们合谋搞了一起所谓的‘双规’诈骗,被‘双规’者,就是孟昭德。嫌疑人里有个以前在纪检部门工作过的败类,后因腐败问题被查处,开除出纪检队伍,安排到企业做了一般行政管理人员。这个人因有双规工作的经验,所以搞起这种诈骗来就得心应手,搞得天衣无缝。孟昭德贪污受贿问题不少,心怯胆虚,人家连诈带骗,就白白交出去了十万余元赃款,还给人家写了认罪材料。连同赃款和认罪材料交出去的,还有一张对我们来说曾是至关重要,险些引发一起重大抗税风波的单据,就是那张假借于家台村民于旺田的名义,孟昭德亲手办下的那张退税单。”
“诈骗犯要的是钱财,那张退税单对他们来说,不过废纸一张,揩腚用都单薄。他们又蓄意挑起风波干什么?”吕国清不解,忍不住问。
“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诈骗团伙里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了。这人就是于家台村的朱景发。因为一些偷蟹丢蟹之类的纠葛,孟昭德为了制服朱景发,便派人盯梢,专抓朱景发的赌,抓到后惩治得又很严厉,不光罚款,还把他送去劳动教养。朱景发因此对孟昭德怀恨在心,蓄意报复。在县劳教所,朱景发认识了因诈骗而被劳教的一个犯罪嫌疑人,便主动加盟,那个所谓‘双规’的恶点子就是他出的。他对那人说,你既会骗,那就别小打小闹,没意思,也得不了屁崩的几个小钱儿。
我给你出个主意,保证一次顶百次,如果以前你偷到手的是一只兔子一只鸡,那这次就是一头牛,甚至是头大象,而且手到擒来,一骗即成。那个被骗的贪官还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绝对不敢举报。那个嫌疑人听了点子,大喜,出了劳教所后,就约了以前一块做过案的同伙,其中就包括那个曾在纪检部门工作过的败类,一同把孟昭德狠狠骗了一次。孟昭德果然吃亏不敢说,甘认倒霉了。在分赃时,朱景发看到了那张退税单,便留下了。据公安部门眼下掌握的情况看,孟昭德到县劳教所工作后,可能已发现了诈骗人的明确线索,但仍没举报,这个问题的性质就更加严重了。在‘双规’诈骗时,朱景发因和孟昭德认识,并没直接出场前台,而是幕后主谋,是策划兼导演。就因这点子,他分得赃款三万元。至于他把那张退税单张贴出去,蓄意挑起事端,一是继续对孟昭德实行报复,二是想浑水摸鱼,以此抗交特产税。昨天夜里,县检察院已批准对他实行逮捕。我刚才对你说的这些,就是根据他昨天夜里的初步交代。案情的具体情况,再看审讯进展吧。”
吕国清大瞪了眼,似在听天外神话。这个神话,主角朱景发,岂只是个普通村民,一个乡下的二流子?如果不是因了他,能引发那场抗税风波吗?没有那场风波,孟昭德能跟自己结下那么大的仇怨吗?没有孟昭德的仇怨,自己能躺到这里来吗?这是多米诺骨牌,一连串的反应。这些天躺在病床上,思来想去,一夜一夜睡不着,吕国清早已怀疑那个谎报自己在谷姗家得了急症的电话是孟昭德所为,只是苦于没有确切证据。如此看来,此案一破,顺蔓摸瓜,这个疑点也将破解。吕国清呆怔了好一阵,才咬牙切齿地说:
“该,该!他罪有应得!那孟昭德呢?”
“这就是我要跟你碰头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因为是县管的干部,你又分管干部和公检法工作,县委必须统一意见。常委会准备下午例会,研究对孟昭德采取第一步的措施,双规。至于最后怎么处理,待双规后酌情再定。我专程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同意。他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对这种人,早该采取坚决的组织措施。而且……”吕国清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是不是可以把我的……这个事,请专案组一并追查。”
“你的什么事?”聂书记怔了一下。
“就是有人往我家里打电话,谎报我得了急病的事,我怀疑也和孟昭德有关。今天既把话说到这儿,我就把心里的这些疑惑都讲出来。我和谷姗的不正当关系,要说有人察觉,就我所知,也就是孟昭德。而且孟昭德有个情人,住的地方与谷姗家不远。我希望组织上不要把我的这个意见看作私人泄愤公报私仇。这涉及到一个干部的品质,甚至可以说触犯了法律。”
聂书记点头:“组织上会重视你的这个意见。其实,你的这个事一出,我就怀疑有人挟嫌报复,也怀疑到了孟昭德,还派人去查过电话记录。可那个电话是公用电话打到你家的,线索一断,只好暂放。你要是早把这些疑点说给我,也许……我早就采取一些组织手段啦。”
吕国清解恨地说:“不怕鬼子闹得欢,就怕秋后算清单。时候一到,善恶有报!”
“说的好,善恶有报。”聂书记应声接道,“对这一点,不光是对孟昭德这类干部,其实对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用老百姓血汗钱养育着的每一个干部,都应该经常这样自我告诫,老天有眼,善恶有报,侥幸不得呀!”
聂书记说着,还意味深长地扫了吕国清一眼。
这一眼,让吕国清顿觉脸上烧起来。他意识到,聂书记要说的第二件事,一定会和自己有关了,而且兆相不祥。一般地说,领导者和下属谈话,都会把轻松些的话题放在前面。如果一开始就直逼要害,让对方心神不宁惊惊恐恐,那下面的话还怎么谈下去呢?
“昨天,下面有同志来向我请示,说今年你雇蟹农养蟹,哦,准确地说吧,是你雇蟹农为谷姗养蟹,你和谷姗从一开始,都并没出任何本钱,所投入的资金完全是孟昭德经手,从乡信用社贷下来的,而且用的是扶助贫困户于旺田脱贫的名义。他们问我,怎么处理?这件事,是纯属偶然也好,是纸难包火、雪难埋尸的必然也罢,于家台村的村支书于水丰已经知道了,蟹农于旺田本人也知道了,我估计,于家台村村民都会知道了。据说,群情愤慨,沸沸扬扬,于旺田还气得当场吐了血,骂天咒地,不肯善罢甘休……”
吕国清慌了,脑门上的汗刷地出了一层:“聂书记,孟、孟昭德以于旺田的名义贷款,这事我完全不知道,真不知道。我以党籍人格担保,要说一句假话,组织上给我什么处分都行。”
聂书记面色冷峻起来:“至于责任嘛,对孟昭德实行双规后,自会水落石出,该是谁就是谁的,想推脱也推脱不了。但雇人养蟹买苗,你确没掏什么本钱,这不会错吧?秋后,孟昭德把卖蟹所得的几万元票子都交给了你,你如数收下,也并没拒收吧?”
“聂书记,”吕国清满面紫涨,越发慌乱,“您、您说的不、不假,这事我……确、确是有失误之处,我当初没问贷款的名义,就是最大的失误。但是,这种错误和我有意而为,不是同一性质。我有贪小便宜,不劳而获的心理,但我真、真是受孟昭德蒙蔽啊。我即便真是个爱贪便宜的小人,也不至于……愚蠢到这种程度,把鞭子送到人家手上,让人家抽我。聂书记,我跟您工作了好几年,我的为人,老大哥您总会知道,这事,您可得为我做主,千万不能让我冤枉啊……”
聂书记叹了口气:“国清啊,你这样说,就是不知我心了。我要真想用这件事做文章,交给纪检部门去调查处理就是了,还会冰天雪地的专程跑这么远来跟你说这事吗?无论于公,于私,我都希望这事要尽快摩挲平整,尽量缩小影响。所以乡里向我请示时,我已明确表态,此事绝不能扩大事态,千万不能再惹风波。风波一起,我估计绝不会比上次小,而且矛头会直接指向你。但我思之再三,觉得这事光压不行,也压不住,还是要因势利导,尽量在最小范围内化解于旺田和群众的忿懑情绪。就好比夏秋季节防涝,光筑坝憋水不行,还得想法把洪水疏导开。怎么化解疏导呢?我想,解铃还须系铃人,还是由你个人出面,为上上之策。如果组织出面,也许反倒会把事情搞得更僵。而且一旦出面,就有个以后如何结论的问题。我想,这个结论不管怎么做,都不会对你有利。国清啊,我真心实意不愿再在你的伤口上揉盐面子呀。你身体不好,正在养伤,心情不舒畅,行动也不方便。我这样说,也许是给你出了难题,但凡事都要以大局为重,以长远为重,能克服就克服克服吧。只有你亲自出面,从矛盾的源头处,也就是从于旺田那里解决问题,请求原谅,才可能化大为小,化小为无。我这样设想,你不会理解我是袖手旁观,故意看你的笑话吧?”
“哪能哪能,”吕国清听明白了,也从心里感动,他紧紧抓住聂书记的手,眼里不由蒙上一层泪光,“我要那样想老大哥,就是四六不懂,不知好歹了。好,好,这事由我来做,请老大哥放心,不管有多大难,我也要努力办好,一定不给老大哥和组织上再添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