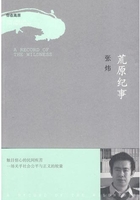这一年的冬天,天气出奇地寒冷,据说还创了共和国建国以来同期之最什么的,直到年底,还没下一场像模像样的大雪。偶尔阴云密布,也只飘过一层稀落雪花,西北风一旋,便刮得干干净净了。农民们开始发愁,说再不下雪,明年开春必大旱,大旱则水库里缺水,水是种田人的命根子呀,缺了水,水稻咋长?蟹子又咋养?农民们盼雪花,如同盼老天爷往下飘票子呀!
于旺田每天清晨出去卖豆腐,顶狗皮帽,脚踏大头鞋,手戴棉闷子,脖子上还厚厚地缠绕着苏凤荣的紫色长围巾,跑回家来的时候,还是冻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站在地上直跺脚。苏凤荣便急急地从灶坑里扒出一盆还闪着火星星的草木灰火,让他坐在火炕头守着火盆烤上一阵。灰火里埋着土豆地瓜呢,烤了一会儿,身上的寒气驱散了些,也闻到了一股甜滋滋的香气在屋子里荡漾。于旺田扒出来,拂打掉上面的浮灰,掰开,土豆起着沙,地瓜瓤糖稀一般黄澄澄地冒着热气。于旺田趿着鞋先送到苏凤荣嘴边去,“来,来,你也吃一块。”苏凤荣总是幸福地嗔他,“别小孩子似的,自己吃去。”
一块热呼呼的地瓜或土豆落了肚,这才觉得身上真的暖和了。薯皮随手往地上一扔,墙角便爬起一只圆圆滚滚哼哼叽叽的活物来,三口两口把薯皮吃下去,嘴巴还叭哒叭哒咂得山响。
这几个月,总算把学校催要的各种费用给水秀交齐了,又攒钱买进一只小母猪。这两年,猪秧子贼贵,一斤顶上好几斤里脊肉钱,一只小猪也得一二百元呢。苏凤荣说,攒下的钱够买一只就先养一只,养上几月,等下过头窝羔子咱就不愁了。于旺田却为房顶上存放的那么多豆腐渣发愁,开春一开化,可就放不住了。苏凤荣说,看屯里谁家养猪,就便宜喽嗖地卖了吧,多少也算些过日子的贴补。
做豆腐就要剩下豆腐渣,每天摔拍出三五砣,送到房顶去,西北风一刮,冻成白亮亮的冰砣砣。啥东西一成规模,就成了一道风景。于旺田家房顶的一片白亮,让屯里人好不眼热。豆腐渣是养猪的上好饲料,猪爱吃,抢膘快。可毕竟家里只有一头半大母猪,铆足了劲让它可够造,又能吃下多少。真要嚷出去卖豆腐渣,就不值钱了,一块钱两砣,买的人也不多。后来苏凤荣说,干脆送人情吧,谁愿拿谁拿,总比开春烂扔了垫圈强。
进了三九天后,天气一日日冷得不松口,苏凤荣怕小猪冻坏,就圈到屋里来养,在屋角铺些稻草,让小猪过贵宾样的生活。那东西是个能吃能喝又能拉撒的活物,粪粪尿尿的难免就在屋子里留些骚臭。于旺田对苏凤荣说,我知你是个爱干净的人,只怕你忍受不得嫌埋汰呢。苏凤荣说,将就它这一段吧,既是咱一家的指望,还嫌弃个啥呢。你没看古人造字,家就是宝字盖下面一个“豕”,那“豕”字就是猪。古人就是把猪养在屋里的,没个猪就不成家了。于旺田说,没看出,你还挺有学问呢。苏凤荣说,我是现学现卖,电视上有个栏目叫说文解字,我也是刚看到的。
大寒是一年里的最后一个节气,到了这个时候,已到处能感觉到过年的气息,屯子里每日都可听到年猪被宰前的嘶叫声。有那性子急的,已扫了房,擦了门窗,门口贴了大红的对子。小孩子们也时不时地点响一两声爆竹,砰叭出年的序曲。
这一天,于旺田卖了豆腐回来,坐在炕头刚烤上火,就见院子里进来了村支书于水丰,身后还跟了两位女子,俊俊俏俏白白净净,看打扮不像是在田里插秧割稻的角色。于旺田急急穿鞋下炕,苏凤荣也急把小猪踢到灶间去,往炕头上礼让两位客人。
于水丰进了屋,就靠了北墙的板柜卷旱烟,一张脸阴沉着,说:“老旺叔,这两位是乡信用社的,来屯里专为你的事。刚才到村委会打听你住在哪儿,我就问了问。思来想去的,觉得这事头头尾尾,还是让你和婶子知道的好,不然别说对不起咱于姓的一个祖宗,都对不起一个屯中住着的乡亲了。”
于旺田听他说得严肃,便问:“啥事呀,让你说得血赤呼啦的吓唬人。”
于水丰又说:“你们听了,千万要稳住性子,别着急,也别上火,事有事在,理有理在,咱慢慢来。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爱谁谁,这天下不还是共产党说了算吗!”
当着两位陌生的女人,于水丰这样破口大骂,不是他的风格。
苏凤荣惊疑地看了于旺田一眼,说:“于书记,有啥话你就说,于旺田老实厚道一辈子,却不怕事。我们没做违法的事,不信谁还敢来扒我们家的房子!”
于水丰将烟尾巴往地下狠狠一摔,骂:“他妈的,我也豁出来了,大不了这村支书不让我当了还能怎么的,我就不信谁还敢把我的×咬去不成!”
于旺田听于水丰这般说,这般骂,越发怔了。这不像水丰啊,当着外来女人的面,不该这般脏字不离口啊。他说:
“你说吧,不管啥事,我和你婶子撑得住。”
于水丰便对两个女子说:“你们谁说?该咋回事,就咋回事,用不着藏着掖着,从根上说。”
两个女子一听此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两眼也都有些发直发怔。年长些的说:“你说吧。”
年轻些的也说:“还是大姐你说,这事你经手。”
年长的似乎多些心眼,使了个眼色,说:“那……是不是咱们今天先回去,向主任汇报了,改天再来?”
年轻的会意,忙点头:“也行。”
两人起身要走。于水丰却一步跨前,堵在门口,黑着脸说:“话你们已经跟我说过了,想再遮着瞒着玩猫盖屎的勾当,就没意思了。我只请你们二位当面,再把事情跟当事人说说清楚。事情该咋办咋办,这事有啥责任也不在你们,我在于家台还说了算,出了天大的事,我担着。你们说完就走,我绝不会难为二位。可我也把丑话说在前头,你们要再想为谁遮着瞒着,今儿谁也别想走出于家台!”
事已至此,那个年长的只好从挎包里拿出一本账薄子,摊展开,说:“是这样,今年开春的时候,于旺田不是申请过两万元钱养蟹贷款吗?孟乡长亲自做了批示,又亲自找了我们信用社主任,这件事就算办下来了。两万元现金是孟乡长亲自替于旺田取出的,说于旺田是他的包贫户,由他负责转交。秋后呢,孟乡长又亲自将两万一千元钱交到信用社,说两万元钱是本金,一千块钱是利息,利钱不够的部分待结算时再找他。说话间这就到了年底,经结算,于旺田还欠乡信用社七十三元六角钱利息。为这事,我们又找了孟乡长。你们可能也听说了,孟昭德上个月已调到县劳教所当副所长去了,乡里离劳教所好几十里地呢,孟乡长又不常回家,所以我们是打电话问的。孟昭德在电话里说,他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了,所欠的七十多块钱让我们找于家台的村支书于水丰要,说于书记从头到尾都知道这个事。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了。其实事情并不大,不过几十元钱,你家里一时手紧,我们再等些日子也行。”
于水丰又骂:“要只是为七十多元钱,我扯这鸡巴蛋?到底是谁欠着谁的,又欠着多少,还不一定咋说呢!”
其实,在村委会一听这事,于水丰就明白孟昭德在玩他偷驴,让别人拔桩子的勾当。他跟县里的吕国清结仇了,想挑拨于旺田跟吕国清算账打官司,可又不想明目张胆地得罪吕国清,所以才当二传手,把直击吕大官人的恶球送到于水丰面前来。于水丰若想巴结吕书记呢,那就代交上七十多元钱了事,只要不让于旺田知道真相,便仍可天下太平;若于水丰敢与老虎谋皮非要告诉于旺田呢,那活该的是吕国清,自讨倒霉的还有于水丰。于旺田找吕国清讨要养蟹的全部收入,吕国清必迁恨于于水丰,县里的官收拾一个小村官,还不如同大卡车碾压小鸡小狗?一石两鸟,又可自躲干系,孟昭德这一手阴险狠毒啊!
于水丰甘愿被碾,也要颠一颠那辆大卡车了。
于旺田虽然不懂官场里勾心斗角的这些奥妙,可他还是听明白了,原来一切都本应是自己的,那两万元钱的贷款,那六亩地的责任田,那一年的汗水养肥的几百斤的蟹子……只有权势是当官的,可人家仅凭着那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点权势,稍稍玩了一点儿鬼招子,就将那几万元的收成连个水花儿都不留地捞走了,干净彻底得连个蟹爪子都没给自己留下,留给自己的只是那说不尽的贫贱与屈辱……
于旺田痴痴地坐在那里,不说话,也说不出话。苏凤荣忍不住,催了他一句:
“旺田,你傻啦?说话呀!”
于旺田果然就傻了,嘿嘿地傻笑起来,笑过一阵,突觉眼前一片黑暗,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又觉眼前一片白亮,耀晃得睁不开眼睛。胸口窝有一股腥腥热热的东西涌上来,他哇地一声,便将一口鲜红鲜红的血液喷吐在地上了。
众人慌了,急急上前扶住他。他拨拉开,三步两步冲到了院里去,仰着头嘶着嗓对着阴气沉沉的天空吼骂:
“我操他八辈祖宗!这些贪官,这些恶霸,你们比黄世仁还贪,比南霸天还狠,你们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黑心贼啊!……这些该挨千刀的混账王八蛋们,这些该下油锅的八爪螃蟹们,你们给我支楞耳朵听着,你们就兴风作浪吧,你们就四处横行吧,共产党早晚收拾你们,老百姓早晚还得跟你们玩命!老天有眼啊!……”
这一晚下了大雪,整整下了一夜。强劲的北风裹着大片的雪花,狂暴地扫荡着沉寂无言的田野和村庄,在枯黄的芦苇荡里,在光秃秃的树梢上,愤怒地嘶吼咆哮了一夜。风过天晴,天地静下来,一片白茫茫。
这一夜的风雪中,还发生了一件事。县里的一辆警车开进于家台,从热被窝里抓走了朱景发。朱家邻居只听朱景发撕挣着喊叫了几声“我没犯法,我没赌博,你们凭什么抓我!我抗议!”就被塞进车门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