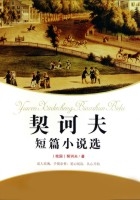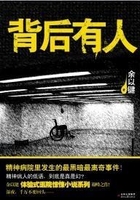杜成林是第二天入夜时分到的于家台,还带着儿子。他问儿子,想不想你妈?儿子恨他跟妈妈闹离婚,答话便没好气,说我的妈我咋不想?杜成林不跟他计较,说那好,我带你看你妈去。儿子便乖乖地跳上车后座,随他来了。
那个时候,苏凤荣正在家里缠毛线,她找出一件破毛衣,拆线,洗净,想抢在天冷前给于旺田织上,添上些新线也有限。她让水秀用两手绷着,自己缠,娘儿俩边干活边唠得亲热。杜成林进屯后,一路打听,隔窗看到苏凤荣的身影,也没敲门打招呼,就径直进院,登堂入室。苏凤荣见了,兀自一惊,问:
“你们咋来了?”
杜成林不用请让,用鼻子哼了一声,自己拉条板凳坐到对面,从衣袋里摸出烟,点燃,抽起来。儿子见到妈妈,眼圈一红,说了声“妈,我想你。”就扑到苏凤荣怀里来。
苏凤荣揽住儿子肩头,鼻子酸上来,说:“妈也想你……”
杜成林四处扫了一眼,冷笑:“抖落抖落破布衫子,又找了个比原来的家还穷得掉底儿的破狗窝儿,还能想得起你儿子呀?”
苏凤荣听他这话是来故意寻碴儿打架的,又看水秀正瞪着一双惊慌的眼睛望着她,便冷冷地说:“你要是送儿子来看妈,我谢谢你。儿子送到了,你现在就回去吧。我身上掉下的肉我自会心疼,儿子啥时想回去,我送他回家。至于这个窝儿穷不穷的,有钱难买我愿意,你也犯不上咸吃萝卜淡操心。”
杜成林说:“孩子明早还得去上学。”
苏凤荣说:“孩子留在我这儿睡,明早上课前我送他到学校,误不了他的课。”
杜成林说:“也不光是在哪儿睡一觉的事。开学了,孩子得交学杂费,这个那个的,又得好几百。”
苏凤荣说:“这个你跟我说不上。法院早断清楚了,房子家产都归你,孩子也落在了你名下,该咋给孩子交,你当爹的心里明白。”
儿子小声嘀咕说:“妈,我就是想你,想来看看你。学费的事,我爷我奶都张罗齐了,是我叔我姑往一起凑的。”
苏凤荣拍拍儿子的肩,心又酸上来,说:“妈知道。你爷你奶你姑你叔都是明白人,一家子就出了一个浑东西。”
杜成林跳起来:“你骂谁?”
苏凤荣轻蔑地一笑:“你请坐。我又没指名道姓地说你,你跳起来干什么?只听说有拣手表拣钱包的,还从没听说有拣骂的。”
杜成林悻悻地复又坐下,说:“好男不和女斗,咱俩好离好散,我也犯不上跟你治气。今儿来,只想取回我的一件东西。”
苏凤荣警觉了,问:“我拿过你的什么东西?”
杜成林说:“一个碗。”
苏凤荣冷笑:“我以为你还有什么好东西,原来大老远的跑来,就为取一个碗。你耍钱耍的连个讨饭的碗都没有啦?我从你们杜家出来,除了几件换洗的衣服,连房子都没要一间,我要你个碗干什么?我还不至于出了你杜家门,捧个碗去挨家要饭吃吧?”
杜成林说:“我是说我放在家里过梁上纸包纸裹的那个碗。你别挨操打呼噜,跟我装气迷。”
苏凤荣瞪了眼:“你愿坐就坐一会儿,不愿坐你麻溜儿地给我滚,这不是你的家,你少在这儿撒野!当着孩子们的面,你也敢恬着脸满嘴喷粪!”
这正中了杜成林的下怀,他只想寻衅惹恼苏凤荣,好借机闹下去呢。杜成林再次跳起身,抬起一脚,就将板凳踢飞了,那板凳直砸向挂在墙上的镜子,顿时,玻璃炸响,满地碎片。
杜成林跳着脚骂起来:“我就喷粪了,你能给我咋的吧?操你个死妈的,今天你不把那个碗给我,看我不一把火点了这个破房子!”
苏凤荣怒从心头起,也骂:“你个吃人饭不拉人屎的牲口,我看你敢!你也用不着在这地方跟我闹,有胆量咱俩另找个说理的地方,去派出所还是去法院,我陪着你!”
杜成林吼:“你想的美!东西就藏在这个房子里,你把我引走了,好让你的野男人转移赃物啊?没门!今儿你不把东西给我拿出来,就别想让我走出这个门!”
虽已入秋,夏日的余热还盘踞着大地,家家户户入睡前多还大敞着门窗,村街上也坐着不少纳凉歇乏的人,听到这边有人扯着嗓子吵骂,立时围来不少看热闹的人。屯里人早知于旺田有了一个还没正式结婚的续老婆,也猜知那个跳脚吼骂的汉子是谁,可有人见水秀躲在院子里抹泪哭,还是问:
“那个打上门来的是谁呀?”
水秀答:“是俺苏大姨以前的男人。”
问话人说:“那你只知哭啥呀,胡子都杀进门了,还不快把你爹找回来?正当其主的一家之长归了位,他就得立马滚犊子!”
水秀闻言,撒丫子就往屯外跑,一路上磕磕绊绊的,摔了个前趴子,又闪跌进水渠里,女孩子也顾不得疼痛和满身泥水,爬起来继续往田野里跑。总算见到爸爸了,水秀往畦埂上一蹲,就呜呜地哭开了。于旺田大惊,忙问咋啦咋啦?水秀一把鼻涕一把泪,哭着说:
“爸你快回家看看吧……苏大姨她原先的……那个男人闹到咱家啦,还说……还说要烧咱家房子呢。”
于旺田一股火腾地直从天灵盖蹿出来,拔腿就往家里跑。跑出不远,听到身后有脚步声跟着,忙又停下,对水秀说:
“你跟着我干什么?回去看蟹子!”
水秀说:“我跟你回去看看,那人还要打苏大姨呢。”
于旺田吼:“他敢!你回家屁事不顶,快回窝棚去,看好蟹子!”
水秀只好停下来,眼望着爸爸向着村里跑去了。
隔着不远正支楞着耳朵大瞪着眼睛留意着这一幕的朱景发大喜,调虎离山之计果然奏效!见水秀又被撵回来,他也没当回事,大人都被我用计调走了,我还在乎你一个小丫头片子?翻翻手心的事嘛。他走到于家窝棚前去,对水秀说:
“家里出事了,你还待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快回家看看去。”
水秀说:“我爸让我留下替他看蟹子。”
朱景发说:“这儿不还有我嘛。快回去,看蟹子也回家换身衣裳,这一身泥水的,女孩子家家,小心溻病了。”
水秀说:“没事,天不凉。再说是夜里,谁也看不见,泥水咋?”
朱景发说:“那是你刚才跑的急,身上热。等一会儿露水下来,你看冷不冷。我夜里都得披棉袄呢。”
水秀仍不动:“窝棚里有我爸的大衣,一会儿冷,我也披上。”
朱景发眨巴眨巴眼,再生主意,说:“你这孩子,咋不听话呢?咋不知心疼你爸呢?你爸拙嘴笨腮的,真要骂架,他跟得上趟儿?跟不上趟儿就可能动手。你爸又哪是会打架拼命的人。你苏大姨家的那个男人我认识,又蛮又狠,块头儿也比你爸大,真动起手来,你爸肯定吃亏。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你亲妈死了,你哥又不在家,这种时候你当亲闺女的不往上冲谁往上冲?还指望两姓旁人啊?到时候抱住那王八蛋一条胳膊也是好的,你爸就能缓出手来往死削他了。”
水秀仍犹疑不动:“我可不让我爸打架,谁打坏谁都不好,都得摊官司。”
朱景发说:“能不打当然最好啊,正经人谁没事盼着打架玩,有病啊?骂人没好口,打人没好手,两边人我都认识,又都是我的朋友,我也盼着别打别骂。可不打不骂,总得说理吧?有争理的就得有评理的,谁评最合适?你快去把村支书于水丰找家去,村支书一进门,保证就把想闹事的震唬住了。于水丰给你爸叫叔,又是一村的,不管论私论公,胳膊肘也不会往外拐。你说是不?”
水秀终于动心了。于旺田是厚道人,朱景发以前偷蟹子的事只放在自己和苏凤荣的心里,从没跟孩子讲过。一个单纯的女孩子哪知社会与人心的阴恶,又哪会疑心防范呢?她说:
“那我就找水丰哥去。你可替我好好看着蟹田,千万别睡觉啊。”
朱景发说:“我睡啥觉,我家还有蟹子呢。你爸不回来,我一夜不合眼。你放心吧。”
水秀急急地去了。朱景发待水秀的身影在夜色里一消失,立刻从自家窝棚里摸出早备好的抄子,故伎重演,下手偷蟹了。此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干就耗子操牛,干大的,而且分秒必争,哪一抄子下去都是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