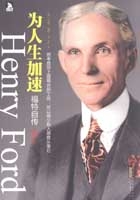酒席散后,于水丰让于旺田搭乡里的车回去,说自己在城里还有事要办,便留下了。临分手时,还悄声对于旺田说,后晌我去找吕书记,争取把给你贷款的事定下来,不能再拖了,再过些日子一起蟹,话就不好说了。于旺田两眼顿时放光,说谢谢啦,谢谢啦,没想我于老旺真要时来运转啦!
于水丰一定要当面跟吕书记谈一谈。于水丰不是那种看不出眉眼高低的人,午间在酒桌上,他也知道吕书记在说官话,在敷衍他。可他确实想跟吕书记谈一谈,为于旺田,为村里的工作,也为吕书记好。他自信有这个把握,他能说服吕书记理解他,信任他,支持他。他肚里已窝了好多好多的话,反复斟酌,再三酝酿,但最主要的,还是为吕书记雇于旺田养蟹的事。
乡间农民,同居一屯,谁家婆媳不睦,谁家兄弟成仇,甚至谁家鸡下了双黄蛋,谁家猫狗一窝生了多少崽,都是家喻户晓的新闻,就别说养蟹高手给县里的大官卖工夫了。朴实而不失狡黠的乡下人也曾为大官雇人养蟹生出反感,但那反感很快就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淡漠下去,随之生出的却是顺风扯旗、借坡上驴的狡黠与智慧。人们不甚关心于旺田一月可得多少工钱,他们关心的是于旺田在田里养蟹秋后还要不要交特产税。
这一带兴起养蟹并渐成气候后,因养蟹的收益一目了然,农民除了每年必交的提留统筹款,特产税已成了一笔更大的上缴费用,前几年是每亩五百元,去年已增加到一千,乡里已有话,今年可能还要往上涨。田地是国家的,从水库引来的水也是国家的,用国家的资源挣来的钱要给国家上税,国家再用这些钱养军队养官员办教育办公共福利事业,这是天在上地在下板上钉钉的公理,没人敢说出个不字,心里不情愿也得受着国家法律的约束,不交就是抗税,抗税就是犯法,犯法自有公安法院监狱收拾你,乡下人懂得这个道理。
可乡下人也从于旺田给别人养蟹的事情中发现了一道也许可逃纳税的缝隙。于旺田一月只得了四百元钱的工钱,他不可能再交特产税,要交也只能东家去交;可东家不是乡下人啊,村委会和乡政府都管不着啊,尤其是那东家还是有权势的,乡长村长们也未必敢去跟人家要。于是,人们便发现希望的曙光了,也发现了迎接曙光的招法,一个个放出风去,说我的蟹子也是替城里人养的,有人还把城里的亲戚朋友找到屯里来,故意在村街上和田野里张扬。还有下棋会看五步的,已光明正大地和城里亲戚朋友签了合同,还去县里办公证,私凭文书官凭印,秋后只要于旺田的东家不交特产税,人家也早有了备雨的蓑衣,不信你一条河还能冻出两样的冰。
于水丰先在县街上转了一阵,估计吕书记已回到县委机关了,便奔了县委大院。门卫师傅看他紫紫黑黑的脸庞,很坚决地拦住了他。于水丰报了姓名和身份,又说已和吕书记有约,门卫师傅便抓起电话机。接电话的是秘书,门卫师傅在抱着话筒等待指示的时候,还对于水丰说:
“不是信不着你,这是规矩。”
于水丰连点头:“知道知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秘书很快回话,说吕书记正开会,没时间。门卫师傅说要不要你直接跟这位同志说一说?可这话只说了一半,电话里就咔地撂断了。门卫师傅便很不高兴地对于水丰说:
“你看你,还说约好了,好像我不会办事,故意给领导找麻烦似的。”
于水丰知道县里衙门的勤杂人员也多是从县郊农村雇用的,便递棵烟过去,又说了声谢谢,离去了。
于水丰并没走很远,他坐在县委大门斜对面百十米处的马路牙子上,开始计划中早已意料的等待。头顶有树荫,立秋后的大日头虽还毒热得号称秋老虎,但只要躲到荫凉处,便觉清风拂面,凉凉爽爽。是稻黍晒米的时节了,只要不再有特殊的狂风暴雨,一年的收成已基本可成定数。三春不如一秋忙,庄稼人又该忙上一阵了。
日爷儿一点点西斜过去,树荫一寸一寸东移过来。于水丰的身子随着树影移,已移了五六次,马路牙子下便丢下了一溜儿的烟尾巴。县委大门口终于有人往外走,有步行的,有骑车的,也有坐小轿车的。于水丰认识吕书记的那辆红旗轿,那辆车一后晌都停在院子里。于水丰早有了打算,如果吕书记下班坐小车,那他立马打出租,妈的,咱屯老冒也豁出潇洒它一回了,跟上他,一直跟他到家门口,到那时再跟他打招呼,说正事,我就不信他还能说什么忙不忙的。
可吕书记一直没露面,县委大院里已安静下来,那辆红旗轿也还停在院子里。这可是计划中没算计到的,这会咋开得这么长?下班也不回家?于水丰终于忍不住,又踅回县委门前去。门卫师傅很吃惊,问:“咋,你还没走啊?”
“我是真有急事,要跟吕书记当面说一说。我们乡下人进趟城不容易,不知吕书记啥时能开完会?”
门卫师傅扭头瞧瞧大楼,放低声音说:“开啥会。天头正长,吕书记下班后好甩两圈扑克,你要真有急事,就再等一会儿吧。”
于水丰不便在门前久留,道声谢,就又避开一段距离等着去了。
待街上多了些吃过晚饭后三三两两散步的人时,吕书记总算出来了。但吕书记没坐车,而是和那几个人一路走,一路说笑,那说笑声也不避人,不外是些你臭我臭互不服输的玩笑话。玩笑话说得也很投入,经过于水丰身旁时,没发觉有人正关注地望着他。于水丰跟在人们的后面,直到一个个分手离去,只剩了吕书记一个人时,他才快赶几步追上去。
“吕书记。”
吕书记站下了,神情一怔:“你?”
“我是于家台村的村支书于水丰,午间吃饭时……”
“哦,知道知道。开完会你没回去呀?”
“有几句话想当面向您请示,就留下来了。没想您这么忙,开完大会,午后又有会。”
“可不是。急着有几个人事安排上的事,戗戗来戗戗去的,就又到了这时候。哪天吧,到我办公室,好不好?”
“我就几句话。陪着您往家走,我就说完了。”
吕书记却伫步不动:“那你就长话短说,拣要紧的。我饿了,你还得抓紧赶回去,是不是?”
领导这么说了,于水丰就只得把早存在肚里的话再拧再榨,把虚虚泡泡水了巴叽的客套与委婉都省略去:“行,那我就下笊篱,专捞干的。我们屯今年的收成估计错不了,主要是水稻和养蟹这一块……”
“这我知道。”
“于旺田为您养的蟹……”
“我声明一点,”吕书记做了个手势,很正色地打断说,“我可没雇谁养蟹。或者换个角度说,于旺田的东家另有其人,但绝不是我。”
于水丰眨眨眼,心里的犟劲有点儿不听话地往上涌:“对,对,东家不是吕书记。但吕书记亲自陪了亲戚下蟹苗,又几次去蟹田,屯里人看到了,就都以为那几亩蟹子是您的。”
“我再声明一点,”吕书记的脸色越发冷峻,“我去于家台村,可不仅仅是去看那几亩蟹,我主要是去搞搞社会调查,了解一下蟹农的生产和生活情况。现在全党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稻田养蟹又是我们县的特色产业和主要经济增长点,我作为县里的领导成员之一,对这方面多些关注和了解,应该是不错吧?”
“我没说错,屯里人也没说吕书记不该去。可乡下人土命,心实,好认死铆子,就一口咬定,说那蟹子是吕书记的,我可咋整?”
“你要多做解释工作嘛。”
“我说了,也解释了,可没用。拉屎怕瞧,写字怕描,有些事是描不得的,就好像拙老婆画眉,越描越显眼,越描越难看。”
“那就随他去,谁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天塌不下来。”
“也不光是说不说的事。屯里不少蟹农都从城里找来亲亲友友,有的还真真假假的签了合同,都说自己也是在给别人养蟹。”
吕书记怔了怔:“怎么个意思?”
“秃子头顶的疤癞,还不是明明晃晃的事。秋后为吕书记养蟹的稻田要交特产税呢,大家都交;吕书记的要不交呢,傻子过年看界比子(隔壁),那就谁也不会交了。”
吕国清听出来了,这才是这个村支书今儿拦着自己要说的核心话题。他沉吟了一下,说:
“要不要我再声明一次?我并没在你们于家台村养蟹子,你回去跟大家说,别攀我,攀也没用。至于特产税的事,事关国家税收政策,我不好枉作评说。但你能注意到蟹农们的倾向,很好,可以直接向你们乡领导反映,乡税务所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对此倾向会有所考虑。”吕书记拔步要走了,“你今天找我,要说的是不是就这事?要没别的事,时候不早了,就这样吧。”
于水丰执拗地追上一步:“不,吕书记,我还有两句话。作为一名村里的基层干部,这话我一定要说。有些事,还是水没来先叠坝的好,不然,秋后屯里真要出现抗税事件,我也难脱责任。我有个主意,或者说是建议,不知当说不当说?”
吕国清望定这个倔强的村干部:“你说吧。”
“如果吕书记真想帮助于旺田彻底脱贫,最好您帮他贷下两万元款,于旺田有了这笔钱,就可先补上蟹苗款,又可将养蟹这几月的饲料等项支出都补上。你们双方若是再彻底解除雇工养蟹的口头合同,那这一天云就彻底散了,于旺田的饥荒秋后可以堵上,那些养蟹的再想攀谁也没用,我们村干部的工作自然就好做了,吕书记您的威望与名声也一定会比以前更好。”
吕国清的心悠了悠,又沉了沉,一股忿恼之火已涌上来。这才是今日话题的核心之核心,关键之关键!刚才真是轻看了这位黑黑瘦瘦貌不惊人的小村官了。在他看似平和的陈述与建议中,已暗含杀机,迫自己就范。如果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这位小村官的建议确不失为一种上策,两万元钱就可摆平可能将起的风波,还为领导者树立了形象,赢得了民心。而贷区区两万元款,对一位县委副书记来说,不过是一个电话一张条子的事。但自己不是旁观者,从今晚这个谈话看,这个小村官显然已不自量力地把县领导当成了角逐对象,就好像场上的两个乒乓球对手,他胜即我败,我败即他胜。如果自己接受了他的建议,那无异于临场交拍,表面是言和,本质上是认败。若是败在同级的政敌之手,兵家常事,或可无辱;可这是个上不得花名册的不入流之辈呀,败在他手,若传出去,脸面何在?自尊又何在?哼,小小一个村屯,即使你村官带头抗税又能如何?我不信你小小泥鳅还能掀起滔天大浪!
吕国清心里冷笑,脸上却掩饰着愠恼,很外交也很平静地说:“我第三次向你,并通过你向所有误解的人声明,我没雇任何人养蟹,也不是任何人的东家。至于你建议给扶贫户贷款的事,这在县里尚无先例,这个口子能不能开,还需我跟县里其他领导集体研究,统筹解决。但我个人意见,这有越俎代庖之嫌,这个工作乡里就可以做嘛。你可以把这个建议向乡领导提,但愿他们会有比较稳妥的办法。”
“越俎代庖”不懂,但吕国清的意思还是听得明白的。于水丰说:“我跟孟乡长提过,开春时就提了。”
“乡里没有办法,我更不好隔着锅台上炕了。”
“你们县领导,本来就坐在炕上。”
“哦,比方没打好。”吕国清对这抗上不尊的口气愈发忿恼,但他故作不觉,轻松地笑说,“那就是隔着锅台下地,程序也不对嘛,是不是?好,要没别的事,我回家啦。”
于水丰呆立在了那里,他本是充满自信,一定能说服吕书记的,绝没想到如此合理的小小建议,竟被毫不客气地否定了,回绝了。是吕书记真看不出三步棋,还是人家根本没把老百姓可能要闹起的抗税风波当回事呢?再回头细想想,也可能是因为自己说话的口气太硬了,在外面马路牙子上坐等了半天,人家在大楼里拒而不见,明明是甩扑克,还人模大样地说在开会,这就让自己在心里窝了火气。窝了火气的人,说出话来还会好腔好调低三下四吗?唉,这事整的!
吕国清走出十几步,可能意识到了自己这般离去有失领导者的风度,甚至有落荒而逃之嫌,便又站下来,回身大声笑着说:
“哎,小于呀,你叫于什么来着?”
“我叫于水丰。”
“好,水丰同志,听得出看得出,你这个村干部还是很有头脑啊。非常感谢你向我反映的问题,也感谢你的建议,即使不可能被采纳,县委也要吸收其中的合理内核和有益的成分,这是我们制定政策的依据和重要参考啊。哎,回去方便吗?要不要我派车送你一趟?”
“不了,天头长,有大客车。”
“那好,欢迎你哪天进城,到我办公室坐一坐,咱们再聊。”
这一幕,街上不少人都看到了。吕书记的声音很大,也都听到了,引得人们伫步往这里看。于水丰心里骂,本来是有理的事,这一整,倒好像自己成了小嘎官儿,大老远屁颠屁颠跑来巴结领导打小报告啦,还得是人家会做人呀!
夜幕垂下来了,街灯亮起来了。于水丰摸出一棵烟,可打火机左按右按就是只冒火星不起火,他骂了一声“他妈的”,就把打火机远远地甩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