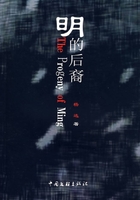夜已很深,天空暗云低垂,昏昏暗暗地遮没了月色,也遮没了星光,村庄与田野的轮廓连在一起,到处是墨一般的浓重。四周静得连草动的声音也听得清楚,只有草虫在不倦地嘶嘶吟唱。
于旺田因心里有了对朱老九的戒备,没出屯口便熄了手里的电筒,又故意往东绕出一二百米,从另一条水渠向自家稻田走去,脚下也放轻了许多。
于旺田悄悄地向自家稻田靠近,果然就见朱老九的身影正在田埂上忙碌。于旺田伏下身,悄然蹑行,近了,再近了,只剩了三五步远的样子。只见朱老九正全神贯注地将一只一米见圆的偌大网抄放到于家蟹田里去,网抄上撒了些豆饼碎末,吸引稻田里的蟹儿爬进网抄,他便猛地将网抄兜起,次次不空,都能捞上十只八只的样子。他将网抄里的蟹子甩进自家的稻田去,直起腰时回头往村庄的方向看一看,那是在防备于旺田的出现,却没料想蟹子的主人早已潜伏在了脚下的暗影里。
蟹农起蟹,一般用两种办法,一是在田埂上打开一个缺口,围上网兜,网兜里丢些饵料,池水哗哗奔泻,蟹儿自然顺水奔食而来,蟹农只管提起网兜收蟹就是,这是一网打尽法。另一种办法,是在稻池里深设缸瓮,缸口与稻田地面平齐,缸里撒些诱蟹的饵料,贪食的蟹儿循味而来,自然纷纷落入缸瓮之底。八爪蟹公没有攀附光滑壁面的本事,只好束爪待擒,此为分批捕捞法。朱老九两种快捷之法皆不用,另用笨招,眼见是为了出手快,缩手也快,贼图方便,又不至留下蛛丝马迹令于旺田起疑。
待朱老九再起出一网抄,并扭头向屯口张望时,怒火中烧忍无可忍的于旺田突然腾身而起,照着朱老九后腰就是重重一脚,怒骂:
“朱老九你个王八蛋,让你偷我!”
毫无防范的朱老九扑嗵一声扑到水田,待他一身泥水从蟹田里爬上来时,竟嘿嘿地冲着于旺田笑:
“哟,老旺哥呀,干嘛发这么大的火?”
于旺田瞪圆两眼,却不会骂出什么花花样:“你个浑王八犊子,口口声声说替我守田看蟹,没想你就是贼!我咋就瞎了眼!”
朱老九仍是笑:“我哪是偷了你的蟹,我是闲了没事,捞起你家的看看比我的大多少。”
于旺田指着网抄骂:“看蟹用这么大的抄子干啥?你抄出蟹来往你家田里甩干啥?你当我眼瞎没看见!你个王八蛋!”
夜里的声音传的远,附近已有几处窝棚亮起了灯光。朱老九扫了一眼,压低声音说:
“老旺哥,你压压火,别吵儿巴火的,行不?我哪是偷你,我偷谁也不能偷你老旺哥的呀。我、我是可怜你老旺哥,日子过得艰难,忙个一春一夏的,怕是秋后连只蟹爪子也摸不着。我、我是为老旺哥你着想哩,这事得咱哥俩商量着办,让别人听见不好……”
于旺田愣了,问:“你偷……还偷出理了,咋个意思?”
“还咋个意思,这老旺哥还不明白吗?”朱老九说,“我早跟你说过的,把你田里的蟹子移到我这边一些,秋后的好处咱俩对半扒。那县里的官为啥不劳而获?咱取他一些不义之财也是应该应分的。我是见老旺哥一直不肯点这个头,才不得不替你下了这个手。”
于旺田恨道:“放屁!我于旺田虽说人穷,志却不短,伤天害理鬼鬼祟祟的事一件不做,昧良心的钱一分也不往兜里装!”他说着,肚里的怒气不由又冲上来,“中了,我不跟你费唾沫了,你跟我找个地方去说理吧,也免得我秋后说不清楚,受吕书记和孟乡长埋怨。”
朱老九一惊:“去哪里?”
“去乡派出所。”
朱老九傻眼了,他知道去乡里将是什么后果,他偷的是县太爷的蟹子呀,蛤蟆攥进了孟乡长的手里,还不得活活让人家给捏出尿来?再说,他是乡里有名有号上了名册的惯赌人物,这回再加个偷,且是偷当官的,就是不送进牢里关押个一年半载,怕是也少罚不了。这么一想,他就软了两条腿,上前紧紧抓住于旺田的手,求告说:
“老旺哥,不行,这可不行啊!兄弟求你了!你把兄弟往那种地方送,兄弟不死也得脱层皮。兄弟家里还有好几口人呢,我老娘七十多岁了,一股火症,还不得丢了老命啊!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佛面看凤荣嫂子面,就从我介绍你和凤荣嫂子认识这一层上说,你也千万不能把事做绝呀!我求你了,我知你肚里有气,打我两拳踢我两脚都成……要不我趴下给你磕俩头,我知你和凤荣嫂子都是面慈心善的大好人,才给你们俩往一起捏鼓,我可没少给你旺田哥说好话呀。凤荣嫂子那人还行吧?你兄弟没瞎白话诓你吧?那可真是打灯笼也难找的好女人……”
于旺田心软上来,冲朱老九的这番哀求,也冲他介绍苏凤荣的那个情谊,那真是个知疼知热有情有义天下难寻的好女人啊,咱于旺田即是有天大的理,也得网开一面,不能做出绝情绝义恩将仇报的事情。再说,稻田里的蟹子确也不是自己的,少个十斤八斤的就少吧,吕书记哪里就知是多少,就算还了朱老九的这份人情债,一来一往,扯平了,咱也不再欠他的了。这般想着,他便冷冷地问:
“你从我田里弄出多少蟹子?”
朱老九见欠缝儿了,有门儿了,忙说:“也就三五抄子,一抄子十只八只的,你都亲眼见到了的,还能有多少?”
于旺田还是问:“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是多少?”
朱老九说:“我说的就是实话,撑破大天也超不过三五斤,我倒想再多抄出几抄子,哪曾想你放着现成的女人不搂着睡美觉,还大半夜地跑回来查岗啊。不信等天亮咱俩都往出起蟹子,我池子里要多出你的来,就都算是你的。嗨,也真是的,刚完事儿你就往回跑啊?种驴种马完事儿还让歇歇乏呢。要不,是凤荣嫂子还跟你绷,不让你沾身?她是黄花闺女呀?”
于旺田斥道:“你小子的嘴,还不如老母猪的……啊呸!你啥时候说过一句正经话!放屁都掺假!”
朱老九急着赌咒发誓:“我要是有一句假话,上马路让汽车压死,端起瓢让凉水呛死,摔个前趴子让石头硌死,放个屁嘣脚后根……哦对,放啥样的屁也死不了人……再说了,我跟你说的凤荣嫂子的事,没掺半点假吧?她炕上侍候你的活计还行吧?”
于旺田见他胡诌八咧嬉皮笑脸越说越下道儿,便不再理他,转身钻进窝棚,坐在铺板上,还在呼呼生大气,连划火柴点烟手都直哆嗦。蓦然间,他的心又抖了一下,妈的,这小子非得在这时节死乞白赖地给我介绍对象,显得比我还急,又自作主张地把女方领到屯里来相亲,会不会是早就拴好的套子在诱我钻啊?听说麻将桌上就有抽夹设套的鬼招子,好在凤荣还真是个好女人,提醒自己早回到田里来,不然,可就让这小子诓大啦……
朱老九先回了自家窝棚,很快又踅回来,褂子脱去了,光着膀子,却还是那条泥泥水水的裤子,手里抓着半瓶二锅头,涎皮笑脸地说:
“老旺哥,整两口,这东西壮阳补身子,尤其是刚卖完力气,绝对解乏。”
于旺田不愿搭理他,脸扭向一边去。
朱老九说:“还生气啊?实在心疼县里官儿的几只毛蟹子,抄子就在外头,你再从我的田里捞回去,随便捞,愿捞多少是多少。为这点儿破事伤了和气,气坏了身子,多不值,是不?”
于旺田抓起酒瓶,咕咚咕咚就是两大口,像喝凉水,然后摆摆手,说:“滚蛋滚蛋,玩勺子去,我不愿搭理你!”
虽说还是骂,口气已缓和了许多,是那种兄弟之间达成了谅解的骂。朱景发抓着酒瓶,心满意足地走了。
一股夜风吹来,很凉很凉,毕竟是秋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