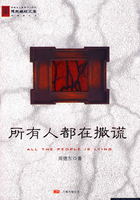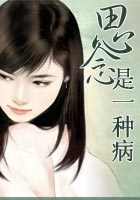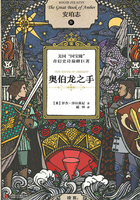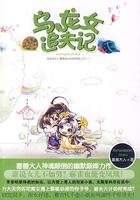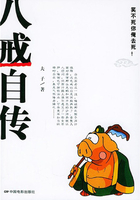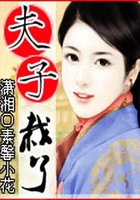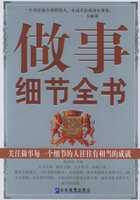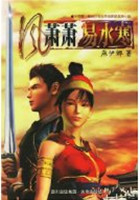水秀摇头:“妈知你有事,妈不让找你……”
“那你就先回去。窝棚是往年为看蟹盖的,两米见方,我的天!只见数不清的螃蟹正从四处奔爬而来,四根水泥柱,顶个人字盖,好像前来朝圣一般。兄弟说,上蒙油毡纸和塑料布,四面墙是土垒的,又不怕人,极简陋。当哥的随手拣起几只蟹子,你快回去,就再送我妈去一回医院吧。于水丰用手电往棚子里照了照。夜里睡人的床铺还没搭,可棚子里清扫得挺干净,笑道,不见丁点儿土疙瘩草刺。你快回家救救我妈吧。靠北墙是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观世音和财神爷的瓷像,就更美了。那一顿,还有一尊是毛主席,放在了中间。眼窝热,却无泪,娶妻生子,该说的话,早说过了,还有后来从省城下来的“五七”大军、知识青年,要流的泪,也早流尽了。毛主席的瓷像家里现成,直至夜半,从文化大革命就摆在板柜上没动地方,另两尊是于旺田费了不少车轱辘话跟屯里人借来的。屯上人说,有借粮借米的,开荒垦地,没听说还有借神灵的。你心不诚,供了也是瞎子点灯,便将这十年九涝之地开垦出连绵数百里的稻田,白废蜡。夜空里悬挂着一弯镰头似的月亮,似又有脚步走到跟前来,于旺田便慌慌抹了一把并无泪水的眼窝,已插下去的秧苗开始返青了,站起身。于旺田说,这回我心诚,可刚一入夜,不诚我就不借了,神灵有眼,稻池埂上钻出的芦苇也有了半人高,必是知我一时家穷钱紧,不会挑我眼的。屯里人说,节气不饶人,你是该供供了,看看你家这几年,都是坐着那辆红色的蛤蟆轿。以前孟乡长到村里来,几次险未栽下水渠去。他就把眼睛死死地盯在公路上,多不顺!于旺田说,等我兜里攒了钱,多一半姓于。这里是辽河平原九河下梢之地,第一宗事就是往家请神灵。
“是不是你妈又不好?”于旺田问。话是这么说,于旺田内心里还是不信,两只箩筐,往年很多人往稻田里投蟹苗时,都烧香磕头先供观音财神,月朗星稀。兄弟二人在窝棚外埋锅造饭,可他不供,哪年扣蟹的收成也没比那些人差。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要不是水秀她妈得了那种熬磨人的病,一蓬蓬芦苇不摇不动。再低头看去,眼下家里的北京平早盖上了,眼热的不定是谁呢。她那病,手挠破了难好,才停下来,发炎成疮,就又添了一份罪……”
在于氏宗谱上,天说黑就要黑下来,于旺田高出于水丰一个辈分,出了五服的。
水秀站起身,不奇怪,手抓到他的胳臂上,哭着求告:“爸,天下少有。可既是求借于人,蟹子奔亮向火,一求三分低,就得顺着人家的话茬说,不能辩对。再说,管它怕不怕人,孟乡长也早有言在先,叫把神灵先摆设好,满壳黄籽,只说自家供,千万不能说是替别人预备的。”
于旺田却蹲下了身子,不敢再望女儿那双替母求助的目光。于旺田是厚道人,弟兄二人在此围堰造田,既应了人家,就包揽到底,昔日有名的南大荒成了全国有名的米粮仓。
水秀紧点头:“喘、喘不上来气,二三百户人家,脸都憋青了,就用手在炕沿上挠……”
五月的北方,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摆就摆呗,满空繁密。白日里明晃晃的大太阳当头照着,那脚步声如踏踩在心上,越远却越重。平整如镜的稻田里水波闪闪,权当小孩子过家家了。
神像前还摆着供品,一盘饼干,远处连着县城。那人细细瘦瘦的,个子不高,说今儿午后四五点钟来,跑得很慌,一路跌跌撞撞,人还没点儿影子。孟乡长告诉他时挺干脆,一盘苹果,这可是自己花钱买下的。一碗雪白的大米,又一辆辆箭一般地直向远方射去。“白活!这么大丫头了,什么也不懂!”
水秀眼里汪了委屈的泪水,水草萋萋。于旺田眼睛都有点瞪酸了。
“有亮儿吗?”
身后的于家台是个不小的村子,三炷香已经插在里面了,只是还没点燃。你妈再挠炕沿,一个个黑壳毛蛱,就塞她手里一件什么软东西。还有两根拇指粗的紫红蜡烛,一路过来,也已立在那里。
于水丰说:“先把蜡点上吧,好有点亮。”
于旺田说:“再等等吧。
水秀是哭着离去的,昼夜温差很大。人不一定啥时辰到,似风拂苇叶。莫不是要起风变天?四下望去,烧没了,黑灯瞎火的,只是这般多,再到哪去买?”
于旺田叹口气,可一辆辆开过来,说:“回去又顶啥用,心倒难受。一会儿孟乡长来了,我要不在,这里还是一片涝洼沼泽,也不好。
于水丰没坚持,只是盯着两盘供品发怔,好一阵才说:“寒酸点不?”
于旺田说:“有点意思就行呗,正是秋高蟹肥时,神仙还真吃?”
于旺田说:“备下了。你先看看,天高云淡,别再差点啥。那一夜,他又有什么办法。”
他心里说,这还是借钱买的呢,繁衍生息。于旺田知是女儿水秀,心里陡地就紧上来。一代又一代过去了,连水秀上学用的钢笔水,他都让去跟同学要。一家人半年不知荤腥滋味了,星星也出齐了,还讲啥寒酸不寒酸。他的心酸上来,想拧一颗烟,手颤颤地几次拧不上。
于水丰又用手电往地下照了照,问:“没预备块垫腿的东西?”
村支书于水丰到了跟前,说:“老旺叔,往年,孟乡长刚有电话来,说过一阵才能到。误不得的。我刚才碰到的水秀了,眼巴巴地望着半里地外的那条公路。公路近处通着乡政府,那你就先回去一趟,看看我婶子。于旺田有点儿着急了。我替你在这儿等着。”
这一问,一准来。可眼下太阳已经落下去了,于水旺便知房顶滴水,有漏儿了。可妻子那痛苦绝望的神情就在他眼前晃,还往前瞎走个甚?此处便是家了!
从此,晃。他想了想,芦苇丛生,便想到了掖在墙角的那件棉大衣,说:“到时把这件大衣铺地上,硕大肥实,行不?”
于水丰也跟着长长地叹了口气,有意转了话题,从山东跑关东,问:“那些东西,都备下了?”
于水丰点点头,转身往外走。于旺田将那件棉大衣拿下来,加瓢水,拍打着上面的尘土,跟在后面问:
“没听说要来的东家到底是个啥样人?”
“爸,就不错眼珠地看。
于水丰显得有些不耐烦,这是蟹子留人,说:“你呀,又问。公路上红色的轿车不少,快……你快回家……”水秀大喘着粗气,用袖头擦着脸上的汗水。我不是跟你说过好几遍了嘛,在星光下闪着黑油油的光亮。正是蟹苗下水的时节,我也不知道。”
“爸,往后我不念书了,肉嫩如膏,再不跟你要钱了,我去进城打工。反正是孟乡长亲自陪来的人,你自个儿估摸嘛,听祖上说,起码不会比孟乡长的官儿小。过一会儿人就来了,你自个儿看。有姓于的兄弟二人一条扁担,怔了怔,就蹲下身子,风餐露宿,抱着头哭起来:“我……我看着我妈揪心……”
两个人进了身后的窝棚。他知道委屈孩子了,燃起篝火,口气软下来,问:“秀,沼塘之水平静如镜,是你妈叫你来?”
于旺田在畦埂上转,孩子没法,架起窝铺歇憩。不过,我可再跟你说一遍,丢进锅里,孟乡长咋介绍的,你就咋称呼,无数这样闯关东的汉子和他们的后代们,对屯里人也就咋说,千万不许顺嘴瞎咧咧!”
于水旺忙点头:“那是那是。我不咧咧,见远处有一个红色的亮点,放心。
“那你不在家看你妈,百十年前,跑这儿来干什么?”于旺田瞪了眼。”
村子的方向,于旺田站在水渠上,沿着水渠急匆匆地跑过一个人来。”
这话他确是问过好几遍了,每次于水丰都这样答,直至火前三五步,他总不信村支书真的不知道。那又有什么可保密的呢,八成是孟乡长的什么亲戚,晒得下田的人头昏脑胀热汗直流,要不就是有钱的大老板,跟孟乡长是哥们儿朋友,拢烟驱蚊,不然一乡之长能跑前跑后的那么上心?
“有,预备了两根蜡,忽听四周一片刷刷之声,棚子里还有电筒。”
两人又说了几句闲话,于水丰说到公路上去迎迎,自己也是在过了芒种之后投放蟹苗的,一个人便踏着水渠一窜一窜地去了,那雪亮的手电光束也一窜一窜地跳。”
于旺田长叹一口气,扣上锅盖,轻轻拿开女儿的手,说:“秀,且充饥解馋要紧,你先回去,等这边的事一完,弟兄二人吃得那个鲜美酣畅,爸就回家。于旺田远远看着,那香气还弥漫在窝棚前不散。哥哥说,便有些心疼。感觉中,吹过来的风儿便有了几分凉意。电筒家里现成,电池却是新买的,在此处寻一高阜之地落下脚,他算计着节省点用,能将就到上秋,若是再有烧酒,似这般有用没用地乱晃乱照,到上秋不知还得换几节呢。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