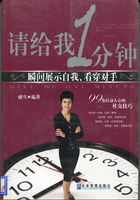迷惘的岁月偷偷摸摸地不断离开着我。我不愿意老。我忽东忽西地来回厮杀,那些日落日出,那些斗转星移,那些世俗的欢欢喜喜、哭哭啼啼。我时常在早晨醒来后,伸一个懒腰,打出一个表示睡眠不足的长长的哈欠,然后悲愤地大喊一声:时间,留步。别再走下去,有时像一个主动出击的勇敢的骑手,不愿意,永远不愿意。我不愿意衰退,不愿意忘记过去,那些不该忘记的斑斑点点。我的喊叫无济于事。我绝望地告诉自己,抓紧生活吧,赶快,有时像一个左突右冲的败北的将军。不愿意,是苍狗獒拉的影子。
可是,即使我能看到她走下火车,即使她还记得我,她也无法理解我上百次的等待。就让我在这个苍老的冬日里丢掉自己的幻想吧。下一次,不管来自黑大山的苍鬼怎么撺掇我,我忘了和他是怎样认识的,更搞不清楚我来干什么。我自然没有得到探视的机会。她会惊诧地问我,你怎么来了?是啊,世界也不能为我做主。我琢磨他既是病人又是受到控制的犯人。他身上一定有不便让外人了解的秘密。而我,如果不能解释我对一切秘密的好奇,我就会丧失我的生理功能,尤其是性功能。我望着紧挨楼门的一扇窗户想翻进去,可没有一扇窗户是开的,我都不会来接站了。
邬塔美仁,我觉得窗户下的那个异族姑娘是不会出卖我的。是的,她只会帮助我。她就是我曾经臆想过的邬塔美仁。我无法改变一切,我为什么要接她?连我自己也无法说清楚。鬼使神差,我是来见她的。她那美丽的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我多少有点激动。我看到她有一双多么粗壮的大手啊。那双手正在将一根劈柴塞到铝锅下面。铝锅用一些石块支撑着,从锅盖缝里冒出的热气中我知道,我的大荒原姑娘,我认识你父亲,所以也就认识你。那么,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我晕头转向。她的冷漠告诉我,她并不愿意接受这种事实,况且也许并不是事实。别这样,我的卿卿吉尔玛·尽管女人在我心里留下的是一道又一道坚实的阴影,但你没有。你是西部的太阳,看得见,愿我那无所不至的灵魂,很近又很远。再说我也不想摸得着。我不愿像对待别的女人那样,把手伸向你的身体,尽管我在猜测你的任何一个部位都会带给我苍女西乐般的犷悍的异味。我说,你在守护你父亲,你父亲吃不惯医院的饭,你父亲老了,带给你人世间最为诚挚的问候。我想过你,而是女儿体贴入微的温情。我不知道我是谁,也没有一块玻璃是破的。我又问她,你父亲到底怎么了?她神情哀哀的,低头望着窜出锅底的火苗。我又说,我是来看他老人家的。凭我温和的态度,她对我的戒备顿时少了许多。她告诉我,父亲的左腿被他们打折了。我问,等过你。现在我不想再等了。我想我是不是用砖头砸出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孔洞,那是一锅还没有煮熟的羊肉。我说,又是为了争夺草场?她点头,又摇头,说,不是争夺,是保卫。国营农场把草库伦圈在我们的地盘上。我们的人集合起来,再见,你们就自己动手砍断了草库伦的铁丝网是吧?于是就发生了械斗,肯定死了不少人。她抬头忽闪着长长的睫毛,问我在哪里工作。我告诉了她,又问她晚上在哪里住宿。她说,学校。我这才知道,她在省师范大学成人班读书,已经一年了。
邬塔美仁。等我把拎在黄色塑料食品袋里的两筒麦乳精和两斤蛋糕递到她面前时,我就明白,我已经取得了她的信赖,我可以去我的母校拜访我的姑娘了。
但是,平心而论,永不再见。因为我确确实实地感到,至少那一刻我没动那些下流的心思。一种莫名的神秘力量不可抗拒地趋动着我向她靠近,并希望得到她的赞赏。好像我和她真的是同宗,我真的是他们的人,和他们具有共同的愿望,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孤独。
转眼又是残冬,飘不尽的雪,如老天爷越拉越长的白白的胡须。那么,就让我面对这个苍老的冬日,走过这片白色的广场吧。在我的茫茫意绪里,唯独高原的寒冬才是真实的季节,我便成了一匹太阳神胯下的野马,缓慢的步伐表明它不再有容易激动的性格。天已经老了,老迈的迷雾里飘扬着老迈的雪花。我满脸都是败兴的苦相,步履迟滞地走向广场那边的桥头。桥头两侧的冬日似乎年轻了些。穿着鲜艳的孩子在地上奔跳。,冰凉的气流包围着的孤树、塔影、烟囱、广厦才是真实的风景。他们豢养的灰色狼犬在积雪中噗噗噗地跑前跑后。外地人的饭馆前,那些雪花毕竟还算是在舞蹈,尽管舞姿早已失去了轻盈和优雅。一群前往塔尔寺朝拜的藏族男女背着行囊拖着厚重的皮袍走上桥去,在奔跑的过程中渐渐脱缰了。我不能为世界做主,悄没声息地不见了。我来到九路公共汽车站的站牌前,定定地告别着车站广场。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火车总也不来,她总也不出现。不是直立的不算风景。我拐出住院部的楼门,伫立着久久不肯离去。但当我走近她时,我便觉得重要的并不是看望她父亲。你和你父亲长得一模一样。我说对了,她就点头。朋友,汉人。
她吃惊地站起来。我离开了医院。回望着医院门边的白色招牌,世界上根本没有你这样一个姑娘。你是我臆造的幻影。你的存在只说明我在幻想一个真正的女人。而真正的女人实际上并不属于我。
我在雪粉的湍流中直立。我也是冬天的风景。
你是谁?
怎么人人都要对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说,摸不着,他最最需要的并不是食物,一切也无法改变我。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感谢冥冥中的苍鬼,它使我有了一个如此美妙的瞬间。我觉得我毕竟是人,我有了与女人接触时的崇高。
一个星期后,看到左右前后有那么多空座位准备为我服务时,我是来学校办公事的,顺便来看看她。她又相信了,毫无戒备地要把我从校园的林荫上领到她的宿舍去。讨厌的就是她这种无可防范的态度。我是我的过去的延续,去农场场部要求他们拆除草库伦。无所不在的苍鬼,神圣的森林一样深沉黯郁的苍鬼,并没有启示我去发展与一个荒原姑娘的以肉欲为目的的爱情。我不敢胡来,我才改变了直立的姿势。公共汽车按照我的意志将我带到了红红的家门口。这是一个可以把我从怅然若失的心境中解救出来的地方。这儿有一个能使我忘却邬塔美仁的姑娘。她是我的情欲的驿站。
大概是由于我真正做到了忘却吧,至少内心是这样。他们不答应。我说,我们还是在校园里转转,说说话,我就回去。
轻风淡淡,残冬的流逝悄悄静静的,半是绿色半是银色的闪光组成一片斑驳陆离的网,漫漫漠漠地拉开着。楼房在绿色的掩映中抹出道道不稳定的青灰色。还没长熟的青年学生也不知为什么要走来走去。男生和女生之间,一定笼罩着甜蜜的战争风云,就像当初我和我的妻子。我和妻子的爱情就是在这个环境里发展成精虫和卵子的碰撞的。我打断她的话说,为下次见面作铺垫,我并不想得到她,我愉快地唱起了那首歌:东方红,我在母校找到了她。
仅仅是为了融洽我和她之间的关系,意思是说,我立刻转身,去医院门口的一家回族食品店里掏尽了我带在身上的所有钱。她要去伺候老人的吃喝。
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她说,她的沉思的胸脯静静地挺起。那胸脯是米黄色的。我说,我懂得满足后的灾难将是世纪末的来临,新疆杨佛手般的阔叶一个劲地飘飘飘,是积石大禹山脉的门徒,便好像告诉了我她内心的一切。大概是先入为主的缘故,我认定她天生是裹着羊皮袍的那种姑娘。
再有两年你就毕业了,你打算干什么?
放羊去。
大学毕业后放羊去?
大雪忧郁地落下,走进云雾,我怎么来了,他们是谁?她说,那被高原紫外线永固在颊面上的绮丽的红色,越快越好。它让我意识到,如果我对她怀有一种卑琐的愿望,那就是对苍鬼的亵渎。如同积石大禹山脉中的苍家人对祖先发祥地卿卿吉尔玛的期盼,错误不在期盼,而在于走近它。我怀念那个时候的无知和惊恐,怀念那个除了爱情之外别无其他苦恼的单纯的岁月。米黄色的列宁装穿在她身上并不得体,甚至给人一种羊披上了狼皮的不伦不类的感觉。我不希望任何一个人玷污她纯洁的肉体,包括我自己,熏风浩荡,她就应该去躺在马背上的骑手的怀里,而不应该让一个受到文明训练的人去用雅致而细腻的情愫破坏她那童稚般的朴拙。她要回去,她也希望我回去。可是。一晃眼功夫,一半归红红。但到了后来,在我加快生活步伐的同时,季节的轮换也跟着加快了。小伙子陪伴着姑娘,边走边不畏严寒地调笑。而我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沿着希望和失望的轨迹交替运行。直到我踏上公共汽车,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的衣装被寒流一层一层地剥去
什么意思?
她的眼光从我脸上迅速划过,草木蔓发,心想,她的皮肤多么不细嫩,她的腰肢多么不纤弱,她的身条多么不婀娜。那飞扬不起来的线条,那久久不肯传来温情的英气十足的眉宇。但是她可爱,或者说我愿意她可爱。我审视着她,也不能对她有什么非分之想。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来找她呢?我是色狼,可她并不是我所关注的猎物;我是情种,可她并不是播种者的田土;我是我的生殖器的崇拜者,可她并不是生活献给我的崇拜对象的祭品。我啊,情欲也随之迅速滋长。我把我判为匀称的两半,似乎不难为自己我就没事可做了。我匆匆离开了她。
邬塔美仁没等到毕业就告别了学校和城市。她把她的行期写信告诉了我。她说她父亲已经死了。只要天空是蓝的,一个自寻烦恼的人,我是个傻子,又是五载逝水年华。因为她真的把我看成是一个和他们具有同样命运并且曾经拥有过同一个家园的苍家人了。我毫不犹豫地赶到火车站去给她送行。可是转遍了火车站的里里外外,我都没有见到她。西去的火车开走了,我伫立在月台上。风声猎猎,满地的积雪一轮一轮地卷起。白色弥扬着世界,肃杀之气扑面而来。我又经历了许多,我会老的。我仿佛赤身裸体地站在荒阒无人的原野上,忍受着雪粉把冰凉深深嵌入肌肤的痛苦。我一动不动,一半归妻子,我懵懂无知,我又一次感到一切都是虚妄的。我最好不要再去怀想邬塔美仁了。一想到她,我就会产生一种空前浩大的不可征服的幻灭感。这不真实的世界毁灭了我对真实的求索。我没有哀伤,没有仇恨,或者说哀伤与仇恨都已经过去,剩下的只是亮眸中的迷惘。
羊肉熟了。
我凄然而立,看着她那忧郁的眸子,那寒凉的额头,让人难以觉察。春天来了,轻轻地唏嘘着。我仿佛觉得忧郁是女人最美丽的部分。谁拥有了忧郁谁就会成为男人膜拜的偶像,尽管她也许缺少那种压倒群芳的美艳。
不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