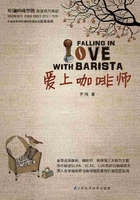哈哈,你这话可以蒙别个,却蒙不了我。魔鬼霍地从台阶上蹦了起来,禁不住手舞足蹈,得意忘形,不觉就露出了三头六臂的魔相,但那只存留了瞬间,随即又恢复了诗哲式的优雅造型。他一边说一边又坐回原处。关于《百合心》手稿丢失的事,你在国内外发表过多次谈话。我冷眼瞧去,就像看一部配音毛糙的翻译片,讲话和口型总是对不起来。譬如那字数,在日本京都大学座谈,孔芳卿记录的是二三万字,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座谈,夏志清记录的是三万四千字,在北京寓所接待采访,彦火记录的却是二万字,以你向来之精细,前后不应有这么大的误差?丢失的途径也不一致,对孔芳卿只笼统地说不幸丢失,对夏志清讲是凭邮寄竟遭遗失,对彦火讲当时乩哄哄,把稿子丢了,查来查去查不到,1980年在《围城》重印前记中,又说当日手忙脚乱中,我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如此圆枘方凿,自相矛盾,是十分违反你的风格的。你这种粗心大意,不要说以诱人犯罪为天职的吾辈,不会轻信,就连崇拜你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夏志清老先生,也觉得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你问我怎么想?我么,恕我放肆,我猜很可能被你主动灭迹了。你没有发疯,你只是预感到文字狱的威胁。一部《围城》,虽然给你带来大作家的声誉,却也潜伏着无穷的危险,它尔后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内,一直被压在阴山脚下,不见天口,就是明证。因此,如果你在《围城》之后,进一步发挥你的讽剌天性一你的所谓比《围城》更精彩,断断脱不了淋漓尽致的冷嘲热讽、明揶暗揄一难保不带来政治上的灭顶之灾。你警觉了。于是快刀斩乱麻,干脆来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喂,我这么说,没有冤枉你吧?
你想向我逼供?钱钟书哈哈大笑。曳着笑声的余韵,夜空划过一道金蛇似的闪电,跟着就炸响一串惊雷。雷声歇处,刚好又听得钱钟书的最末一句笑骂:你呀,你真是魔鬼!
不知阁下这是正面的夸奖,还是反面的赞美?魔鬼起初被响雷炸得跳离台阶,在雨箭中呼拉拉转了十几个圈子,然后才抚摸着胸口,慢慢地停下;说到乖觉、警醒,你可是比我强出百倍。我有时都觉得不可思议,以你那种口无遮拦的狂傲劣性一一《围城》姑且勿论,光《人兽鬼》中一个短篇小说《猫》,据说你就拿它影射讽刺了梁思成、林徽音、罗隆基、林语堂、周作人、赵元任、沈从文、朱光潜等一大帮社会名流一竟然于某天早晨,效老僧入定,金人缄口,幡然学乖,立地成佛;就像高速旋转中的陀螺,说停就停,不带一点前冲的惯性,这要多么大的定力!倒是令尊大人自己,1957年老马失蹄,被阳谋引蛇出洞,招致不堪回首的坎坷:
魔鬼的条分缕析,侃侃而谈,令钱钟书大为惊讶。他想这世界果然变化快,才星移斗转几十春,连魔鬼也似乎通了人性;他还在想……但是魔鬼打断了他的思路。
上帝不会白差你进入人世一冋,魔鬼谈兴未衰,天生奇才必有用。你的成就,前有《围城》、《谈艺录》,后有《宋诗选注》、《管锥编》。当然,价值最大的,是《围城》、《管锥编》,一部《儒林外史》式的讽喻小说,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读书札记。很多人称赞《围城》,因为它好看,而且百看不厌。相比之下,《管锥编》就乏人问津。不是它不值得看,而是无法看懂。正如房龙说的那样,在笛卡儿、斯宾诺莎生活的年代,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把自己的着作写得模糊蒙昽,从而使得他们的敌人难以理解和歪曲,这一点你也做得非常成功。你用古奥的文言筑起一座学问的围城,存心要把许多人,自然也包括许多是非拦在城外。侥幸闯过文言关的,你又要用渊博和睿智来测验他们的天赋。倘若把《管锥编》比作宝山,你拒绝才薄如纸的登山者,才厚如书也不行,你要求他们的才具至少要如一柄开山斧,一包烈性炸药,这样,才不至于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在方兴未艾的钱学热潮中,也有不同的声音,问题集中在你采用的形式:读书札记,让人感觉是万川分流,散珠未串,缺乏完整的体系。这是尘世的纷争,我辈魔鬼没有义务表态。但我辈看得清楚,《管锥编》酝酿于文革大寒纪,这事实本身就足以石破天惊。再说,那是一个容许文人学士建立自己学说的年代么?遑论构造体系!既然明知不可为,而你又执意要干,于是,审时度势,鉴往察来,你就取了现在的架构。这是你比较熟悉的空间形态,也是一种打不倒、攻不破、消不灭、摧不毁的空间形态。表面上的无体系,正暗含着独特的体系,即所谓千里绝迹,百尺无枝……
等等,钱钟书迫不及待地拦截下魔鬼的叙述。他此刻不仅是惊讶,简直还怀疑身在前尘的大梦。他记起那年在湘西初见,魔鬼整个儿表现得像一头乱拱的刺谓和一条腌过了劲的老黄瓜,其愤世嫉俗,尖酸刻薄,至今想起,还忍不住要脚心发休,头皮发麻。魔鬼当日的即兴发挥,尔后被好事者统统安到自己的名下,变成钱某人阴阳怪气、玩世不恭的铁证。而眼前的魔鬼呢,却分明成了知情识理、中正充和的长者。你老人家如今豁达多了,想必是年龄在起作用?钱钟书停了一下,又说,看来也读过我的不少书?
豁达谈不上,岁数愈来愈大倒是真的。魔鬼煞有介事地拂弄着银色的胡须,眉下抖动起两朵冷幽幽的黑焰,说,你们写文章,画画,写字,总爱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把平淡当成最高境界。其实,满不是那么一回事。花绝对是怒放的美,舞绝对是霓裳羽衣胜于小放牛,历朝历代的传世文章,绝对是文采斑斓的胜过文采枯索。所谓平淡乃更高一个层次云云,多半是老年人的自辩。人老了,体力、精力、活力都跟不上,激情的羽翼、想象的翅膀再也不能如从前那样自由自在地飞翔。但他们有地位,有威信,有话语权,于是,就制造出诸如此类的高论,为自己枯竭的才思贴金。孔夫子说六十而耳顺。人老了,洞悉世情,看穿利害,任你说什么,他都无动于衷,不予计较,这是其。但绝不是唯一。六十而耳顺的另一面是,人老耳背,你说什么,他都听不明,听不真,因此自然就不拿你说的当一回事。你笑什么?笑我班门弄斧?哦,对不起。现在回答另一个问题。你刚才问我是不是读过你的不少书?哪里,我们魔鬼不读,只偶尔用鼻子嗅一嗅。用你老先生的话讲,人的视、听、触、嗅、味五觉,可以互通或交墀,也就是感觉移借。
这本领,不是吹牛,我辈个个是天生的大师。蒲松龄记录的那个以鼻嗅文的瞽僧,习的就是我辈的末技。在人类是不学无术,在我辈则是不学有术。我辈就凭嗅。从阁下的着述,我还嗅出了一种风骨。你说风骨这词不应出于我们魔鬼之口?好吧,那就称它为铁质。我想说的,你大概也能猜出。在阁下生活过的这块土地上,从古以来,就存在着一种病态的游戏规则:热衷折磨男子汉,尤其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男子汉一这倒有点像普洛克路斯忒斯的那张铁床一试看历朝历代的冤鬼枉魂,多数莫不是因阳刚致祸。倒是娇小柔弱的妇女,一步一步得到了解放。难怪世人要惊呼阴盛阳衰!而在你的身上,却始终活跃着纯男的基闪。你啊呀,又来了,又来了!钱钟书警惕地扬起浓眉,讲话也不由地转成吴侬软语。他这才记起了魔鬼的本性,连忙检讨是否在不知不觉中又中了他的什么圈套。我早说过的呢:福过灾生,誉过谤至,这是辩证法的规律。所以最不喜欢人家给我戴高帽。现在,连你魔鬼都赶着吹捧我,夭地的讽刺真是到了极顶!哦,你今天追踪我到这儿,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吧?你还有什么话,就快讲。我马上就要离开。去哪儿?反正不是去昆仑山,更不是奥林匹斯山一具体保密。
别急,下面说几点你爱听的。魔鬼望风扯旗,顺流转舵;要不怎么配称魔鬼!他说:上帝虽然万能,依我看,并不是绝无败笔。比方说,第一,你老先生的脾气,就显太冷,对芸芸众生,甚至包括你的长辈与师友,缺乏必不可少的理解与同情一一这恰恰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弊病!一你的种种怪僻与乖僻,也都由此而产生。第二,你老先生过目不忘,属于西方人所说的照相机式的记忆。记忆太强,也有副作用,当年盛澄华就曾对人说:钱钟书说的话好像没有一句是他自己的……
说到这儿,魔鬼突然来个紧急刹车,像钓客拽着上了钩的鱼儿,在水面来回转悠,并不急于拎出:你很感兴趣,是不是?你既然感兴趣,我就不说了。关键时刻卖关子?没错,就是这么!事。本魔专门批发真知灼见,但等对方出个好价钱。你不买?真的不买?那末,再见!湖上有谁在叫我,听声音像是陈寅恪、吴宓,还有但丁、歌德,啊哈,承他们情,他们都是说好了要来为我饯行。魔鬼三蹦两蹦地跳到院门,又踅凹数步,压低嗓音,故作神秘地说:我很快就要离开地狱,你没有想到吧?这是天机,不妨先透露给你。反正你已魂归道山,不会再泄露给阳世。除非托梦,那玩艺儿世人又不信。喏,实话告诉你,自从那年在湘西拜会阁下,一篇《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的散文,让我名动三界,大黑大漆。上帝爱我鬼才出众,魔法无边,天恩大开,特赦我于近期脱离苦海,也到人世走它一遭。上帝说了,如果表现出色,将来还有机会重返天国。我么,嘿嘿,咱暗鬼不打诳语,今晚找你,实在是有一事相托。你不用张皇,这事不会耗费你多少精力。阁下最近若有机会见到上帝,只要代我向他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呶,就是跟他说无论如何,也不要让我成为钱钟书第二!当然,当然,我同时已通过当值天使向上帝反映。我想你本人再去说一次一一你比谁都更拥有这种权利一效果会更好。你老先生明鉴,我辈魔鬼虽然低人一等,亦有魔格;将来人世,也自有人格。你想,千修万磨,好不容易才挣来个圆颅方趾顶天立地,万一上帝开玩笑一上帝常常是令魔鬼捉摸不透的一一罚我终身跟在你老先生的屁股后面收拾脚印,那有多晦气!
魔鬼说罢,郑重道声拜托,随即身影一晃,出了院门。钱钟书望着魔鬼的去路,若有所悟,他从蓝色中山装的口袋掏出笔记本,在上面写道:新版《魔鬼辞典》,绝佳批评一一找一些不明不白的人,写一些不明不白的表扬文章;绝佳表扬一找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写一些不三不四的批评文章。写罢,轻轻摇头,拿笔在上面打了一个叉。想了想,又用一连串的圆圈把它勾回。并接着在后面写道:文章究竟如何,后世自心识者。当代人碍于利害得失,评价多作不得准;即便是地狱的魔鬼,也不例外。钱钟书又在小院略作逗留,仿佛重拾儿时的旧梦。然后化作一股清风,悠悠荡荡地飘去。他俩,一个想必前往太湖舟上,和老友切磋转世为人的战略部署,一个大概仍回他的仙山洞府,啊不!八成是仍回他的荒江野老之屋。
旦看滚滚红尘,又将上演新一轮的围城。